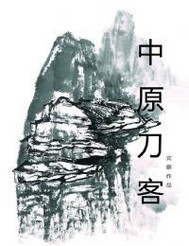刚到城梯口,猛然听到有人说着话向城上行来,大奎左右观瞧,左近并无藏身之地。情急中大奎一纵身斜里跳下城防梯,身在空中却是伸手一抄,正按在城防梯的边沿上。如此一来,身子整个悬空挂在了城防梯一侧。
一队元兵唠唠叨叨沿着城防梯上了城,经过大奎藏身之处时,竟是毫无所觉。
如今正值两军交战,元兵不得不小心提防,一旦被明军趁夜占了城头,要想夺回来就难了。
这队元兵刚过去,大奎便抖手发力翻身上了城防梯,沿着城防梯一路下了城。此时放眼再看,庆阳城内已是满目狼藉。沿街的房屋多数已经拆毁,只剩下残垣断壁。那些房舍的梁木砖石早已运上城去,用作守城之用。街道两侧满是困倦的百姓倒卧在地上,想必是被逼着协助守城了。
大奎闪身藏进一处暗影,向着庆阳城的纵深行去。
大户人家的客房还真是讲究,窗明几净字画古玩,无一处不透着雅致。虽然是黑灯瞎火,但靠着月光的微亮,大奎仍可将室内布置一览无余。
大奎要找一身衣服,至少要将身上的铁甲换下来。哪成想潜入大户人家,竟是进了一处客房。两日夜奔行数百里,大奎却是有些累了。找衣服也不急于一时,大奎走到床榻旁脱了身上铠甲置于床头,随即和衣而卧。不肖片刻,大奎已是沉沉睡去……。
虽是战乱之年,但街上仍传来阵阵更鼓响,却已是寅时初刻(凌晨三点十五分)。
大奎翻身坐起,伸手取了置于床头的连鞘长刀,黑暗中轻轻走到了门前。稍稍开了点门缝向门外看去,只见月华如水,不见人踪。
两军即是交兵之际,尚有这样的大户人家不受战祸,只有两种原因。一是破财消免灾祸,二是与元军亲近之家。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明军的死敌。有这样的大户出钱出粮出男丁支持元军,明军要想攻取庆阳城怕是要大费周折。
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趁早杀个干净。如果是积善之家,知道明军要围城,应该早就举家避祸了。
大奎闪身出了客房,沿着回廊一路行走,每经过一间房舍都要侧耳倾听一番。可惜寻了十余间房舍都不闻人迹。
出了小院,再奔后宅。后宅由内栓了中门,大奎纵身翻过中墙,脚一落地便闪身一处花丛后。即是中门上了门栓,后宅自然是有人居住的。
无奈秋风瑟瑟,所谓的花丛也只是几根花茎挡在身前,此处却非绝佳的藏身之地。放眼再看,坐北朝南一处大屋,靠西墙一排厢房。厢房是丫鬟仆人住的,那间大屋就该是本家的家主所居之处了。即是在后宅有一排厢房,想必这宅院的主人也是非富即贵了。
大奎看清了地势,转过花丛直奔大屋,来到门前蹲身倾听房内动静。好在是凌晨未晓,四下里静寂无声,大奎细心倾听下已对房内有了定论。房内有两人,呼吸间平稳安逸,想必是睡得正熟。
大奎试着轻推门扇,房门轻轻向内开启,竟是没有上门栓。大奎毫不迟疑,闪身进了房间回手关了房门。房中燃着檀香火炉,此刻虽是深秋,大奎也觉得温暖如春。这间房以雕花隔断内外两间,外室自不必看,大奎轻步走进了里间。
借着窗外的月色,可见里间陈设颇为奢华,迎面一张雕花大床放着帷幔,床前的地上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双鞋。
大奎走到床榻前,轻轻抽出长刀挑开了帷幔……。
这家宅院的主人姓廖名广博,在这庆阳城中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庆阳廖姓起源却是颇有些典故。最早的一支源自帝颛顼的后裔叔安,因其被封在廖国,又称廖叔安,他的后代称廖氏。廖姓的第二支是周文王之子伯廖的后世子孙,以其名字中的“廖”为姓,亦称廖氏。
只是这廖广博与王孙后裔却是一点都不搭边,其本为沿街乞儿,后经廖家收养并起了个名字叫做廖喜。原本廖家的老爷年岁已高,却是乐善好施。但膝下却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其子吃喝嫖赌早早被掏空了身子,且染了一身的风流病。廖老爷只此一子,见到儿子不成器,一时急火攻心之下撒手人寰。
廖老爷刚去不久,廖公子便将勾栏中的相好赎了身,八抬大轿娶进了家门。廖公子本就已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虽是堂堂仪表但却早已中看不中用了。新媳妇二八年华正值妙龄,又是烟花之地出身,如此却怎耐得住春闺寂寞。
于是乎,新媳妇和年少精壮的廖喜暗地里勾搭上了。
许是天随人愿,过不多久廖公子也因大病缠身一命呜呼。廖喜与廖家媳妇趁势占了田产,过起了小日子。后来这廖喜觉着名字不好听,请来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是廖喜注定要大富大贵,并且交友遍天下。廖喜便依照算命先生的话,改名叫做廖广博了。
这廖广博占了廖家的家业,廖家却非人丁死绝。也不知怎么来了廖家的远亲,得知廖家败落,家奴勾搭主母占了田产,当下一纸诉状告到了衙门。
可惜正值元庭腐败没落,廖广博在衙门上下使钱打点关系,那廖家的远亲反被判作诬告下了狱。俗话说:斩草除根。廖广博又花了大价钱,买通狱卒在饭菜中下了毒。那廖家的远亲却是有怨难申变作了黄泉冤鬼。
天下纷争,世道崩殂。但庆阳城却一直落在元庭手中,。这些年来,廖广博与庆阳城的守备大人相交甚厚,私下里称兄道弟。如此一来,廖广博更是作威作福,嚣张不可一世。有道是‘逍遥快活鸿福无边’,按说在这庆阳城中已无人能出其右。
说起来也该这廖广博倒霉,明军攻城两月有余。百姓的民宅从街边拆起,梁木砖石上城用作守城,唯独他廖广博的大宅完好无损。偏偏大奎今夜入城,却无巧不巧的找到了他的头上。
美妻在怀,软玉温香。当初的主母几年前又被他卖回了勾栏,如今他廖广博在庆阳城好歹也是家财万贯只手遮天的人物,怎么能藏污纳垢留个勾栏女子在身边。此刻陪着他的却是名门正娶的大家闺秀。
许是春宵劳累,大奎把帷幔挑开,站立在床榻前许久,这廖广博却并未觉察,仍旧抱着美妻酣睡。
大奎将长刀的刀头贴到了廖广博的脸上,心想:刀身冰凉,看你还不醒。谁知这廖广博真乃是一奇男子,竟是梦呓道:“别闹,明早还要……。”嘀嘀咕咕不知所谓,并伸手将贴在脸上的刀头拿到一边,继续睡。
大奎挠了挠头,心中想好的说辞却没用上。本以为将这廖广博惊醒,然后大义凌然的训诫一番,问明张良弼的去处然后将这对狗男女宰杀了。哪成想这廖老爷睡意如此之浓,竟是刀贴在脸上犹自不觉。
即然如此,大奎也顾不得斯文了,走到室中圆桌旁提了茶壶回到床边来,抖手向呼呼沉睡的廖广博头脸上泼去。哪成想茶壶的把手并不结实,竟是‘啪’一声断了。茶壶脱手飞出‘嘣’一声闷响正砸在廖广博脸上。
大奎也是手顺了,这一下力道虽是不大,但险些将廖广博的鼻子砸平了。廖广德睡梦中突然被茶壶砸到脸上却如何不醒?
“啊!~”廖广博猛地翻身而起,不想一柄钢刀带着寒光已架到了脖子上。
“再喊宰了你!”大奎恶狠狠的恐吓道。
这一阵动静,将廖广博的老婆也惊醒了。女人遇事多是沉不住气的,廖广博的老婆还没惊叫出声,大奎刀身一翻,以刀背横斩一记。正砍在廖广博的老婆脖子上,这女人哼都没哼便昏死了过去。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廖广博起身跪在床上磕头如捣蒜,连连求饶不迭。
大奎也不客气,拧身坐到了床边,将手上长刀立在床边,这才好整以暇的问道:“我想问点事情,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说与我知晓?”
“方便方便!好汉有话尽管问,廖某知无不言。”廖广博说的斩钉截铁,那里有一丝的犹豫。如果回答问话不方便,估计掉脑袋就会很方便。
大奎也不兜圈子,直问道:“张良弼现在何处?”
整个庆阳城被明军围得铁桶一般,张良弼统领城内元兵拼死抵抗,廖广博怎会不知张良弼的大名?只是如今守备大人都归张良弼管辖,元兵在城内四处戒严。廖广博只是一介土财主,却哪里知道张良弼的去处?
听到大奎的问话,廖广博不仅露出为难之色:“好汉莫要见怪,这张良弼乃是统管庆阳城的大将军,我这……。”答着话,廖广博却是心思电转,看样子来者不善啊,竟打听张良弼的去处,既如此当要好生应对。
大奎点了点头,笑道:“你不知道我不怪你,但在下还有一事请问。”
“好汉请讲。”廖广博强挤出一副笑脸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