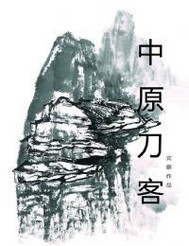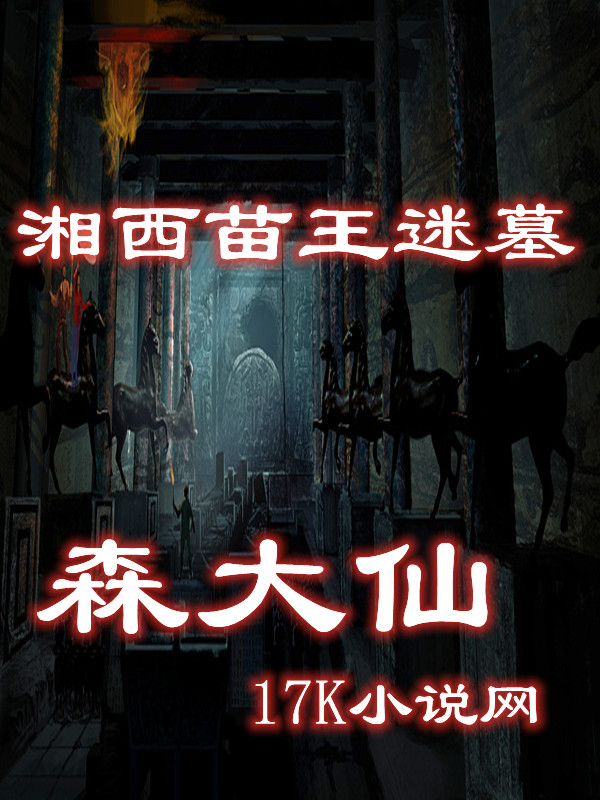见到余铮一脸疑惑,大奎笑道:“本官办案遇到一些事情,须得过江查访。有劳余大人为本官筹措一番。”
大奎此言一出,余铮心中方才释然,但转瞬思量道:“如今已入长江春汛时节,江水猛涨水流湍急。若是舟船过小恐不稳妥,若以大船过江恐被江对岸发觉,这可如何是好?”
大奎不禁问道:“趁夜过江应不妨事吧!”
“哎!”余铮当即反驳道:“夜晚过江便如盲人瞎马,便是大船又岂能在激流之下安然过江?不妥不妥!”余铮连连摇手,大奎反倒有些急了。
“那要如何才能过江?哎~~。”大奎一拍大腿站起身来,急的在厅内来回踱步。过了片刻才道:“既如此本官不过江便是!”
余铮也站起身来,呵呵笑道:“大人一路鞍马劳顿,且到驿馆歇息。”
大奎也确实觉得有些累了,当即在余铮的安排下去了客栈,饱餐鼾睡直到夜半三更,大奎却有些睡不着了。若是在太平府耽搁了时日却如何能在一月内救出潘磊家人?若无舟船过江难道肋生双翼飞过去?大奎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灵光一现。
儿时也曾下水嬉戏,但毕竟是在水中玩耍,无非是在水中胡乱扑腾几下,不过却也能游得一段。如今自己大病初愈,但还算身强体健,只需请个水性极佳的师傅来请教一番,自然能学的泅渡之术。
大奎心中计议已定,当下再次强迫自己入睡直到天明。大奎穿衣起床后刚拉开房门,门前两名衙差却早已恭候多时,原来这两人竟是余铮派遣来充当侍卫的。大奎不由苦笑,自己一路劳顿贪睡至此,有人在门前站了一夜竟不自知。
大奎洗漱已毕,就在客栈吃了早饭,便随两名衙差去了府衙门。见到余铮余大人,大奎将心中想法跟余铮一说,余铮惊得连连摇手道:“张大人切莫开玩笑,这长江水流之急岂是人力能胜之的?不可不可!”
大奎哈哈笑道:“余大人但放宽心,本官自有分寸。大人且为本官寻来精于水性的艄公一名便可。”余铮见大奎执意为之,只得命人去寻精于水性的水手艄公。
过了将近一个时辰,衙差方带来一名布衣汉子。这汉子一脸虬髯身材壮硕,尤其是双目炯炯更见精干。汉子进了衙门后厅,来到厅中站定抱拳道:“草民谢之化,参见两位大人。”说着深深一揖到底。
余铮呵呵笑着起身过来搀扶起谢之化道:“本官寻你前来有要事相托,来来来,这位是江南通政使张大人,你们慢慢聊。”说着又对大奎道:“张大人且与谢壮士慢慢细谈,本官尚有他事便不相陪了。”说完向大奎拱拱手,随后示意厅内其他人等退出了厅堂。
大奎见其余人等皆出了厅堂,这才起身拱手道:“本官今日有一事相求,还望谢壮士能应允。”说着便向谢之化作了一个揖。
谢之化连忙迎上来搀扶大奎道:“大人何必如此,有事但讲无妨。”
大奎抬眼望定谢之化道:“本官欲横渡长江,想请谢壮士帮忙。”
谢之化闻言一惊,半响才道:“长江两岸皆有军兵把守,却如何能渡?如今江上连渔民都不准下水,却如之奈何?”
大奎微微笑道:“来,谢壮士请坐。”说着拉着谢之化落座,这才坦言道:“本官欲泅渡长江,想请谢壮士指点一二。”
“啊?”谢之化大惊之色,这春汛长江便是自己也游不得远,眼前这位大人却如何能泅渡?江水之急可谓鹅毛不起,人若下水岂不是自寻死路?
大奎见到谢之化一脸惊诧,不由笑道:“总能想到什么办法的,谢壮士精于水性,张某求教了。”大奎说着起身亲手倒了一杯茶双手奉上。
谢之化连忙起身双手接过茶盏道:“大人无须如此多礼,折杀小人了。”
“谢壮士坐。”大奎再次请谢之化入座。
二人再次就座,谢之化沉吟良久方才道:“若要过江绝非易事,须知人若入水必会不堪水力而被冲走。如此须得加重身体的重量,但如此一来亦会下沉。这……。”
大奎笑道:“谢壮士只管教我如何游水便可,其他事情我自理会。”
谢之化闻言这才道:“浮水者首重换气,须以口为之。游动时或在水面上或在水下切记肆意呼吸,在江水中若是吸水入鼻则性命堪忧。”这些大奎倒是懂得,儿时嬉水也曾被水呛到过。鼻子里进了水会让人发懵,所以游水时呼吸是不用鼻子的。
谢之化续道:“潜游以蛙式,水面游动则以叠式,口中之气不能持久故此需频频换气。”谢之化说到这里,大奎打断道:“谢壮士不如与我同到江边,详细教我。”
谢之化点头道如此也好,说罢与大奎起身前后出了厅堂。
大奎与谢之化策马到了长江边上,寻了一处死水湾。就此水湾,谢之化详细教授大奎游水之技艺。如今已是近五月,天气温暖江水却颇具寒意,谢之化周身脱得只剩底裤,下水将游水的技艺一一示范。
大奎也不避嫌,当下也除了衣裤鞋袜下了水。谢之化尽心的教授,大奎细心的学,未及午时大奎已经深得游水的要领。原来游水门道颇多,既要感知水流动向亦要运用身上部分肌体,若是不明水流动向势必会被水势所挟,若是肌体用力不当定会很快疲乏,大奎直练了近两个时辰方能在水中随心所欲。
大奎习水性主要是为了不时之需,如今大奎水性已熟便不再耽搁,与谢之化回到太平府衙随之命人找铁匠打造了一柄铁桨,又准备了一艘小舟送到江边。
大奎换了一件平民百姓的衣服,持了铁浆来到江边。眼望茫茫江水大奎暗自祈祷:“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满天神佛保佑我渡此长江吧。”
随着小舟下水,大奎跃身纵上小舟,岸边十余人前来送行。看着大奎只乘小舟下水,余铮不禁心中感叹:‘都言无知者无畏,这位张大人果然不是等闲之人,一叶扁舟竟要强渡长江,如此气魄却非常人可比……。’
大奎伸浆在岸边一点,小舟全身下水。大奎随之左右挥舞铁浆入水。小舟便如风中黄叶一般划入江中,江涛滚滚浊浪滔天,奎奋力划桨一路漂泊前行。亏的大奎臂力惊人,小舟虽是随波逐流但却依然航向不改直向北岸行去。
小舟行至半途,历经数不尽的惊涛骇浪,小舟内已是积水甚多,大奎不由得暗暗心急,如此这般未到对岸恐怕舟内已经灌满了水。当下大奎挥桨更见急劲,小舟一路乘势破浪向长江北岸疾划。
自然之力自非人力可抗拒,眼看距北岸还有数十丈远近,小舟终究还是沉了……。
大奎不等小舟沉没,已纵身前跃扑入江水中。身子刚一入水立时被江水推出数丈远,大奎奋力前游才知长江水流之利害。每每前游数丈只时已被江水向下游冲出十余丈,但虽是如此大奎仍是按照谢之化当时的指点,感受水流借力前游。
数十丈的距离大奎直游了半个时辰方才上岸,环目四望不禁傻眼。四周芦苇茂盛,脚下淤泥没膝,再向前行举步维艰。待到大奎等上陆路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何时已丢失,无奈之下大奎只得赤脚前行。
放眼望去原野茫茫却不见人家,渡江时被江水向下游冲了不知多远,如今身陷何地却也不知。大奎赤脚走在路上,赤脚时不时被路上石子搁到直疼的大奎呲牙咧嘴。大奎空有疾行之术却无法施展,好歹走到一处荒野草甸,这里稿草甚厚。大奎到了这里席地而坐歇息了片刻,便起身去收集干草。
少年时跟着母亲也学过编草鞋,大奎用了半个时辰编就一双草鞋穿在脚上,如此一来便舒服多了。大奎望天定向,心知自己此刻身在庐州东南,当下取道西北一路疾奔。
此时的大奎多时不曾如此疾奔,此刻却比之从前慢了许多,大奎心中不免暗暗吃惊。武术有句谚语:天天练日日功,一日不练百日松。如今大奎久不练功,此时奔跑起来确实感到些许吃力,但晓是如此也比寻常人快上数倍不止。
这也难怪大奎疏于练功,实则是大奎曾受毒害身体比之从前自是不如,加之横渡长江体力消耗过甚,此时再奔跑难免力不从心。
大奎从后晌奔到天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村落。大奎进村后寻到了一户农家,大奎不敢实言相告只说自己路上遇了土匪,故而落难到此。这家人是一家五口,老中幼三代。虽是贫困之家但心地颇善,留大奎吃了一顿饱饭住了一夜,第二日大奎便问明庐州所在上路了。
庐州古名庐子国,又巢伯国。春秋时舒国及群舒诸国皆在此地。隋朝开皇三年(583年),改合州为庐州。大奎一身破衣烂衫足蹬草鞋进了庐州城,把守城门的元兵并没刁难。大奎状如乞丐身无分文,元兵自不会多加注意。
进得城来,大奎随便找人问道:“请问庐州同知朱守仁朱大人府邸怎么走?”
那人摇摇头道:“我一个百姓却如何得知做官的去处?你问别人吧。”
大奎无奈只得再次寻人查访,眼见一间烧饼铺子。大奎走到摊位近前拱手问道:“店家,敢问庐州同知朱守仁朱大人府邸怎么走?”
谁知那店家开口便问道:“你买烧饼吗?”大奎一瘪,伸手一摸怀中却是空空如也,当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摇摇头。
店家见到大奎一身寒酸又不买烧饼,当即挥手道:“去去去,不买烧饼来此作甚,快走快走。”
大奎无奈只得向城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