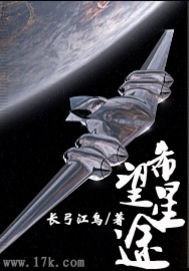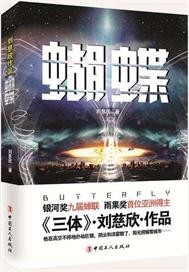17点15分巴克特号货船摇摆着笨重的身子缓缓离开东原这颗满是风沙的世界,在货船离开的第二天瘸子的小酒馆终于倒塌了,而一支由孤儿组成的队伍背着沉重的行装穿行在沙丘的阴影间,身后遥远的方城远远传出人的喧嚣声,有哭喊声、有欢呼声、有哀嚎亦有兴奋。
“一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一个稍小的孩子问着狼一,狼一没有回答仅仅是深深的看了眼远处的方城心里默默的念叨:“会的!我们会回来的。”
这是离开的决心,也是承诺,更是希望。
夜幕下,在微弱的台灯的灯光下,一条隐秘的信函被加盖上了联邦军部的印章,而印章的右下角苍劲有力的批注着两个刺眼的红字——“绝密”。
信函通过特殊渠道转送出去,看着信函内容的安东尼奥眉宇狠狠的皱了起来,发白的眉宇间掩藏不住的不安和焦虑,心里反复思考着:“做还是不做。”
“做又该安排谁去执行这项命令,不做又怎么回复总统官邸直接下达的密令。”
一种深深的隐忧始终在安东尼奥的心间徘徊不已。
当天微微亮起,初升太阳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打了进来时,思虑了一昼夜的安东尼奥终于下定了决心。
“回总统阁下,联邦的意志志高无上。”最终安东尼奥选择了遵从这项密令。
一艘联邦的轻型战列舰关闭了无线电通讯,以静默的方式沿着联邦防御网络的边缘向着一个被遗忘多年星区行去。
只是这份密令在抵达安东尼奥之前一份复印件已经经过帝国情报部门转送至帝国的行政中枢,当萨罗斯七世拿到复印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这一天帝国的皇帝陛下心情格外高兴,也难得让侍女为自己清理了下下巴那毛茸茸的大胡子,嘴里更是哼着宫廷乐队很早前创作的一首乐曲《荒野我来了》的一小段曲调。
被飞船爬升时头脑充血的感觉惊醒后,迷迷糊糊的许飞宇转了个身又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中,他实在太困了、太累了。
这一觉睡的特别的熟,特别的香甜,也特别的辛苦。
站在高高的山崖上,看着山下苍黄的大地,远远的可以听到不知名的野兽的嚎叫,远远的视野的尽头一座耸立直插云霄的山峰,孤寂、苍凉的耸立着。这一幕已经不陌生了,从十岁那年起每天做梦都会来到这里。
沿着十岁时摸索的山道走下山崖,崎岖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岩石的缝隙里还长着青绿的野草,顽强而又脆弱的在岩石的缝隙里摇摆着、挣扎着。
山崖的风很大、很冷,昏暗的阳光打在人身上没有一点一滴的温度,在走到山脚的最后一个拐角从草丛里抽出一根结实的木棍。
山下等待自己的是各种各样的野兽和怪物。
从十岁开始的八年时间里,在这睡梦中每一夜都在与这些野兽进行厮杀,手里的木棍断了也不知道是多少根了。
耳朵里听着四周狐狗和豺狼的低低的吠叫,对于这种体格小身体灵活的野兽,许飞宇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手中握着的木棒缓步而行,步伐不急不缓每一步的步距都是相等的,步伐的跨度并不大,这样足以保证遇到突然袭击自己的腿部、腰部的发力点维持在最佳状态。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这个世界里没有生与死,有的仅仅是疼和痛,那种刺入心扉的剧痛甚至会让人窒息。
这是一个充满着战斗的暴力的世界,从走下山崖开始四周警惕的狐狗就注意到了许飞宇,在一声犬吠后,原野上扬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来了!”许飞宇双眼微微的一眯,脚下一声沉闷的爆音,握着木棍抢先出手。
所谓先发制人,无数次痛苦的经历和经验让许飞宇率先冲了过去,他要赶在狐狗和豺狼们合围前尽可能的多杀掉一些。
每一棍挥出飞溅的狐狗和豺狼的鲜血,以及高高抛飞出去的尸体,而许飞宇身体则尽可能的缩在棍棒的攻击半径里。挥舞的幅度并不大,脚下则踏着古怪节奏的步伐,仔细看去怪异而又充满着一种奇怪的韵律。
双脚每一步并不踩实,挪动时总是以一个半圆形的弧度旋转,挪动的同时也是腿部小幅度的横扫。
这种奇怪的攻击方式是在这些无数次同这些狐狗豺狼的战斗中缓慢积累起来的经验。
记得第一次进入这里许飞宇仅仅坚持了不到五分钟就被跳跃起的狐狗扑入怀中咬中咽喉死去,那种疼痛让许飞宇整整一个晚上都捂着喉管**。
而第二个晚上来到同样的地方,许飞宇惧怕了躲在山崖上不敢下去,可没过多久从远处飞来的巨鹰,让许飞宇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冲下了山崖,这次许飞宇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咽喉,没有一只豺狼和狐狗成功袭击中。
但最终的结局却是被成群围上来的狐狗扑倒在地,最终依然是没能躲过死亡的命运,那一夜许飞宇全身每一处都充满着疼痛。
第三个晚上的结局也是同样以死亡告终,只是比第一天稍稍多挺了几分钟后罢了。
在疼痛的恐惧下许飞宇很快患上了一种对睡眠恐惧的症状,尽管怕的要死但依然不自觉的会睡着,睡着后来到的依然会是这里,面对的依然是这些要人命的野兽。
就这样一日一日的痛苦中慢慢的度过着,害怕、恐惧、躲闪,成了十岁时许飞宇的写照,直到有一天在方城看着一个被强行收取了城市保护费的杂货店老板,在被抢夺了大半财务后,并没有像其他那些同样被收取了保护费的店主那样痛苦、流涕、咒骂、叫嚣,仅仅是一谈笑依然乐呵呵的看着外面升起的太阳。
“您不生气吗?”许飞宇曾问过小老板。
杂货店小老板笑了笑道:“气啊!气了他们不还要来收、来抢,与其为这这些不能因为生气而改变的东西生气,不如坦然去面对,生活嘛?就像……”小老板想了半天,到嘴的话最后还是忍住了,蹲着身子拍了许飞宇的脑袋不自觉的笑了笑。
“说了你也不懂……小孩子。”
那天后许飞宇依然害怕、恐惧、躲闪,只是面对黑夜来临却多了一股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