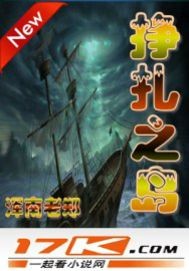“张妈”并不是这位帝王的生母,而是奶娘,皇权争霸时期这位帝国堪比一代国母的伟大女性用自己的亲生骨肉保全皇族一脉,在萨罗非七世执政以后也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劝阻了这位义气奋发的皇者的铁血报负,转而用怀柔策略将原本处于和联邦劣势的帝国硬生生拉平,可以说在萨罗非七世的心目中,他的这位奶妈的所占据的位置比的上他手里的权杖。
屋子里很是陈旧,同这色调金碧辉煌的皇宫大院比起来,他甚至连一间普通的柴房都有些比不了。
皇宫里的厨房并没有联邦那种快速高效果的高科技,转而用柴和煤炭,最高档的不过是一些微波设备。
“皇帝可是饿了?”这位乳母一生最牵挂的不是权利,也不是金钱,只是她养大的这个孩子,原本这个时间乳母会去听上些宗教的祈祷或者朗诵些祈福的经文,这些被联邦丢进博物馆的书籍确成了这位乳母最喜爱看的东西。
对于皇帝陛下的驾到,侍女们都是诚惶诚恐的,这些深宫里的女子都拥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她们看的出此时陛下心情并不好,而且非常糟糕,虽说萨罗非七世被誉为帝国开国以来最贤名的皇帝,没有之一。但是只要是皇帝,只要他还是个人,而且是个男人,他总会有脾气的,要知道人来脾气的是那种暴虐几乎可以毁掉一切。
“母亲,孩儿不饿。”在乳母面前那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终于走下了那高高阴森冷酷的冰冷王座,像一个受了气的孩子一样,周围的侍女早就在自觉的退了下去,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位帝国站立在权利巅峰的母子。
似乎是看出萨罗非有心事,乳母张妈慈祥的笑了笑。亲手给萨罗非倒上一杯桑菊茶,乳母年纪大了嗓子总是不怎么好,几乎这种桑菊茶几乎成了这简陋的住所里的常备品。
看着母亲满脸的深深的沟壑和沧桑的白发,萨罗非同幼时一样将自己的烦恼一一倾出,只是这一次不一样,萨罗非只是简略的说下前方战时有些复杂之类的话,并没有提的过深。
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张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给萨罗非倒上一杯水。
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将水喝下才絮絮叨叨的说道:“小时候家里穷,父亲总是会偷偷的上山去打猎,家里孩子也多,但总会带上我,当时我以为是父亲害怕我在家孤独,直到父亲去,我才知道那是坚强,后啊果不其然父亲一走,后母就将我撵了出去,家住的太过偏僻,走出来靠的就是父亲留下的一张弓和一把猎枪以及那被当做是垃圾丢8说完张妈站了起来从一个老久的储柜里翻出一个旧的酒囊,看着破破烂烂的酒囊,萨罗非没来由的心里一酸。
乳母只是摇了摇头慢悠悠的回味着:“就是这东西我逮住了第一只猎物,现在那东西叫什么我是搞不清楚了,那些个学者们给他加的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名字听起来绕口,我是记得村里叫他山猫子,肉可香了,那皮可值大钱了。
为了这后母又把我找个了回来,从那以后我就干起了父亲的营生,成了一个猎人。
现在啊,想想都有些不可思议,村里进山的的猎人很多,但每年总有进去出不来的,身边的人总是换啊换的,从熟面孔到生面孔,再从生面孔到熟面孔,这人命真的不值钱,那时候啊挺恨那些山猫子和腰豹子的,后来想想,我想要他们的命,谁的命不是命,他们吃人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现在总想起父亲那句话:不要总感觉自己才是最聪明,做一个合格的猎人要将猎物看成一个聪明奸诈的对手,而自己则是一个平庸的笨家伙才行。”
乳母张妈声音顿了顿后轻笑了起来,有些自豪的说:“后来我就是村子里最好的猎人,他们总不相信我的话,老是将山猫子和腰豹子当成自己家逗弄的土狗,现在他们依然听不进我的话,前几天小菲利给我拿了些小村子后来的一些趣闻,那些和我同龄进山的都没出来,他们啊总说自己聪明,总说山猫子笨,可我觉的山猫子比他们都聪明。”
走出简陋的屋子,带路的侍女在前面引路向紫衣轩行去,刚走到流金桥原本沉着脸的萨罗非七世猛的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的痛快和明悟。
接着萨罗非七世对着身后跟着的侍女猛然笑了起来:“朕是不是很笨,哈哈哈。”
听着皇帝那爽朗的笑声,乳母嘴角浮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回议政室,告诉紫衣,朕今天不过去了。”说完萨罗非七世大踏步的向寝宫外走去,边走边吼道:“厅议!”
再看这份喜讯,萨罗非七世脸上的乐观情绪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和思虑。
坐在高高的皇座上,萨罗非七世声音冰冷而肯定的说道:“战线长兵力不足,这是好事,但虫族不是动物,我们不应该只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好好想想这四个点未免太巧合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没次我们的士兵都是刚刚守住,这说明什么,我想不用我教你们吧?”
一时间大殿上寂静无声,接着轰的喧哗了起来,有深思的,有讨论的,有不以为然的,更有的压根就没有表情,依然跟死去人一样面无表情。
这一切萨罗非七世看在眼里却什么也不说,相信他们都是聪明人。
俗话说的好,巧合的巧合就不再是巧合。
“陛下您的意思是他们并没有尽全力,可这说不通啊。”左宰有些犹豫的问道。
这的确说不通,这样不温不火的攻击,若是从这个角度来品位,虫族这样的构想就大有文章可做。
“除非,除非,……”终于有人隐约的猜测到了某种可怕的可。
大殿上几乎同时说那句不可能,但似乎也只有这些才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