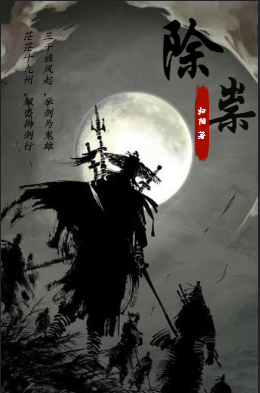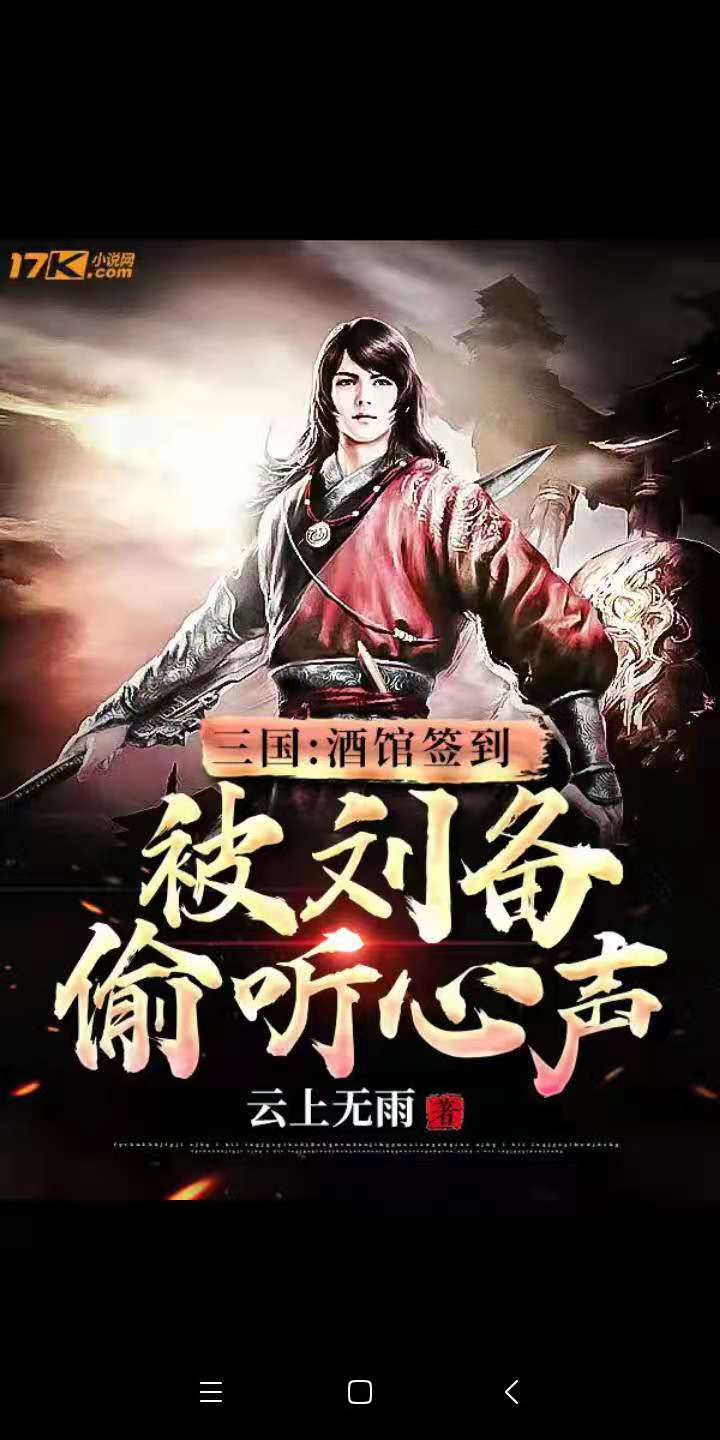天阴了,又晴了……天黑了,天又亮了……
我叫晚晴。
我只记得,爸爸妈妈去世的那年,我还是个傻的,带着不满三岁的弟弟糖果在城隍庙前满嘴满脸的开心——哇,有糖吃了。回到妈妈灵前,看着哭晕过去的二姨,瘫软成一团的舅舅姨妈们,在我迷蒙的脑袋里才有了亲人逝去的悲伤,跟着大人们跪在灵前哭。那年,我五岁。
我母亲兄弟姊妹八个,我父亲兄弟姊妹五个。那个年代,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没人愿意抚养我和弟弟。祖父母怜惜他们的三儿子夫妇英年早逝,怜惜他们的孙子孙女没了爹妈,担负起了抚养幼小的我们的责任。父亲母亲间隔不足百天相继离世,这个家庭头顶的天空布满了阴霾。
上世纪末西北的农村家庭,或许熬着熬着,日子也就熬过来了吧。
家里院子西面两间红砖红瓦的屋子,一道墙隔出一个小套间。紧挨着的北面一间土坯房,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的小厨房,里面摆着一张台球案子——听说早年是父亲开矿矿上的家具。听说,那个年代,家家有矿,生出来儿子都是矿长。祖父母来到家里,面缸里没了面,揭不开锅了,于是祖母背着一口面袋子在剩下的三个儿子家,一家一家的要,前面说了,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最后祖母红肿着眼睛回到家,要到了不到三分之一口袋的黑面粉。我还是傻傻的,不明白生活的艰辛,弟弟应该也不懂的,他比我还小两岁呢。
从前,母亲在院子里的小园子里种着些耐活的蔬菜,小葱啊,白菜之类的。我还记得,院子里有一棵山楂树,父母在的时候,院子北面的另一角养了许多兔子,那是童年的欢欣之一。当然,那时候兔子可不是萌宠,都是养来食肉的。所以,我总记得父亲和三舅舅将兔子挂在山楂树上剥皮的场景。
祖母童瑛兰是非常能干的农村妇女。父母逝后,她将家中的小园子修整翻土,来年春天长得葱葱郁郁。自那以后,夏天总能吃饭新鲜的蔬菜。奶奶还移来一株葡萄藤,如今搭在新建的屋檐上,夏日可以乘凉了。
祖父廖德同年轻时也是爱闯荡江湖的。他热衷于收藏各类麻钱(铜钱)和硬币,然后带上奶奶烙的饼坐上火车去其他地方贩卖。卖是卖不了多少钱的,倒是每次都是摔得鼻青脸肿有气无力的回来——毕竟老了。但是爷爷每次都会给我和弟弟带新奇的吃食回来,比如那时候我们眼里稀缺的面包,真是绝味啊,怎么那么好吃。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弟弟站在或蹲在院子北面的土坎上,眯着眼睛细细品味,仔细斟酌那面包里的味道……那样的日子,也算无忧无虑吧。不懂得生活的悲伤与艰辛,难受的时候想哭就哭,想闹就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