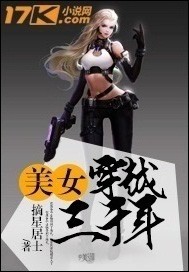楚庄云说着,双眸含情,在楚庄澜看来,着实别扭,心中怒火像是浇了一桶油,登时就熊熊燃烧。
‘二弟如此了解,恐怕暗地里,不乏走动吧。’楚庄澜阴冷的声音问道,如此对立场面,楚庄云一点都不觉得过,如此对立,已在他意料之中。
‘皇兄如此说话有些伤人吧,玉溪并不常到我这里,只是遇到难以解决之事,求我帮忙而已。’楚庄云立即回应,没有再称呼太子妃,而是直言其名,让楚庄澜听起来两人更加亲昵了些,姜玉溪从未去过庄云阁,但楚庄云用的却是并不经常,不经常,那就是去过。
‘这是我的家事,二弟好像不应该插手吧。’楚庄澜的脸色已经明显阴沉了许多,皇宫里最忌讳的就是女人不安分,楚庄云简单几句话语,将所有过错全扣在姜玉溪头上,在楚庄澜心头,像是撒了一把盐。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看到她难过的模样,却忘记了这是皇兄的家事。’楚庄云带着歉意道。简单一句话,给了楚庄澜一个小台阶。
即便楚庄澜不想下,也得下。并不是他这个太子当得窝囊懦弱,而是对手太强大,想要动他,需要十足的把握,加之,这里毕竟是庄云阁,每个角落都可能藏着杀手,楚庄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末了,还会落个是他先动手挑事的结局。
冷哼一声,楚庄澜愤怒转身,拂袖离去。身后楚庄云双眸微眯起,嘴角弯起一抹弧度,红唇轻启:‘太子殿下是不是应该把朝服还给我呢。’
楚庄澜感觉被电击了一般,光天化日之下,要他脱去外衣,只穿中衣中裤在皇宫里行走,岂不是明摆着要他颜面扫地。
‘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朝服被撕坏的事情既然皇兄已经知道我也就不隐瞒了,新朝服,还请皇兄自己想法吧,’楚庄云的话语很是坚决,是男人,敢作敢当,楚庄澜毫不犹豫,将朝服脱下,身着一身白色中衣中裤,离开庄云阁。
几声嘲讽笑声响彻半空,陆延年从房顶落下,站到楚庄云身边。
‘看到了吗,他要与我为敌,总以为自己是赢家,最终却要着中衣出门,如此太子,如何与我相争。’冰冷而阴险的凤眼微微眯起,嘴角撇起一起笑意,深邃目光望向楚庄澜远去背影。
‘殿下神机妙算,将来定是江山得主。’身边陆延年双手抱拳向楚庄云躬身道。这不仅仅是句奉承,作为楚庄云的心腹,若是主子称霸江山,自己也可稳坐半边。
满心的怒火转到姜玉溪身上,楚庄澜双手紧握,若不是她去求楚庄云帮忙,楚庄云怎会去洗衣院,如此明显答案,烙印般烙入楚庄澜心中。
换上常服,心中怒火依旧不减,为何白莲死了,她还要活着,明明都是她所为,为何还要死不承认,躲进洗衣院就能摆脱所有罪孽吗?如今还要走近他的劲敌,是要决心与他为敌吗?
疾步去往洗衣院,这一账,应该去好好算算。
‘澜哥哥。’清脆银铃般的声音打断楚庄澜的思绪,驻足转身看去,玉儿已经朝他走来,粉色裙袍在风中飞舞,此刻他却无心欣赏。
‘看你疾步匆匆,是要去哪儿?’沈玉儿问道,楚庄云把自己朝服给楚庄澜一事她还未知。
‘洗衣院’楚庄澜愤怒的语气道,虽然知道冲动像条没有理智的毒蛇,可想到姜玉溪给自己制造的难堪,心中就气愤难平。
沈玉儿断定,楚庄澜肯定知道了朝服被撕坏,但没有质问她,想必还不知道朝服是她撕坏,心中隐隐不安,毕竟一切是她所为。
怔怔的看着楚庄澜离去的背影,沈玉儿决定跟上去,看看姜玉溪会怎样辩解,自己也好知己知彼,全身而退。
‘太,太子殿下。’菊儿在门外看到楚庄澜习惯性的紧张害怕,也难怪,屡次见到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准没好事。
紧闭房门被意料之中一脚踢开,姜玉溪忍着头痛从床上坐起,眼前男人青筋暴露的模样,心中大概猜到几分缘由。
朝服被毁,尽管楚庄云送来一模一样的代替,只怕没有不透风的墙。
脑海还在思绪,暴怒男人已经走到床边,已知来意,姜玉溪勉强下床,迎上楚庄澜愤怒嗜血的眼睛,本来心中忐忑不安,事到临头时,却感觉释然了,该来的总会来,就算你躲也躲不过。
‘是故意让我难堪吗?’冰冷质问传进耳朵,姜玉溪不解的眼神看向楚庄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还请你言明。’
‘还要抵赖吗?为何撕毁朝服又要送别人的朝服给我,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恬不知耻的去求那个男人,但我真的很想看你求饶的样子。’楚庄澜满肚子火寻找发泄,有力大手狠狠抓住姜玉溪纤细手腕,似要捏碎的剧痛感瞬间传遍全身。
沈玉儿站在门外,同样想听到仇人求饶会是什么样子,可心里却又忐忑不安,心慌的厉害。
菊儿见事,哭喊着给楚庄澜跪下,除了哭喊,她什么都不能做,她只是一个小丫鬟,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救不了任何人。
‘太子殿下,求您饶了她吧,昨日沈……’
‘住口!’菊儿刚要道出昨日之事,姜玉溪便严词制止,双眼带着命令的目光投向菊儿:‘不要向他求饶,你这是哭给谁看。’姜玉溪故意将楚庄澜的思路从昨日之事转移到菊儿求饶上。
就算道出真相,也不见得楚庄澜就会相信,她在这个男人眼里,早已是只会抵赖的坏女人,况且,沈白莲之死还没有弄清真相,心中总觉得或多或少的欠着沈玉儿的。
‘主子,您干吗死扛着。’菊儿两行眼泪流到嘴边,埋怨着主子,想为她抱不平,她却死死不肯,那沈玉儿已经心狠手辣浇她一身水,撕坏衣服,主子却还要给她顶罪。
‘菊儿!’姜玉溪厉声制止,回过神来对上楚庄澜嗜血眼睛:‘朝服已坏,即便你杀了我,也无济于事。’
突然的拉扯力将姜玉溪拉近身边,另一只手抓住后脑头发,向后的拉力,姜玉溪不得不抬起头对上楚庄澜愤怒眼睛。
‘朝服撕坏我会杀了你吗?为什么要背着我去找他。’听得出眼前男人已经知道一切:‘你我若能平等相待,又怎会发生今日之事。’
姜玉溪故意将事情曲折,听起来好像因为害怕再起风波再受蹂躏把撕坏朝服换掉。一边菊儿知道姜玉溪秉性,不能说是不依不饶,但也不是任人欺辱,任人宰割的对象,现在把左右过错揽在自己身上,菊儿实在不明白主子是涂了个什么?
话音落,楚庄澜冷笑两声:‘平等相待?那白莲呢,你残忍杀害白莲河她的孩子的时候,为何不说平等相待。’猛拉一把纤细手臂,姜玉溪险些跌倒,撞进楚庄澜宽阔胸膛。
‘如果你是想故意让我难堪,我会让你更难堪。’温暖气息传进耳朵,却是如此冰冷的温度,抬头看着楚庄澜冰冷憎恨的眼神,冷笑起来。
‘很可笑吗?’结实大手增加了力度,手腕传来更深疼痛,冷笑表情退去,换上痛苦神色。
‘朝服确实是楚庄云送来,并非想要让你难堪。’姜玉溪解释,痛苦表情不减,本就受伤寒,又加之楚庄澜蹂躏,头痛欲裂,眼前视线模糊,忽明忽暗。
痛苦表情并不能让楚庄澜的憎恨退减丝毫,在他眼中,姜玉溪不过是在为了免受折磨而伪装柔弱,白莲不能死而复生,他也绝不会让她得逞。
结实大手松懈,换来的是用力一推,姜玉溪身体瘦弱加之有病在身,怎能承受男人一推,身体向后退去数步,最终后背撞在结实墙体,方才停下。通红粗糙的手用力扶住墙体,勉强站稳。
‘差一点我就相信了你的说法,白莲之死或许另有真相,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了,你就是你,看似懦弱,阴谋算计,不可能改变。’楚庄澜心灰意冷看着眼前扶墙而站的女人,却不知,姜玉溪是在用所有意识强撑着身体站着,眼前一切就像黄昏一般,模糊不清,黯淡无光。
‘你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我所言,句句属实。’姜玉溪头痛欲裂,双眼太累,想要闭上,但意识让她不得不睁开。
‘这里是洗衣院,他是皇宫的二皇子,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媚术去求他,但我不傻,如此巧合之事,若换做你,你信吗?’楚庄澜反问一句,姜玉溪无言,也不想再说,浑身酸软,难过不堪,也无多余力气再去与他争执,多说也无意,他也不可能相信。
‘屋外之人鬼鬼祟祟,不用藏了,进来吧。’楚庄澜冷声道,虽然满肚子怨恨,但并没有冲昏头脑,身后一直有人跟着,脚步有力,很容易被发觉,一想便知是不会习武之人,想来也只有沈玉儿鬼灵精怪,一路跟随。
‘这里阴暗潮湿,我们还是快些走吧,免得沾染晦气,那就不好了。’沈玉儿看一眼已经有气无力的姜玉溪,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提及沈玉儿半字,倒是那个丫鬟,一心想要澄清,沈玉儿赶紧催促楚庄澜离开,以免丫鬟道出实情。
‘姜玉溪,你若想要平等相待,最好不要耍小聪明,阴谋算计,总会付出代价。’楚庄澜冰冷警告回荡耳边,拂袖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