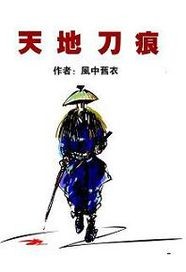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星罗棋布不知多少渔家水寨。沿岸的碧溪镇算不上什么大镇,但仗着水利之便,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来往往,也颇热闹。
镇西头立着一座背水而立的二层小楼,飘扬的酒旗上写着葳香楼三个大字。楼下有三四十席散座,二楼迎着门的三面围着一个悬空的回廊,沿廊排了一圈雅阁。整座楼都是木制的,既无凿花亦无朱彩,算不上雕栏玉砌,倒是简练大方。
这天是腊月初三,天色阴沉沉的,乌云层卷,覆压在广阔的湖面之上。葳香楼门口挂了两层厚厚的棉布帘子,用作挡寒。帘外风舞,帘内酒香,倒似是两个世界一般。
此时尚未到晚膳时分,楼下却已三三两两地坐上了客人,看打扮,有渔民庄户、有儒袍书生、有商贾小贩、有庄稼汉,有的甚至像绿林好汉,时时传来操着各地口音的高谈阔论之声。
二楼廊上,夏侯瑾轩拾阶而下,他未及弱冠的年纪,眉清目秀,文质彬彬,颈间一枚金锁,腰间一块白玉,一身大红锦袍衬得肤色如玉,内着白缎长衫飘飘似仙,并不见得多华美,但细瞧过去,一处暗绣,几笔丹青,无不精妙绝伦,恰到好处,更显得风雅出尘。就连身后跟着的小厮向儒,一身红色短褂也是上好的料子,走起路来精神奕奕,毫无忸怩之色。这等做派,非累代富贵不能有。
夏侯瑾轩寻了一处靠窗的座位坐下,略略打量起四周,只见客人们服装不一,神态各异,但无论斯文还是豪迈,俱是精光内敛,显是练家子,微乎其微地叹了口气,嘟囔道:“可惜可惜,竟无半个文人雅士。”向儒正熟练地吩咐伙计沏上一壶上好的金镶玉,听闻此言,忙欲出言提醒,莫要一语不慎招惹了哪位凶神恶煞,转念想了想自家少爷的性子,又不禁摇头作罢。
夏侯瑾轩对随从的担忧一无所觉,目光仍漫无目的地四顾看去,身后,酒店掌柜暮菖兰正百无聊赖地斜斜倚在柜台上,一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着算盘珠子,点头笑笑算作招呼。别看这位大掌柜年纪轻轻,却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泼辣爽利、八面玲珑,一手快剑功夫也俊得很。她身着一件翠绿衫子,五官十分艳丽,特别是那对含威凤目,透着一股子精明干练,现下虽是一副闲散模样,却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哪个伙计敢偷懒耍滑,保准一个冷眼递到。
正当此时,酒楼一角坐上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说书先生,他身材瘦削,佝偻着腰,干枯的手一拨琴弦,抑扬顿挫地讲着:“自那夜叉、罗刹、修罗三部缔结盟约,去岁突然大举入寇,官军一触即溃、仓惶南顾,大好中原逐渐沦于贼人之手。贼寇凶横残暴,所到之处焚掠残杀,百姓苦不堪言,依依生死别,凄凄闻《黍离》。”说着,清了清嗓,拨了拨弦,幽幽琴声起,唱腔颇含几分悲凉,吐字听得出北音。
难得在江南听到北音唱出的诗经名篇,夏侯瑾轩顿时来了兴致,正准备凝神细听,门口的棉布帘子忽然被人掀起,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姐姐,姐姐,快进来暖暖。”这女声清脆动听,夏侯瑾轩不由侧目看去。
只见帘下走入一位娇俏伶俐的少女,青衣短裳,杏眼桃腮,樱唇瑶鼻,一双灵动美目仿佛时时带着笑,其后又跟进一位蓝衣姑娘,回身细细将门帘放好,又抬手抚了抚妹妹衣上褶皱。她样貌虽不如妹妹明艳亮丽,却处处透着一股子温婉沉静,眉如远山含黛,目若秋水凝波,如云秀发挽成简单的发髻,簪着白玉莲纹簪,青玉额饰缀在双目之间,更衬得眸光清润。
夏侯瑾轩不禁在心中暗赞,真是一对谪仙般的人物,俏生生往门口一立,满室生辉。
酒店伙计眼尖,忙迎了上去,笑嘻嘻地招呼道:“二位美人,里边请,打尖还是住店?”那伙计身材壮硕,浓眉朗目,头发随意地系在脑后,寻常伙计的衣饰穿在他身上,无端惹上一股草莽江湖气,不像伙计,倒像是哪个寨子里的“英雄好汉”,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二人看。
那两姐妹好似被吓住一般,怔在当场,温婉沉静也好娇俏伶俐也罢,全都只剩下一股子茫然。
夏侯瑾轩见状不禁暗暗好笑,他也不是头一天来了,这伙计自然认识,名叫谢沧行,向来大大咧咧、口无遮拦,但在他看来,这位谢大哥看似粗俗的谈吐里,时不时会透出一丝禅机。
这时,就听身后的暮菖兰恨恨骂道:“死性不改!”只见大掌柜的眼中,冷冷寒光如刀似箭地向伙计射去。仿佛是觉出了这股子杀气,谢沧行忙回过头来,赔笑道:“掌柜的有何吩咐?”
暮菖兰咬牙切齿,纤手一指:“姓谢的!没看见陆兄弟要会账吗?还不快去!”随即转向两姐妹温言道:“我家这伙计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让二位见笑了。两位姑娘容色照人,咱们这种小地方实在少见,任谁见了,都忍不住多瞄几眼呢!失礼之处,我给二位陪个不是。”
那年长的姑娘回过神来,忙抱拳道:“言重了。”
暮菖兰伸手一迎:“二位里面请。”侧目就见谢沧行还戳在原地,凤目立刻剐了过去,“还不走!”谢沧行却像没见着似的,不痛不痒地嘿嘿笑着。
旁边的客人见状笑道:“我说掌柜的,你怎么请了这么号人物做伙计?看把人姑娘吓的,莫不是以为你这儿是黑店了吧?”听那口气,显然甚是熟稔。
“石兄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谢沧行笑嘻嘻地应道,“光冲着咱掌柜的,就算是黑店,还怕没人来吗?”周围人闻言,顿时笑作一团。
青衣姑娘扯了扯姐姐袖口,凑到耳边低声道:“姐,你看这……”蓝衣姑娘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也压低了声音回道:“静观其变吧。”
妹妹点点头,不禁又偷瞟了几眼正被大掌柜拎着耳根子教训的谢沧行,只见那壮硕的大块头被窈窕俏丽的老板娘数落得毫无还手之力,狼狈不堪地讨饶不休,禁不住扑哧笑出声来,被姐姐责备的目光一瞪才勉强收住。
两人在夏侯瑾轩的邻桌落了座。夏侯瑾轩不好再打量下去,啜了口茶水,再度听起了说书。
“话说赵铤随着众兵将一路且战且走,眼看着渡口已然在望,心说可算见着了生机。须知贼寇再厉害,终究不谙水性,这江水乃是他们的克星。可喜归喜,赵铤总觉得哪里不对,定睛望去,只见江边渡船竟不知被哪个杀千刀的凿沉了大半,歪歪斜斜地搁在浅滩上。
赵铤暗叫不妙,回头一看,心顿时凉了一大半,那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只见地平线上扬起一阵尘烟,黑压压一片人马攒动,依稀可见竖着靛紫旌旄,必是赫赫有名的铁鹞骑无疑,再看那大纛之下,一人提枪纵马而立,身披飞鳞甲,头戴紫金盔,一张青面獠牙的铁面具,狰狞可怖。可知来着何人?”
说书先生顿了一顿,续道:“来人正是贼寇统兵大将,幽煞将军,汉名龙溟者是也。此人最是奸滑狠戾,自南侵以来尚未尝败绩。众兵将都吓破了胆,只知道徒呼吾命休矣。不过说来也怪,谁都知道铁鹞骑素以攻势迅捷出名,可却见那幽煞将军龙溟把手一抬,千余铁骑就停在一箭地外不再动弹。赵铤心下狐疑,直往官军中戴着红缨的将官看去。那将军反应倒快,立刻三两下除去将军甲,一门心思往那仅剩的渡船上挤去。将且如此,何况兵乎?众人也回过味来,一窝蜂似的往江边涌,自相践踏,尸体满路……”
只听那青衣姑娘悄声问道:“姐姐,铁鹞骑还有那幽煞将军,都是什么来头?”
蓝衣姑娘回道:“铁鹞骑是夜叉铁骑的精锐前锋,素以来去如风闻名,而执掌铁鹞骑的就是幽煞将军,也是夜叉部的大王子。胡人尚武,国中要职多为武官,这幽煞将军一职不啻于储君之位,就像我们中原的太子一般。”
青衣姑娘点点头,又问:“这沉船莫不是他使下的奸计?”
“多半是了。”夏侯瑾轩接过话茬,皱起眉头,喃喃自语道,“这胡人当真好毒的心思。渡船沉的多了,官军怕是要破釜沉舟;沉的少了,争抢又不致如此惨烈。只可怜我华夏大好男儿,浑身力气全没用在杀敌上。”说到此处,不禁幽幽一叹。
靠窗一桌的汉子听得怒起,一对扫帚眉根根直立也似,拍案喝道:“这帮官军,瞧那熊样!”
邻座同伴忙一拉衣襟下摆:“别胡说!万一被官人听去了……”
“怕什么?”边上一作渔人打扮的老者冷哼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要是那帮孙子能顶用,咱们还犯得着巴巴地赶来这里开什么武林大会?”
说书先生的讲述还在继续:“话说这时候也不分是兵是官,全争先恐后地往船上爬,落水冤魂不知凡几。赵铤使出吃奶的劲儿,好容易扒住了船舷,又不知被哪只手扒拉了下去。忽听得身后号角声起,千余铁鹞骑分成三路,如饿虎扑羊一般掩杀而至。
人说铁鹞三千能抵官军十万,对付这点吓破了胆的残兵败将,还不是砍瓜切菜一般?赵铤心中一阵绝望,把心一横,高声喝道:‘兄弟们!挤不上渡船也是个死,不如跟贼寇拼了!’可哪有人理他?
就在这倾巢之际,忽见江上远帆若隐若现,有人喊了一句‘援兵到了!有救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军中的气氛渐渐变了。赵铤心中一喜,忙加把火道:‘兄弟们守住渡口!别让贼人抢了去!’这时终于有人肯听了他的话。
贼寇反应却也恁快,一名黑脸蓄须的魁梧骁将领着十余骑,一路左砍右劈,纵马直奔渡口而去,只见他从马背上抄起一柄百斤大刀,臂上肌肉贲起,猛地一声大喝,向着栈桥砍落,几刀下去,登时木屑四落,轰隆一声,栈桥远端登时塌入水中。
赵铤一惊,暗叫不妙,须知江边水浅,这援兵所乘皆为大船,不论登船还是登岸,都须得靠栈桥才行。众人也意识到要糟,忙抢上阻拦,可那十余骑甚是骁勇,牢牢守在贼将身后,栈桥又窄,当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见那黑脸贼将再度举起了大刀,这刀要是落实了,栈桥非得七零八落不可。”
讲述至此,听者俱是一脸紧张。尤其是夏侯瑾轩,一双眼睁得大大的,一瞬不瞬地盯着那说书先生。
“千钧一发之际,忽见船上人影闪动,一人如大鹏展翅一般斜飞而下,去势未竭,足尖在浮于水面的木板上一点,又斜掠出去十步远,掌上铁爪直捣黄龙,奔那持刀贼将的要害而去。细看此人,方才弱冠年纪,紫衣长靴,身手矫捷,赵铤心中立刻闪过一个名字——折剑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