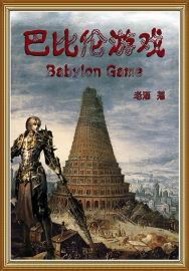张赢川连说带比划,三人已听得清清楚楚。金花公主坟巧夺天工,竟然依托山势,把整个碗形的山谷充分利用起来,做了龙穴,又费了如许心力,消砂纳水藏贪狼招七杀,端的是一口好穴。
张政社小心翼翼地用旋风开出一条长约三十米的水平盗洞,果然又碰到了一道直上直下的墓墙。这仰盂墓真象足了一只碗,两侧石壁成弧形把整个海子水库抱在怀中,下面又有一圈墓墙作为碗底,真正的墓室就在碗底之中。如此奇墓,不知怎么想得出来。
按上面海子水库的大小来看,这墓室也小不了。张赢川爬到墓墙跟前,拿过黑折子探查了一番,低声道:“这墓墙跟上面的石壁不一样,是青条石用糯米浆筑成的。按五行方位推断,火蛊只在上面弧形的石壁才有,这里恐怕另有玄机。老二,把探龙笔找出来。”
张政社点点头,依言取出一根黑黝黝大拇指粗细的钢管,装上龙头龙尾。这探龙笔前端形如毛笔头,只不过是精钢打造,一圈圈细密的螺纹从尖到底,跟钢管相交的地方,绕着一匝鱼鳞似的凸起。龙尾末端有两根三寸长短的手柄,平时并在一起藏在铜管中,退出铜管,向两边分开,就像酒瓶木塞的开瓶器一般。
张赢川接过探龙笔,戴上胶皮手套,把龙头对准相邻两块青石条之间用米浆填塞的夹缝,右手握住龙尾用力一旋,钻进去了半寸长短。张赢川一边动手一边低声解释:“这探龙笔跟洛阳铲一样的道理,是专门用来探查墓墙背后机关的。一般积沙积水或积火墓 ,沙水火油硝粉之类,都在两层墓墙之间。钻进去之后,并起龙尾,龙头后面的鳞片翻起,沙水火油就到了铜管中,再合上鳞片退出来,就知道是到底是用什么防盗了。”
说话间,探龙笔已钻进三寸有余,突然停住,再也钻不动了,像是碰到了什么障碍。又用力试了试,仍然纹丝不动,张赢川一皱眉:“奇怪,这探龙笔的龙头,连花岗岩都钻得动,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反旋龙尾,慢慢把探龙笔退了出来。
张奉孝举起荧光棒,照向龙头,只见精钢打就的笔尖上,沾了一些铁屑样的东西。张政社赫然惊呼一声:“好家伙,铁水。”
防盗墓技术发展到了唐代,已经登峰造极。张奉孝看过一些资料,讲的就是唐陵。唐陵凿山为墓,工程浩大,从山体的一侧开墓道,把山腹整个抠出来当作墓室。棺椁装进去以后,墓道里用碎石回填,墓门则用长条石砌死。长条石之间用铁条箍紧,再灌上烧熔的铁汁,铁汁冷却之后,整个墓门混然一体。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金花公主墓竟然在墓墙里也灌了铁汁。要知道金国虽然兵马骁勇,冶铁技术却不过关,所用兵器都是从大宋用马匹牛羊之类换来的,铜铁之贵可想而知,又怎么会舍得在一座公主坟里这般使用?
张赢川知道铁汁青石牢不可摧,单靠自己几个人赤手空拳,干到下辈子也甭想打穿墓墙。一商量,决定还是用先前的办法,贴着这道墓墙,向下打竖井,再折而钻到墓底之下,反倒盗洞进去。如果连墓底也是这般难挖,再找不到虚位的话,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张政社依言施为开始往下打竖井。秦琪儿突然笑了笑:“大哥,依你易理术数研究之深,难道还能找不到虚位?我先前还以为,打盗洞下来就是直奔金花公主坟的虚位而去,怎么会舍近求远,发现墓墙挖不动之后才想到去墓底找虚位呢?”
张赢川伸手往头顶指了指:“这墓处处不依格局。古人以天为圆地为方,所谓天圆地方。你看,地面上神道之类的一概没有,地下却大费周张,上面仰盂,底下墓室分明也是圆形而非方形,这样不依规矩的墓,我还是头一次见。虚位有没有都还是个问题,哪里敢说一定能找到虚位。”
张政社已经打入地下两米有余,突然停下旋风铲,弯腰从土里捡了一截树根样的东西仔细看了看,扬手扔出洞来:“奇怪,打到现在都一百多米了,怎么还会有树根?”
张奉孝闻言一愣,来的时候查过,平谷县地下水位也不过十几米,这一路往下,除了土壤越来越潮湿,也没见到地下水,本来就觉得奇怪,这时候又听说挖到了树根,可算是开了眼界了。
张赢川拾起树根,三人仔细一看,更是觉得奇怪,不但没腐烂,表面竟然还有弹性,一点儿不像老死的树根。秦琪儿用指甲抠下一点儿皮,发现里面竟然青白湿润,顿时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树汁苦味。
张赢川脸色一变,厉喝一声:“老二,快上来!”
张政社不明所以,弯腰去抓旋风铲,抬头笑道:“没什么,这旋风铲结实得很,就算是棵大树用不了三分钟也搅烂了……”,话音未落,脚脖子一紧,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借着荧光棒的光亮,低头一看,惊得把剩下的话吞回了肚子里。
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堆树根,已经把竖井底下铺满,如活蛇一般互相纠缠成一团,还有几根昂着头在半空中来回摇晃。缠住张政社的那一根粗如儿臂,钻在土里的部分不知有多长。冒出来的一头缠住他脚脖子上,越来越紧。
一转眼的功夫,又有一根来回摇晃的树根碰到了张政社的小腿,立即收紧。张政社双手撑在竖井的井壁上,跟树扯往下扯的力道斗了个旗鼓相当。张赢川在上面看得清楚,左手撑在井沿,身子一侧,右手伸进去,一把抓住了二弟的胳膊,拼命往上拉。
张政社得此大援,慢慢挣脱开缠在腿上的树根,双腿交替用力慢慢爬出井口,已经汗透重衣。定了定神,探头看看,树根仍然在井底纠缠不休,慢慢把井壁都盖住了,只是爬了一米左右,就不再继续向上,不由松了一口气:“好险,再晚一步,就爬不上来了,可惜旋风铲扔在下面了。大哥,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跟活物一样?”
张赢川冷冷一笑道:“还能是什么?树根!这座墓处处透着古怪,刚进来的退堂里遇上的是水蛊,上面石壁伏了火蛊,这可能就是木蛊。时干落于墓库,七杀罩顶,底下生气勃发,木现生机,一旦被缠上,用不了一袋烟功夫,就能把人缠得骨碎筋断。”
张政社吁了口气,抹抹额上的汗珠:“还好还好,木蛊上没布着迷离蝶,要不这条小命休矣。”
张赢川腮帮子哆嗦了一下,摇摇头:“五行蛊相生相克,浑然一体。迷离蝶断然不会只布在水蛊火蛊上,只是不知什么缘故,刚才没有发作而已。如果我猜得不错,这周围地下,到处都是树根,在哪里打竖井都一样。还得想办法下去,除了这些鬼东西。”
秦琪儿一骨碌翻身起来,从背后摘下猎枪压上子弹,往井口一趴,笑道:“这个好说,就是活的一枪下去也崩碎了。”说着枪口下压,看也不看伸进洞口就是一枪。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只震得张奉孝脑袋铮铮作响。张赢川没想到这丫头说干就干,脸色一变,探头往井底一看,不由叫得一声苦,低声喝道:“老二,抄家伙!”
话音未落,张赢川伸手抓住秦琪儿,往后一拉,身子一仰,两人都倒在了地上。接着,贴着井壁,数十根粗细不一的栗色树根从井口爬了出来,张牙舞爪在空中似长蛇一般摆动。井口湿土撑不住,一块块脱落,掉进了井里。
张政社脸上青筋突起,回身从包袱里抽出唐刀抖手出鞘,一脚把张奉孝踹到一边,半跪着抢到井口处,挥刀就砍。树根似乎有灵性,纷纷扭动着向后缩去,张政社这一刀何等快捷,终究有几根避之不及,刀锋过处,被砍下尺来长的一顿,掉在地上。
说来也怪,被砍掉的树根落在地上,像被抽去了灵魂一般,抖动着越缩越小,到最后只及原来的一半粗细,也短了许多。趁这机会,张赢川拖着秦琪儿向后挪了挪,退出树根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沉声道:“别开枪!老二,金克木,唐刀正是它们的克星!”
张政社点点头,矮着身子向前挪了一步,挥起唐刀横七竖八乱剁一气。树根像是对唐刀颇为忌惮,四下里炸开了窝,原来紧密的一团散开来,更显得诡异无比,不时有几根被唐刀削掉,立时缩到树根堆里,还在外面挣扎扭曲的越来越少。
张政社砍了一阵,颇为解气,回头笑道:“一物降一物,五行生克,总有解决的办法。”话音未落,冷不防一根粗如儿臂的树根突然暴涨,趁张政社回头分心的一霎那,卷住了他的手臂。张政社手一松,唐刀落地,跟着一股大力涌来,身体被树根拖倒,慢慢向井口移动。
张赢川离唐刀较近,只是胳膊被秦琪儿压在身下,急切间抽不出手来。张奉孝心急如焚,来不及扑过去捡唐刀,伸出把绑在小腿处的那把匕首拔了出来,一咬牙,向前一扑,狠狠砍在了缠住二哥的树根上。
张赢川来不及阻止,闷哼一声:“不可!”
张奉孝手腕一疼,只觉匕首砍上去如中败革,不但没把树根砍断,反倒被反弹回来,再也抓不住,眼睁睁看着掉进了井口。张政社胳膊被缠紧,左手在湿土里划出一道深沟,离井沿只有一尺远近。
幸好他出手这么一阻,那树根顿了顿。这功夫张赢川已抽出胳膊,一把抓住唐刀,赶在张政社被拖进井口之前,及时砍了上去。树根慢慢松了开来,退回了井中。张赢川这一刀虽没把它砍断,好歹救下了张政社,长出一口气,一扬手,把唐刀扔了回来。
这几下兔起鹘落,秦琪儿根本来不及反应,见张政社安然无事才放下心来,拍拍胸口道:“可吓死我了。对了,既然金能克木,为什么二哥的唐刀能行,蔡叔那把匕首却不管用呢?”
张赢川还没来得及开口,井底下突然轰隆一声,接着井口缩成一团的树根突然一起坠了下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拉扯一般。四人相顾骇然,不知底下发生了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怪物?
张政社抬起左手看了看,小指没动,松了一口气,笑道:“顶多就是几根树根成了精,大不了再砍它几刀。我去看看,”说着拖着唐刀,矮着身子往井口爬去。
离井口还有一尺远近,地面突然剧烈抖动了一下。四人对望一眼,刚稳住身子,就听轰隆之声不绝,接着地面往下一沉,泥土四溅,眼前一黑,连人带包被裹挟着急坠而下。
张奉孝身在半空,借不上力,好在感觉没受伤,稍一定神,刚想问问其他三人情况如何,一张嘴就吃了一口土。就在这时,背上一凉,一股大力撞了上来,把下冲之势阻住,显然是掉进了水中。
水流很急,张奉孝不会水性,笨手笨脚地扑腾了几下,怎么也挣扎不出水面,一张嘴,连土带水灌了两口,心中一凉,没想到头一次进墓倒斗,就把小命丢了,早知道就学会游泳再来。正自怨自艾呢,后背一紧,有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衣服,接着冒出了水面。
张奉孝伸手抹了把脸,吐出嘴里的泥浆,睁开眼来,只见秦琪儿正抓着自己的衣服往岸上拖。不远处岸边的湿地上,张政社蹲在一个人身边,不停地敲着自己的秃脑壳,看起来甚是着急,张奉孝心中一凛:大哥出什么事了?
秦琪儿又游了几步,撒手放开了张奉孝,回过头来道:“还不起来,想让我一直把你扛回老家?快点,这一趟没白来,运气不算,没想到地下这么深,竟然有一条暗河。”
张奉孝身体在水里漂了漂,脚底踩上了实地,顾不上跟她啰嗦什么暗河,好不容易上了岸,向张政社身边跑去,边跑边向四周扫了一眼,冷不住抽了口冷气:
这他娘的究竟是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