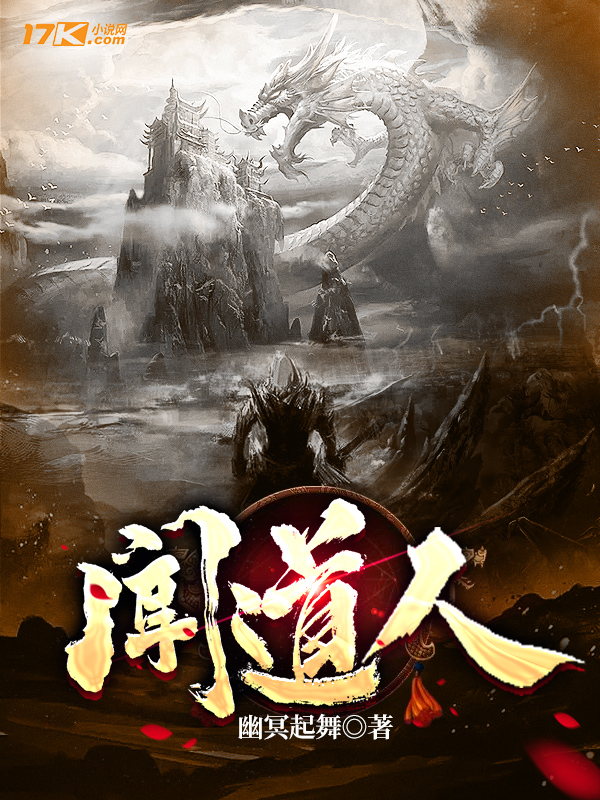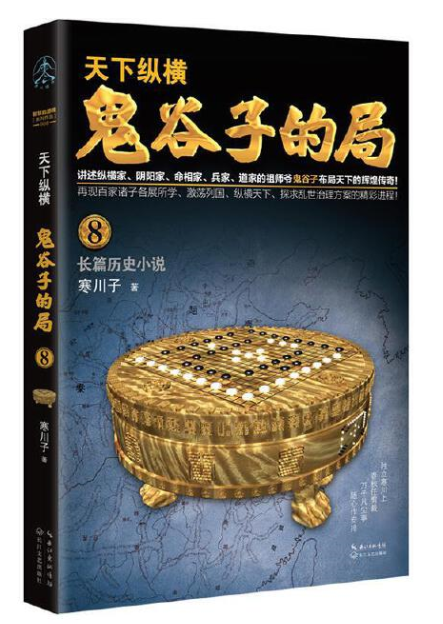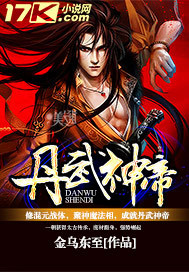数百年后,北宋年间,西北成州,一座小村落中。
时值农历六月初六,烈日当头。放眼望去,热浪滚滚,天地一片惨白,就连知了也似因为太热,在树上拼命的叫着。空无一人的村中土路之上,被行人踩的有些虚浮在地面上的尘土,随着阵阵清风吹过,在空气中旋转飘荡着。
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之上,漫山遍野全是青柏,层层叠叠,郁郁葱葱,映衬的天空更加蔚蓝。手持羊皮鼓的鼓声带着高低起伏的韵律不断的从山上某处传来——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接着就是一阵谁也听不懂的嘶哑歌颂神灵的声音传来,然后是鞭炮声、唢呐声响起。
“快点,跑快点,要起轿子了!再晚就看不到了!”听着唢呐声音的响起,一群十几岁的少年边跑边喊,沿着一条林间曲折的山间小路,向着半山腰的那座庙宇奔去。
此时庙宇门前的院子上,在院子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之上钉立这四根高约一丈、粗约碗口的小木柱,从小木柱上牵引出了四根大红色的绳子,以四根木柱围绕成一个矩形,然后在矩形较长的两边上,每隔一尺就有一根细细的白绳引出,与矩形的短边平行,从地面抬头看去,仿佛是将整个矩形分成了一尺的长条形。在这些分割的细细的白绳上边,则是挂满了有草纸做成的小三角形,小三角形的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微风吹过,各色的小旗摆动,看上去异常美丽。
而在院子上边,此时已经满满的跪拜着一群虔诚的村民。庙宇的六扇大门仅有中间两扇开着,显得庙堂内有些昏暗,十二名手持着类似扑克牌中黑桃形状的羊皮鼓的鼓手正在按照某种古老的韵律敲打着手中的鼓面,正面三下,然后鼓身一转,再在背面敲击两下,然后抖动三下。随着抖动,羊皮鼓手把下方悬挂的些许铁环发出撞击声,给人一种韵律十足但非常庄严的感觉。
在十二名鼓手前方正中央,站着一名约莫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造型奇异的帽子,上边插着不知是什么鸟类的羽毛,双手扶着供桌,摇晃着头脑,嘴里不断的含糊念着大家听不懂的神咒。在他的脚下,则是一盆还在燃烧着符纸的瓦盆和一只捆住双脚的彩色大公鸡。在供桌中央摆放着香炉,里面三柱九根供香正在缓缓的燃烧着,袅袅青烟从长长的随时有可能会掉下来的香灰上盘旋升起。香炉两侧摆放的则是两盘贡品,左边一盘是水果,右边一盘则是西北特有的面点食物,两盘贡品的供果上边均有着不知是用何种染料涂抹的红色图腾。在供桌的左方,悬挂着一顶钟磬,一个道童隔一会敲击一下。
供桌后方的庙堂之上,一共摆放着三座神像,左边的一座是一位面目清秀,书生样的中年男子,一生白衣,端坐在神座上,俯视着殿中一切;右侧是一位女性,挽着高高的发髻,鹅蛋脸,柳叶眉,表情祥和,仪态端庄神圣,也是坐像;中间则是一个四面用雕刻着祥瑞神兽、奇花异草围绕起来的竖立着的长方体“盒子”,“盒子”顶部被一顶八角宝盖盖的严严实实,仅在前方靠近脸部的位置有见方不足一尺的格子,透过格子,可以隐隐约约看见里面的神像的鼻子和嘴巴,以及赤红色的面部皮肤,其他什么则再也看不见了。
就在供桌正前方的那名中年男人念完了神咒,将一张符篆点燃的时候,那群小孩也刚好赶到,在庙门口正前方的院子最边缘处,呼啦一下全部跟随着大人跪倒在地,唯有一个少年还站立在后边,好奇的望着庙堂内正在进行的祭祀活动,忘记了下跪。
这个少年挽着宋朝特有的发冠,或许是很多天没有打理,又或许是刚刚跟其他少年打了一架,发冠显得非常凌乱,并且在发冠上也没有平常男子常戴的那种平式幞头。身上穿着深青色的粗布长袍,胳膊肘、袖口和屁股上都已经出现破损。而唯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稍显稚嫩但棱角分明,并且隐隐中带着些许刚毅的脸庞上滴溜溜的转个不停,好奇的望着周围一切。
在这名少年看来,此时门口跪拜的人群额头紧紧的贴着地面,没有一人敢发出声音,都在虔诚的跪拜着。天地间除了鼓声与铁环声,还有地上被捆绑着的公鸡偶尔因为不舒服挣扎鸣叫几声之外,四周再无一丝杂音,一片寂静,都在紧张的期待着某一重要时刻的来临。
虽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观看传神仪式了,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今天好像与往年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他又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