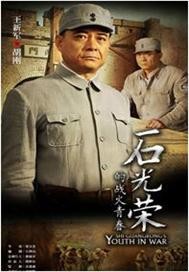左右各有一翼,每翼五千人,每一千人为一大队,排列五层,层层推进。每一百人为一分队,每十人为一小队,迂回包抄,十里之外,梁军斥候急射响箭向中军示警,警讯刚刚传到军中,晋军呼啸而来,距其目标已仅止五里路程,一时蹄声雷动,随风而来,梁军的运粮队伍顿时骚动起来。
右翼先锋是晋军的一县都尉叫尉迟芳,左翼先锋是另一县的都尉董藩,尉迟芳都尉见潞州城被围得水泄不通,一面向晋阳城求援,一面联络周边州县,出动轻骑,袭击梁军的粮队,尉迟芳披挂齐全,午只是一身轻便的黑色皮制铠甲,皮灰顶上红缨突突乱颢,犹如一簇火焰,掌中一杆长枪,随着越发逼近,他的枪已挟在肋下不,枪尖前指,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晋军竟然还敢袭扰?”
庞师古又惊又怒,正欲令人工前迎敌,只见左右两翼无数人马滚滚而来,较此前一路上所遭遇的七八次劫粮兵马何止多 了数倍,这才晓得此番敌人有些扎手,当即下令:“快,依托粮车,布三环套月阵。
来不及了,河东控制着上党这个产马之地,军马速甚快,梁军军依托粮车,三环阵刚具雏形,晋军已冲到近前,左翼领军的都尉董藩跨下战马撒开四蹄飞奔如箭,手中的钢刀高高举起,在凛冽的寒风中闪耀着嗜血的寒光。另一侧,尉迟芳紧攥手中长枪,长枪前指,铁蹄踏踏,犹如一阵旋风般卷过雪原,五十丈、四十丈、三十丈……
“绷绷绷绷……”一阵弓弦声响,刚刚扎下阵脚的梁军第一泼箭雨呼啸而去,尉迟芳一抖长枪,上护人下护马,拨打乱箭,速度一刻不停,在他后面,士兵们或以兵器拨打,或以取出了马盾,一蓬箭雨下去,倒也有些冲锋的士兵中曾落马,但是根本没有整个部队前进的步伐和速度,这一蓬仓促凌乱的背雨下去,就像一块石头抛进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只溅起一抹无关轻重的浪花。
另一侧,董藩的人马不像尉迟芳的人马都是制式武器,统一的训练,反应就是五花八门,各显其能了,有人蹬里蕺身,有人举盾迎箭,有人挥舞兵器拨打,有人狂呼乱叫悍不畏死地狂冲,还有人反应极快,早已取了弓来骑射反击,两路大军主将冲锋在前,无数英勇的武士呼啸其后,在溅起的雪雾之中,好象天兵天将一般冲杀过来。
董藩和尉迟芳充分发样骑兵的机动能力,迅速集结,迂回包抄,突击穿插,切割作战,漫说是庞师古在指挥一支梁军,就算是朱温在此,所部又又体力充沛,在这样的劣势下也唯有失败,顶多会让对方多付出些牺牲罢了。
这一路上,晋军假劫粮劫了七八次,把梁军拖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如今又在梁军最为懈怠的时候突然出现,九浅一深,直捣黄龙,梁军……终于高潮了,丢盔卸甲,任人宰割……
晋军十人一小队,仿佛一百枚锋利的箭簇,在运粮的长龙队伍中凿穿而过,左右两翼同时夹击,就像是咬合的锯齿,梁军的防御阵线全部告破,整个粮队被切割成了一截截的零碎。
第一波的冲锋就如波分浪涌,杀得梁军人仰马翻,紧接着,第二波打击接踵而来,晋军千人为一排,左右两有五列纵队,五次咬合之后,梁军成了被剁碎的肉馅。
最后一拨冲锋的骑兵交错而过的时候,第一拨冲杀过去的晋军已拨马回来,开始了下一轮的冲锋,长枪大戟,铁叉钢刀,利刃碰撞,火花四溅,横七竖八的车队中已抛下了无数的尸体,面对着这种根本无法抵抗的打击,梁军之中有的士兵不得不放弃了粮食,开始向雪原四处逃散,如此一来,更轻易成为对方的猎杀目标。
庞师古惊怒交加,舞动一杆长枪,恍若猛虎出柙一般左挡右杀,可是战阵之上哪有万人敌?一 人之力实在微乎其微,晋军十人一队的密集冲锋就像一波一波永无止歇的潮水般涌来,庞师古杀得汗流浃背,却觉得敌人似乎越杀越多 了。
他原本一尘不染的风采全然不见了,当他的汗水模糊了双眼。双臂酸软的已抬不起枪时,忽然发现,厮杀已经停止了,在他的周围,是一圈端坐马上,凶狠盯视着他的晋军军士,其中一人用嘲笑的眼神看着他,只轻轻一举刀,七余条套马索就齐齐飞上半空,向他头顶罩来。
“真他娘的有钱,这么多粮食。哇哈哈哈……,好多箭矢……”
董藩兴冲冲地检查着一辆辆大车,顺手一刀刺开一袋粮食,白花花的大米流淌出来,顺手接了一把,在阳光下,那一粒粒米就像珍珠一般晶莹剔透。再掀开一辆车子上的油毡布,只见里面是一匣匣的利箭,箭羽雪白,箭簇锋寒。垫在下边的却又是一件件的冬衣……
“有钱啊,真他娘!有钱啊。”董藩口水直流,立即吩咐道:“快,快快,每个人都尽量往马上装,能拿多少拿多少,剩下的全都烧了,快一点 !”
大雪弥漫,天地一片迷茫,呼啸的风雪扑打在脸上,刀子一般生痛,运粮的梁军步卒顶着风雪艰难地跋涉着。他们知道运往潞州城下的辎重已经被梁军劫掠多次了,他们知道围困潞州的袍泽们现在面对的最强大的敌人不是潞州城中的军队,也不是潞州城外不断袭扰他们的晋军,而是严寒的天气和粮食的匮乏。
他们一路上就不断地遭到晋军小股骑军的追击骚扰,不分骤夜,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晋军盯上,当他们被拖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可是……潞州他们必须得去,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把粮草和军需平安的送上前线去,围困潞州才变得不是一纸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