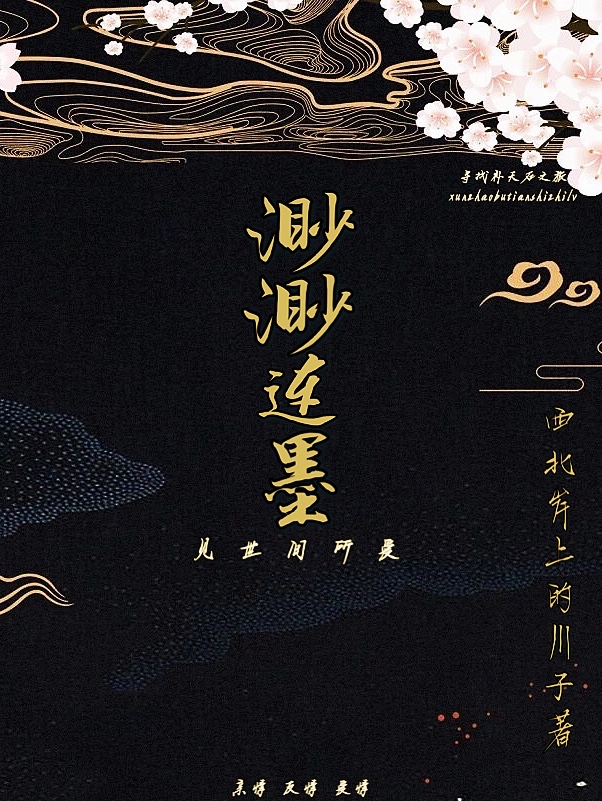青音正分析得热闹,丝毫未注意到穆苏与乐凌轩正迎面走来。我没有打断她,也未想过打断她。
穆苏还是那张看不出任何情绪的俊脸,仿佛在陈述着一个事实,依稀是些朝堂之事。“近日,自称曹国旧属的势力日益壮大,不日前方占领葵丘,眼下正迅速向周边城池扩张,我军顽抗御敌,两军僵持不下,君上欲调兵支援,将其一举清灭。”
“先君上在位之时,久未立储,众臣降于听政,君命皆以太宰达。先君病薨,太宰奉公子启以立,奉丧殡于大宫。然众臣皆知,朝中政事多由太宰把持,不知此次是何属意?”
“如你所言,现今太宰把持朝政,世子之位形同虚设,举国上下唯大司马统领众将士,为太宰忌惮。而此次陶丘之乱,则正是个借君命削弱司马手中实权,偷梁换柱的好机会,太宰一党必定有所行动。”
“当年君上亲自率师伐曹,执曹伯、司城归杀,一举灭曹,如今多年过去,旧日曹地早已归入我宋国版图,谁曾想竟会在此刻死灰复燃,其中恐另有蹊跷,恐非简单。既是请援,此战凶险,不论成败,我军必面临一场恶战。”乐凌轩与穆苏对视不言。
“对了,你最近感觉如何?可有不适?”
“无碍,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再清楚不过。只是雪婴,雪婴遇袭之事事出蹊跷,宿寒尚在查探。我近日鲜有时间顾及到她,府内发生了一些事有关雪婴,我有些担心她的情况,所以请你过来看看。”
“正好,我也打算瞧瞧她。”
“另则,还有一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看这医学上可作何解释。此前我曾将她一手养大的小狼带给她时,见她一脸恐慌,很是害怕。我想一个失忆的人却能记得一匹狼的凶悍,这与她昔日的观念很是不符,不知她这般是何缘故?”
乐凌轩眉头微蹙,也若有所思。“这倒有些奇怪。”
“那妙陶曾与我提起,说雪婴她自醒来以后便经常不自主的说起一些奇怪的词,有时候还念叨“明希”这个名字,她这般会不会是落水之前,看见了或者知道什么。”
我忽忆起前两日与穆苏在书房里的对话。
“妙陶说我现在刚刚恢复过来,不宜出府去,是你让她守着我的对不对?那等我好了,是不是便可以出去了?”
“现在府外不安全,你如今身体尚弱,我担心你的安危,让妙陶照顾你我也放心。”
“可是我已经完全好了。发生什么事了?府外为什么不安全?”
穆苏顿了顿,道:“眼下正值战乱之际,女孩子,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我朝身后妙陶瞥了一眼,默不作声。
乐凌轩闻声却双眉微蹙,忽然止声看过来,低吟唤道:“雪婴。”即刻支手打断了穆苏。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片羽毛飘落耳畔,却很温暖,竟有些让人着迷。
闻声,青音愣了愣,低声叫了声“公子”便没了声。
急急赶上来的妙陶来不及喘气,匆忙行礼:“公子,乐医师。”
穆苏随声看来,微微点头便径直问我道:“雪婴,怎么不好好休养,这是要去哪儿?"
声音依旧是淡淡的疏离。
“屋子里太闷,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府里几乎都逛遍了,所以便想出去走动走动。” 我觑了穆苏一眼,淡淡答道,有几分刻意回避的意思。
转眼看向一旁的乐凌轩,刻意搭话道:“是你啊?你叫……凌轩,乐凌轩对吧?”
自第一次见面后便再未见过他,险而模样都记太不清了,只有个烟水朦胧们模糊印象。
乐凌轩点点头,微笑着赞叹道:“你虽是失忆了,记性倒还很好。
他这话叫我不禁小得意了一番。目光偷偷滑过穆苏脸上,只见穆苏沉着脸瞥向一旁的青音和妙陶,两人连忙低头不语。
“怎么回事?”
青音顶着压力解释道:“公子,青音一回府便听说雪婴她落水之事,如今又失忆了,青音想这件事并不简单,所以自作主张,想带雪婴出府去看看以前去过的地方,我想或许对她恢复记忆有所帮助。还请公子将此事交给青音去查清楚,我不舍雪婴像现在一样什么也不知道的活着,我一定······”
穆苏一言不发,朝青音的方向轻飘飘又瞟了眼,但仅管如此,青音却像受了莫大的压迫,随即压低了一重头,不敢出声。
气氛突然变得古怪,我有些尴尬,连忙附和青音道:“是啊,青音姐姐说要带我去以前熟悉的地方走走,说不定我就记起来了呢,你不也答应过我会给我讲我生前的事吗。”
我看着穆苏,他也看向我,眼里流淌着我看不明白的东西,却莫名惊了我一身冷汗。
穆苏冷脸不语,周身骤然萦绕着重重寒气。
乐凌轩忙接过话头,道:“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雪婴失忆一事,事实上我也很难断定原因。她的脑部并未受创,周身又无外伤,用药汤也不能对症,让她多接触以前熟悉的事物,也有助于她恢复记忆。”
“这样吧,不如我带雪婴出府去一些她以前去过的地方,看看她的状况如何。”转眼看向面色凝重,一脸阴郁的穆苏。
穆苏终于不情不愿地从我身上挪开了眼,深深望了眼乐凌轩,又看了眼我,欲言又止。
乐凌轩像是了然会意了什么,按上穆苏肩头沉沉一握,依旧微笑着劝道:“我知道你顾忌什么,放心,我自会小心,不会出事。”
纵然一阵疑惑顿上心头,不知为何觉着,穆苏他似乎并不乐意我出府,然这些在乐凌轩答应带我出司徒府后便又很快被我抛之脑后。
不过自上次后我就再没见过乐凌轩,这次出府却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不免觉得心里有些不安,遂望向穆苏。
穆苏叮嘱了几句:“放心去吧,别玩太晚。我有些公事要处理,不能陪你一同去。”
我这才放下心来。
“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停住,看着身边来来往往许多人,立在人群中静静望着他。
乐凌轩发现我走散,遂回头朝我走来,只一声不吭地拉起我又继续朝前走。我挣了挣,没挣开,便觉着手上的禁锢愈发加深,被他紧紧握着挣脱不得。抬眼望见他冷若冰霜的侧颜,心头一凛,随即又听他答非所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乐凌轩,救我的医师。”刹那懊恼后我脱口而出,心道这难不成又是一个当我白痴的?
只听他不急不缓地又问道:“除开名字,你可还记得我是谁?”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
孰料他仿若未闻,脚下步子却渐渐放缓下来,拉着我顾自慢悠悠朝前走着。
见他久久不回应,我只好硬拽住他,一言不发地瞪回去。
他侧头看我,了然会意,忍不住轻笑问道:“你真想知道?”
我点点头。自然是想知道才会跟你在这儿死耗着。
说着,他已拉过我的手去。两手相触的一瞬,他掌心的温度一点点传度过来,竟让我觉着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它来得很亲切,很突然,又很温暖,脑子里依稀闪过一些零星片段,仿若早前被遗忘的东西正就要破土而出。
“这里原本住过一个女孩,跟你一般大小,不过早些年便不住了······”
“师父哥哥,那她后来怎么样了?”
“死了。”
他眉眼俱弯的对我轻笑道:“你若真想知道,我告诉你,你跟我来。”旋即紧了紧手中力道引我走。
我甩甩头,跟上他的步伐。
然而他牵着我一道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却并没有即刻告诉我的意思。
街头的叫卖声不绝如缕,擦肩而过的姑娘眉眼弯弯,笑得恬淡。很快,街道两旁的繁华吸引住我的目光,两侧的摊位上摆放着各色各样的物件,琳琅满目。我挣开他的手,奔到一个摆着各种样式泥人的摊位前,一眼便相中了众多泥人里有个着绿裳的胖娃娃。
“姑娘真有眼光,这个小泥娃娃甚是可爱,您要是喜欢我便给您包起来?”
我拿着胖娃娃瞧来瞧去,爱不释手。
“好啊。不用那么麻烦,我就这样拿着就好。”我欢喜地看着手中跟自己有几分相像的泥人儿,转身便要走,全然未顾身后那卖泥人儿的小贩慌急的模样。
小贩急忙上前拦住我,道: “哎哎,姑娘,您还没有付钱呢!”
“钱,是什么样子?可以让我看看吗?”
那小贩一愣,随即“嘿嘿”两声笑,眼光里闪烁着狡黠道:“姑娘您别开玩笑了,这世上怕是哪个垂髫小儿都是知道'钱'为何物的,姑娘您是在逗趣小人吗?”
“你喜欢?”温润的声音忽在头顶响起。
我回头望向他,郑重地点点头。
见他侧身与那小贩交涉,衣白如雪不染纤尘,“这个泥人怎么卖?”
那小贩快速将乐凌轩上下打量了一番,手指比出个‘二’来,眉开眼笑道:“二铢,二铢。”
乐凌轩不惊不扰,轻扬嘴角。“二铢?你是说用二铢让我买你这全部的泥人吗?”
那小贩刹那慌乱,随即换上一副面容,陪笑道:“不不不,是二铢一个泥人。”
“呵,你可真会做生意!也罢,这个泥人我要了。”乐凌轩丢下两个铜片,便带我走。
路上我越想越混沌,越想越感慨万千,觉着纵使最近我身体终于恢复了过来,并且感觉脑子也好使了不少,然而今次被拉出来溜上一溜,便好似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我终于忍不住叫住乐凌轩,“虽然我在府中的用度不愁,但我没见过真真实实的钱,你说,那两个东西可以换那里所有的泥人,可为什么我们只要一个?”不然我即便腾出两只手加张嘴,也还是可以多拿几个的。
他却微笑着看着我,缓缓说道:“心爱的东西一个就足够了,哪里能贪多呢!”说着顺手朝我鼻尖刮了一下子。
我惊于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双颊"轰”的烧了起来,后颈一股热息突然上窜,竟是与上次惶急间‘熊抱’穆苏后的感觉一般,诡异又尴尬。
他望着天边,天色渐暗,幽幽叹道:“如若是心爱之物,即便用再大的代价去换,也是值得的。”
他不急不缓认真向我解释着,那一刻,似乎有些暖暖的东西从心间流淌而过。耳边的声音温润的如同渠水,眼前的笑颜淡如水墨,我心下突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倘若可以牵着这样一个人的手,就这么一直走到落日尽头,就好了。眼光飘过他的侧颜,唇角已没了先前的笑容,安静得像是天边淡淡的日光,又恰是霜风骤降远方孤落的白菊,寂寥得徒剩下满地殇。
那天,他带我走过许多地方,陪我看过许多从前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看静女其姝,贻管桥头;一起赏霜菊凋零,黄花漫天;一起听茶楼说书,画楼丝竹。纵然我依旧只有熟悉的陌生感,零星的记忆有些混乱不清。
可就是这样,我真的同他从寒日初阳走到了日落山河。
“我今天好开心哪,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呢!你呢,你开心吗?”我们坐在商丘最高的楼阁的屋顶上,他说,从那里看日落最美。
“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他望着远方的天边,眼里迷离,我能感觉到那里面隐隐流动着的淡淡忧伤。
“如果你肯带我出来,我们以后都还可以有许多个像今天一样开心的日子啊。”我笑着对他说道,刹那间仿佛对他放下了所有防备,那样自然,那样自然地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乐。
一阵风吹过,带起我散出来的碎发,撩在脸上痒痒的,我伸手挠了挠,却见他突然转过头极为严肃的看着我,郑重地说道:“雪婴,既然现在你这么快乐,不要过去了,可以吗?”
我有些惊疑,仔细想了想,以为他是在担心治不好我,便笑同他说道:“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过去吧?虽然现在好像也挺好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过去的自己,想知道过去的人和事,也、也很想知道过去我脑海里的你和······妙陶。”还有,关于雪婴的真正死因和一切,我也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顿了顿,见他目不转睛的看着我,继而转头望向远处的天边。“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不能治好我,其实也无所谓,我知道这事儿急不来,总有一天会记起来嘛!你真的不用担心。”不知怎的,我单纯地以为他是担心我,那是一种奇怪的直觉。第一次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好像,竟是因为一个人。
“如果过去是伤痛的,是酸苦的呢?还是想记起来吗?”他迫切的声音忽然透着浓浓的悲伤与寂寥。
见他紧锁在眉头间的那团忧愁,我迟疑不定,想要为他抚平,却终究也未伸出手。
我一时语塞,这个问题倒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抬头尴尬的笑了笑,“总该还是会有一些快乐的记忆吧!等我找回那些快乐的记忆后,我会记住它们,便不会再伤痛了。不是吗?”我朝他笑了笑,看向天边孤风残叶,那样萧瑟。
其实,我也有过犹豫,过去会是怎样的,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不要记起来。可是要搞清楚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必须想起以前的事,想起雪婴的一切,或者说,我的一切。
那个叫做雪婴的女孩,身上究竟有隐藏着怎样的过去,为什么我又会出现在这里,而我到底来自哪里?如果肉体里寄住着一只灵魂,那这只灵魂是属于谁?我?还是她?
他久久凝视着我,良久后,像是做了一个很难绝断的选择。“雪婴,如果哪一天你记起来了,你要记得,我、我是······你的哥哥,最疼爱你的哥哥。就算哪天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了,我也会陪在你的身边,像这风,像这霞光,一直在你的身边。”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捧着我的脸痴痴望着,仿佛时间都静止在了那一刻。
我靠在他的肩上,等着看远方的夕阳慢慢落下山头。谁都不知道,悄悄躲在周围的乌云早就预谋好了—切。阳光渐渐消失在了大地上,天色暗了许多,秋风渐起,漫天枯叶,天空突然飘起了细雨。街上的叫卖宛转,冷冷清清,不复繁荣。深巷里的青石板路一点点被润湿,湿滑的青苔沾湿行人的布履。
“哥哥,你看他们,要回家了。”
“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你也会有。”
“哥,你说你是我哥,那咱们的家在哪儿啊?那儿,那儿,还是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