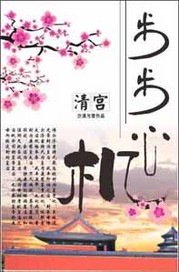翌日醒来已是巳时。
脑子方清醒些,便纠结起此前发生在自己身上奇怪的事,现在摆在我眼前的三大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们说的那些关于我的事情,当真如此吗。不过到底因为失忆不记得以前的事多,刚记着现在的事少,纠结着纠结着也就没大放心上了。
妙陶一边帮我更衣洗漱,一边提醒我道:“主人,方才公子来过了。公子见主人尚歇着便先回了,还嘱咐我不要吵着了你。主人大病未愈不宜走动,待主人朝食完毕后,妙陶请托绮罗姐姐替主人向公子报个平安吧。”
“嗯。”我抬了抬下颌,由她替我整理衣裳。对于目前的生活方式等等一切,我仍旧是一头雾水。
听起来那个叫穆苏的男人地位非凡,据妙陶说他是宋君过继的养子,现任宋国大司徒,掌土地之图和人民之数,佐君政务。所以我现在所处之地,也便正是她口中所说的那个宋国,一个处于乱世之中且即将迎来又一个乱世的诸侯国之一。
宋国原承旧商一脉,由周天子亲封公爵,地位殊荣。然王室衰微,天子不过空有天下共主的名号,事实上各诸侯国间早已烽火四起,群雄争霸,纷争不断。宋国虽曾是霸主之一,只不过寥寥几年光景,人事更迭,强主后起。乱世中人只会在相竞相制下生出更多欲望,天下也只会在国国吞并下促生出更多的强者,剩下的不过是这较量中终会成为牺牲品的大多数者。所幸这个方经过战火渴求安宁的宋国,在弭兵之盟后的几十年间倒暂得了一段难得的安平日子。
妙陶替我更衣完毕,又开始梳妆。粉黛薄施,简单的发髻拢上头顶,人也精神不少。柳眉杏眼,小巧挺拔的鼻子下一张红润了不少的秀唇,衬在雪白的皮肤下,犹如万顷皑雪中若隐若现的一点梅红,不过好好的一张面皮上,却是在左额处生着块怎么也掩不住的桃花胎记。
抚着额上的胎记,那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派陌生,所以除了觉着不那么好看以外也便无甚感觉。脑子里脩忽闪过些零星片段,我眯了眯眼,头又隐隐作痛起来,再欲深想,便愈发觉着头痛难耐,怎么也记不起来。
我深吸了口气,试图缓解心头的不适感。“妙陶,那穆苏,我与他是何干系?我为何在此地?”
“公子、公子与主人关系甚好。”妙陶脆生生答道,又补充说:“主人是公子带回府的,听闻主人曾救过公子的命,所以……”
“所以我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吗?”
原来是这渊源!看来我还有点能耐,回头培养培养指不定还能晋升救世主了。
据妙陶说,原本我也是个孤女,彼时住在遥北不咸山的千日谷中,与养我的阿翁相依为命十几载。阿翁会医术,耳濡目染之下我也便学了些,勉强识得百草。那日恰逢下过一场桃花雪,山路本就难走,我便上山去替阿翁采药。也是在那一日,一切事都发生得刚刚好,我遇上了受伤的穆苏。那时我初遇穆苏时,他一身长袍皆被血水染透,气息微弱得几乎就要死掉了。我救了他,并且带他回千日谷里疗伤,可后来伤好,他便要下山了。当时我玩心甚重,又从未下过山,见过外面的世界,一道跟着他下山后,我曾遇到过许多人和事,可也很快发现自己与外面格格不入。所幸因为我遇上穆苏,穆苏大约念及救命之情,收留了我,顺带才有后来容我帮助妙陶的事。
其实,真正于妙陶有恩之人应是穆苏才对。
“妙陶,你说要是我真的一辈子也记不起来了怎么办?”
那丫头听我这般说,霎时犹如那黄河之水泛滥,一双大眼睛像两汪泉水一样,登时蓄满了池子,瘪着嘴哭道:“不会的主人,乐医师会有办法治好你的,公子也会想办法的,总是会记起来的!”
我张口哑言,想了半天也终不知道该拣些什么话,便道:“没关系,要是记不起来,你会陪着我吧?你有吃便给我一口吃,我有吃也给你,有地儿睡就成了!嗯?”我就势靠向妙陶的手臂蹭了蹭。
“啊?”妙陶一个楞儿样呆呆地望着我,不明所以的咬唇急问道:“主人打算离开司徒府吗?”
我知道,我又说错了话。
这段时期,我时常觉得有什么东西被遗忘在了脑子里,却总是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隐约感觉自己好像并不是这里的人,但却又好似与这里有着很深的渊源一样摆脱不掉,那真是一种无法言语的诡异感觉。我想这些话万万不能再给妙陶听着,只怕会吓着她,便只得自己想想作罢。或许唯一能解开疑惑的办法,便是赶快记起这一切来,如此来去何从便都有了选择。
终于收拾好我,妙陶转身从案上端过一碗黑漆漆的汤药到我面前。我一嗅到那味儿,顿然觉着恶心反胃得紧,连忙撇开药碗嫌弃地瞪眼,推脱道:“这会儿挺晚的了,一会并着就午饭一块吃吧。”
“主人听话,医师嘱咐过了,这贴汤药要进食前服下,药效才会更好。”妙陶说着,又朝前递了递。
“我觉着我今天精神好了许多,身子也好了不少······”虽然偶尔会有些小腹疼痛,但相比喝药还算能接受。“我不要再喝那个乌漆墨黑的东西了。”
“主人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喝个药也能愁成这样儿的。”妙陶嗤笑着又向前送了送。
“你自个儿喝喝就知道有多难喝了,昨儿个灌了三大碗还不够么?”
我捏着鼻子掉头速遁,由得她这个小尾巴在身后追着满屋跑。
“乐医师嘱咐说,这药每日需服用三次才可,主人现在的身子这么弱,得好好养着才行,可别落下了病根儿才好,麻婶儿说了,这女孩子落下了病根儿可是很难再养好!”她说着顿了顿,语调也忽的落了几分,变得有些吞吐。“况且,主子想记起来,就要按时喝药啊。这才过了巳时不久,正好赶上朝食,主人,哎呀主人别躲了,仔细着凉了······”
“乐医师乐医师,他是你什么人啊,你怎么就那么听他的话啊!我还是不是你主人啊?”
“主人说得对,妙陶都听。但乐医师是王宫医术最好的医师,也是我们宋国最厉害的医师,妙陶可以不听他的话,可是主人你得听啊!”
我经不住低咒这该死的最好医师,他这一言便成了圣旨金言了。
可转念一想,又觉着哪里不对劲。朝食?医师?
我一个急刹车险些没停住,害得身后的妙陶也措手不及,差点打翻药碗。
“什么朝食跟医师?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那么陌生。你们都这么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