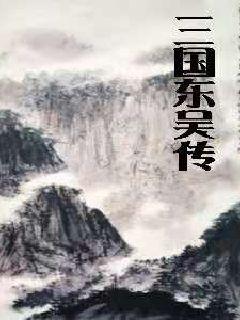“面相先生出摊,招牌写着三不要钱。一,命后孤不要钱。二,乞丐相不要钱。三,将死之人不要钱。”太公一手端着水烟斗,一手拿着麻竿,自言自语从外面进来。看似自言自语,实际上声音大得满屋子都能听见。屋内一间堂屋,一间厨房,两间卧室。堂屋和厨房之间的门框上挂着一盏煤油灯,门框上从来就没装过门。煤油灯是用废弃玻璃罐头瓶子做的,光线调得特别微弱,屋里只能免强看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面孔和表情。
太公习惯的坐到他每天晚上坐的老位置上——我奶奶亲手编的一个草墩。慢吞吞的在火塘里点燃麻竿,在水烟斗里填上一锅烟叶,咕噜咕噜深吸了一口。“……客官,敢快回家准备后事,把钱财账目交给家人,你过不了明日丑时……你这命不值钱,不是我不收钱。”说着又是慢不打紧的吹烟灰、填烟叶。他讲故事从来是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也从不讲究怎样引出话题,想讲什么故事就从门外一个人一路高声讲进来。这时侯,爸爸在一旁等不及了,说:“后来说准了没?”“如果他不去算这个命他就不会死,正是他在算这个命时算命先生的一番话被他老婆的奸夫听到了。所以呀,被他老婆联合奸夫在当晚子时把他谋害了。你说准吧!”
太公是我爷爷的小叔,本名葛大富。认识他的人都称他富爹。在我们家人亲戚中辈份最高,年纪最大——八十多岁了。因年轻时他爱人——我太婆没生育能力,没生得一儿半女,祖上分给他的房子和别的兄弟一样多,就因为多了几间房子所以解放后被打成地主。后来留下一间半房子给他们,多余的都无偿划给了外姓人。生产队里的脏活累活都由太公夫妇二人全包了。那年夏天,正值“双抢”季节——抢收早稻立即抢种晚稻,生产队长夏满斗命令太公夫妇二人必须一天收割二亩水稻,否则就会被绳子绑起来开批斗会。
那天正值七月中旬,入了头伏。天刚蒙蒙亮,太公为了尽量让我太婆少受一点苦,还没吃早饭就一个人偷偷下地开始收割水稻了。太阳一出来,气温就上升到了三十多度,稻子巳经割倒了一大片。稻草上的灰尘从鼻孔里吸入,感觉肺里一阵阵刺痛。太婆带来了水和煮熟的红薯,为了赶时间,特意多带了两个,中午准备不回家吃饭了。中午时分,太阳象火一样在头顶烤着,脚下象蒸笼一样冒着热气。他们夫妇二人拼命一样踏着打谷机转动,机器发出一声声嘶心裂肺的嚎叫。汗水和着灰尘挡住了视线,用手一刮大把大把的甩在地上。太公每当想停下来休息一会时,眼前又浮現出自己和爱人双手被反绑在背上,头戴高尖报纸帽,被人压着双肩跪在台上挨批的情景。想到此处,脚下踏机器的速度猛地又快了起来,刚才打谷机发出的象一声声的**突然又象一只落水的猛兽,发出最后的挣扎和呼救。我太婆叫保佑,从小家境不错,就没受过这种苦,看到自己的老公这样卖力的爱护自己,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敢用眼睛直视老公的脸,任凭泪水夹着汗水吧嗒吧嗒往下掉,努力的不让老公发现。
渐渐的觉得小腹部一阵阵绞痛,太公咬紧牙关,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保佑在一旁发现了情况不对,赶忙停下了打谷机,用毛巾帮他擦去脸上的汗水,这才知道太公额头上由热汗变成了冷汗。
“不要紧,老毛病犯了。”太公坐在地上,双手捂着下身,“保佑,帮我去叫先知来,他对我的病很熟悉。”先知就是我爸爸,大队的赤脚医生。
太婆去大队卫生室找我爸,却惊动了生产队长夏满斗。夏满斗急怱怱跑到田里来指着太公大骂:“恶霸地主葛大富,欺上瞒下,投机取巧,装病偷懒。”双手拉着太公的脚,从稻田里一直倒拖到了晒谷场上——足有两百米。“我管你大富还是大贵,敢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招,老子拖死你!”夏满斗一边拖,嘴里一边骂骂咧咧。等把人拖到晒谷场,太公已昏死过去,我爸爸赶来经检查是小肠下垂,下身肿得皮球一样。爸爸说他再来晚一点太公就没命了。太婆保佑实在受不了折磨就跳到门前池塘里自尽了——她那年二十五岁。当时我们村里有一户最贫困的村民叫旺田,他老婆叫细花,是村里最光荣的贫农。太公平日里和他们无怨无仇,也没有什么感情交集。太婆被人发现投塘自尽时,已经肚子涨得老高,早已没了生命迹象。被人捞起来放在门前晒谷场上,细花双脚在太婆遗体上一踩一跳,大声骂道:“该死的地主婆。”还用竹筛子筛一些油菜籽在池塘里,传说阴魂到地府以后,阎王爷要他把油菜籽一粒一粒从池塘里捞起来才可以投胎转世。细花的意思就是要让她永世不得投胎。
太公从来不讲这些,这是我三十多年后才听我母亲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