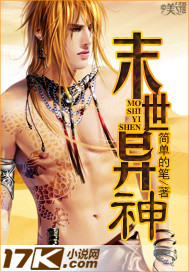陷井太深,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那么长的藤蔓。时间紧迫,分分秒秒都在生死边缘。
聂印想不到那么多,只想走捷径救他的王妃。他多希望惹祸精呼一声救命,或者对他表示出一分依恋。可她只是一声声催促他离开,一声声绝情地赶他走。
危险来时各顾各!
他相信,如果掉下去的是他,她也一定不会抛下他,独自一个人逃命。
机灵的猴子眨巴眨巴着眼睛,听从聂印的指挥,分成两列排好队,等待命令。
聂印用不算太长的藤蔓,一头拴在树上,另一头绑在猴子的身上,后面的猴子灵巧地抓住前面猴子的腿,一个接一个,形成一列猴梯。另一列如法炮制。
“惹祸精,我的猴儿朋友们来救你啦!”聂印的声音轻快起来,完全忽略了越掉越近的箭。
邱寒渡抬头一望,只见一个个鬼精灵的猴儿们如耍杂技般翻腾叠加,就那么做成猴梯渐渐延伸至她的眼前。
她的眼眶一热,少年终是没把她扔下。尽管她心里骂了他一万次,可是仍旧激动得有些忘我。
他说,不要忘了,你是我的王妃。
他说,不要忘了,我是你的相公。
那声音和音调,仿如烙印烙在她心上,烫得她的心生疼生疼,却暖和,暖和得连脚底被竹尖扎刺都无所谓了。
猴儿们吱吱喳喳,仿佛在催促她快点上去。
邱寒渡还真是有点心虚,要是猴儿们承受不住她的重量,掉下陷井,只有死路一条。想到这个,她心里一阵恶寒。
设计者,心思多么狠毒。
幸好,掉下来的是她,而不是聂印。据她了解,聂印的武功和轻功都太平常,他只是对用药出神入化。可是在陷井里,根本无他的用武之地。
一切,都直指聂印。
一切,都直指真龙天子。
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聂印的习惯和他的短处来设计的天罗地网,让他没有活路可逃。
她忽然明白为什么初进山林便发现了毒药,那时他们都以为,是有人捕杀猎物。其实,真正的猎物是聂印。之前用毒药捕杀动物,只是因为怕聂印真有与动物沟通的能力,进行了一次剿杀。
传说一切生灵都听命于聂印,他是山林之王。
聂印在选妃的宴会上,为了让太后支持邱寒渡当王妃,也曾小露了一手使唤动物的本领。
只是,山林终究深不可测,又岂是一场围剿就能杀光所有的动物?
杀不死生灵,山林之王又岂会死?
邱寒渡的心一横,双手抠住沿壁,指甲深深陷进泥土里,再猛提一口气,尽量减轻身子的压力踩在猴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攀爬。
猴儿们吱吱喳喳的叫声,渐渐整齐划一,发出的频率基本相同。
无比响亮,无比震憾。
那像是艄公的号子,或大或小,起起伏伏,仿佛世间最好听的歌声。
邱寒渡从来没想过,原来动物真的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甚至,动物的思想和感情,比人类真挚得多。
心潮起伏。
邱寒渡人冷心硬,很少会被什么事儿感动。此刻,她的心灵深处,被某种柔软的情绪挑痛。她曾经是一个见了兔子受伤,都不会停下来看一眼的人。
她只知道世界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在于权利和金钱。
蓦然,猴儿们的叫声猛地混乱。不知什么原因,一个猴儿的手滑了,就那么掉了一串猴儿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邱寒渡双腿灵巧地夹紧一只猴子,迅速仰身向后一倒,紧紧抓住掉下去的猴子。
此刻,情况更加危急。
邱寒渡头朝下,双脚缠紧一只猴子,手里却拉着一串猴子。她的力气渐渐弱下去,她脚上缠紧的猴子也深感吃力。
此时,只要她手一放,就得救了。可是她不,死也不。
下面是死亡的地狱,就算死,她也应该是最先的那一个。
一只箭从聂印头顶上嗖地飞过去,他全然不顾,只是趴在井口,大声呜噜着邱寒渡听不懂的话,最后,才是跟邱寒渡说的:“惹祸精,别怕。你死了,我下来陪你。”
邱寒渡心里猛地一股热流澎湃着汹涌的热潮,袭卷着,拍打着,淹没着她。她又是猛提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上的猴子往上一送。
猴儿何等机灵,就那么一送之间,它便再次抓紧了前面伙伴的腿。众猴均发出赞叹欢欣的吱喳声儿。
邱寒渡大汗淋漓,仿佛虚脱一般,趴在一只猴子的背上。片刻,她再次往上攀登。
彼时,最下面的猴子,意识到不能像刚才那么傻,非得等人家爬上去才动。这会子,一个个儿的,鬼精鬼精,只要被当成梯子踩过的,就自动往上窜。比邱寒渡窜得快多了。
只是,上面也并不安全。箭在上空飞来飞去,吓得猴儿们吐着舌头做怪样儿。
邱寒渡终于一步一步,离聂印近了,更近了。
“惹祸精!”聂印趴在井口,一张俊脸薄染笑容,伸手拉她:“我不是在吗?你哭什么?”
邱寒渡将手放入他的掌心。手心贴手心,灼热得快将彼此的心都烫化了。她小心翼翼地探出井口,爬了上来,匍匐着。
四目相对,百感交集。
邱寒渡变成了一个爱哭的女人,莫名,泪流满面:“风……好大……”她使劲擦着眼睛,找着拙劣的借口。
聂印宠溺地弹了一指在她脑门儿上,全然无视危险的境地。
猴儿们都上来了,毫发无损。一阵欢呼,还吐舌头,做怪样,有的翻筋斗,浑然不觉此处有多危险。那只被邱寒渡救过的猴儿,还蹦过来亲了一下她的脸。
仿佛一个瑰丽的童话。
聂印再次吹了一声口哨,那是撤退的号令。猴儿们不敢留恋,便隐入密林中。
远处惨叫声声,敌人正被动物袭击。只是,他们一定人员众多,渐渐收紧包围圈。箭,越来越密地射向聂印和邱寒渡。
两人抱着就地一滚,躲到一棵大树下。聂印二话不说,掰起邱寒渡的脚来看。
邱寒渡将眼泪擦干,再次一脸冷漠之色,仿佛刚才那个易哭的女人不是她。她脱下军靴,穿着白色布袜的脚,已全是鲜红之色。
血水,一滴一滴渗进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