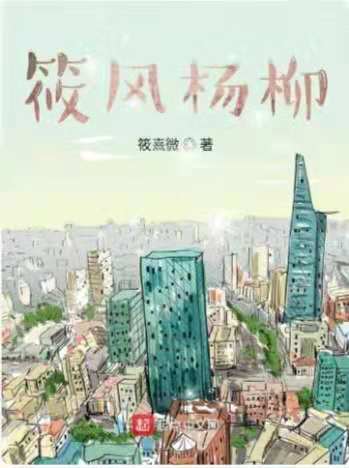“我真的已经无法承受痛苦、也无法忍受对他的那种思念之苦了,无法摆脱自己失魂落魄的状态,又一夜过去了,外面已经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也就是从殡仪馆回来后的第三天早晨,我最终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他,我付出生命也不觉得过分,因为我的爱已经被他带走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我换上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穿的那套婚纱,吃下了一整瓶的安眠药之后,抱着他的照片,躺在了我们的床上平静的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一样,在同一个空间里了,我就可以找得到他了。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医院里了。”莫桐说道。
“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还有我的堂妹都在病房里,我看着他们,再次流出了眼泪,但是我没有说话,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办法理解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堂妹虽然被我赶走了,但是她根本没回家,而是在门外陪了我两天两夜,每隔几个小时就轻轻地打开门看看我的状态,我当时因为心绪太乱,精神状态恍惚,所以竟然没有察觉。幸亏是她发现得及时,否则我已经死了。”莫桐拿着万宝路的烟盒,在手里上下翻飞,就如同是一个带着记忆色彩的风车在旋转。
“生命是珍贵的,能活着是一种幸福,而且在天堂里的他也一定希望您能振作起来,能够抛开痛苦,开心地活下去,那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否则,您连怀念他的资格都没有了!”我说道。
“你说的没错,一旦我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我连怀念他的资格都没有了!我出院之后,没有再回去我和他的那个家,而是被我的父母带回到了他们的家,是强制的!因为他们怕我再出问题。后来,他们带我去了一位熟悉的心理医生那里,他和我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的精神受到了刺激,有抑郁症的早期症状了,他建议我能够休养一阵子,并且接受心理治疗。”莫桐说道。
“我的状态的确也不适合做任何工作,我的脑海中每天几乎不知道要想起他多少次,根本不可能去构思什么设计方案。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只是觉得自己无法从失去爱人的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之前,我在父母的陪伴下去了我工作的公司,我向老板提出辞职,他也知道我的家里出的事情,还有我的精神状态,但是他还是提出要挽留我,并且说可以给我时间去治疗和恢复,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但是还是决定离开这家公司。”莫桐说道。
“经过了六个月的治疗,我的状态相对之前好些了,就再次开始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做了两份兼职,一份工作是做一家私立学校的基础美术课老师,另一份工作是为一家杂志社做摄影师。做兼职的那段时间,我回到服装学院找到我以前的老师,了解了一下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时装设计与技术专业的招生要求,之后就开始了备考,并且还要准备自己的作品集。”莫桐说道。
“九五年,我一边工作一边专心的备考,准备了一整年,顺利的通过了考试,九六年九月,我如愿以偿的到伦敦时装学院深造!那个时候,想要在这方面继续深造只能去国外,而且换个环境对我来说也有好处。我在伦敦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段时光,暂时让我远离了失去爱人的痛苦,我的生活被每天的课程填充了,阴影开始逐渐的散去。但是我的心里清楚,完全恢复自我是没有可能的了!”莫桐说道。
“我的第二任丈夫,就是我在伦敦国际时装周上认识的。他是一名记者兼摄影助理,父母是定居日本的华侨商人,他那时刚刚从早稻田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东京的一家比较有名气的杂志社工作。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日本人,因为他与同行的人聊天时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认识之后才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华人,只不过是熟练的掌握了日语、英语和汉语罢了。”莫桐说道。
“我和他在伦敦见面的次数只有三次,因为时装周结束之后,他就得回东京去了。见面的那几次都是他打来电话约我到舰队街145号的柴郡奇斯酒吧,之所以选在那里见面,原因是他说他喜欢那里的非自然光线,真是个匪夷所思的理由。每次见面彼此客客气气的聊聊天,话题全都是一些关于英国流行时尚方面的话题,多半是他提问,我来回答,他的职业让我觉得,那与其说是约会,倒不如说是即兴采访。所以,我那时并没有对这样的会面有什么更深的猜想,时装周一结束,他就回了东京。我还是重复着我的生活,每天上课,下课,每周末还兼职做一家培训机构的汉语会话老师。”莫桐说道。
“如果不是一个月之后突然收到他的来信,我对他的‘采访’这件事情恐怕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在来信里说,自从在酒吧聊过之后,我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回到东京之后,仍然无法忘记,他在请求,我是否可以同意与他交往。我当时看了他的信之后,觉得他的想法和这样的举动蛮幼稚的,不用说我们只见过那么几次面,单单是伦敦与东京上的时空距离就很成问题。我认为他的想法太‘年轻化’、 ‘欠考虑’、 ‘冲动’,而且实际上他比我小了四岁,无论从哪一点上来说,我们都不合适。我回信告诉他说,我们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之间的了解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距离又这么远,从各个角度看都没有什么可能性,所以劝他打消念头,认真选择自己的情感对象,比我适合他的人一定多得是,最后我强调,我不仅是个结过婚的女人,而且还是个经历过痛苦的女人。”莫桐说道。
“回信的内容就这些,尽可能用简洁的文字和冷淡的语气,以期熄灭他的想法。我自己的考虑是,我要让自己的生活平静下来,不想再经历任何的波折,我想自己要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事业,对于婚姻和情感不再有什么期待了。我很难相信自己可以再次投入情感去面对另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准备去这样做。在我给他回信之后的第二个月,他竟然从东京飞到了伦敦来和我当面谈,并且告诉我说自己无论怎样都阻止不了自己这么做。”莫桐说道。
“他的这个举动的确让我惊呆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下了决心要和我交往,也许他真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还也许就是他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毕竟我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上也不是‘漂亮女孩’的年纪。我找不到可以让他确认我‘漂亮’的依据,或者说我的外表会有什么可以吸引他的地方!”
莫桐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她的语气如同是把“漂亮”这个词加上了引号,而加了引号的这个词,并不一定是否定或者反语,但也不能作为肯定。我从其语气中揣摩具体的含义,从她表述的中来看,“漂亮”这个词的语气比前面的话语的语气要加重了一些,她眼望着咖啡杯里的勺子柄,语调略有起伏,仿佛是有意与无意的混合物。而在现在的我看来,那个时候的莫桐,大概仍旧是漂亮的,并不如从她的语气上所表现出的含义中的那种模糊式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