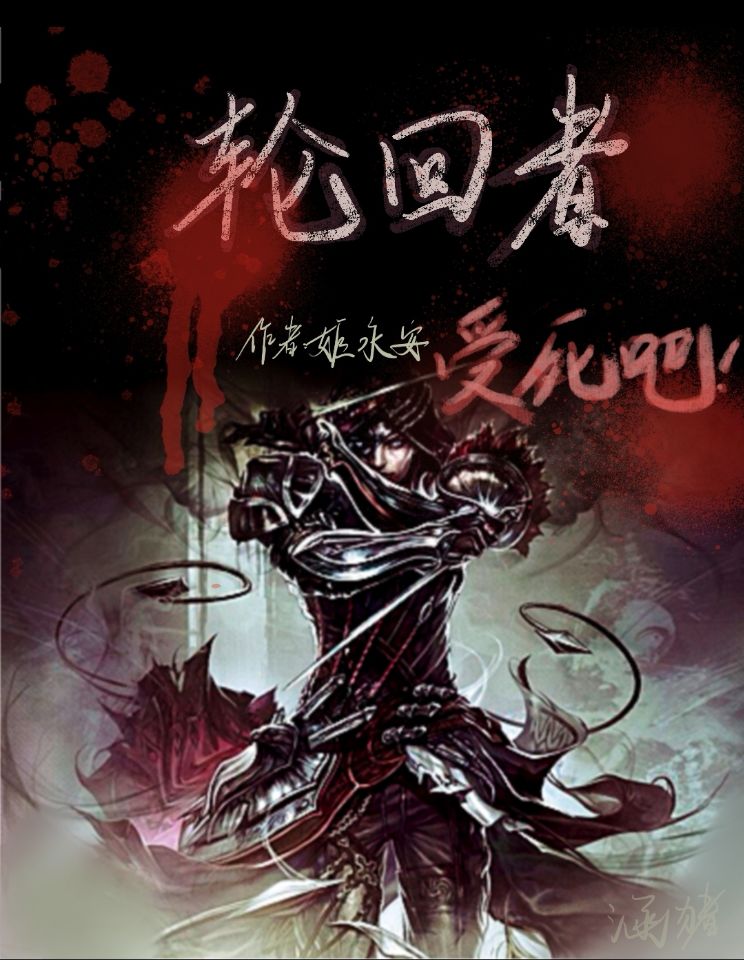回到学校,便面临着繁琐的休学注销和申请博士答辩等一系列的程序手续,真的是狗屎做鞭子——又臭又长。
不过日子倒是充实又平静,杨娃娃和李悟都没有来找过我,甚至连我家这边,也就只有我老妈打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家,被我搪塞了过去。而其他人就彻底没有什么消息了。
连王子和阿寻都没有露过面,要不是我打过几次电话,问了问他们的情况,我都要以为他们被杨子的人带走了。
毕业答辩除了一些材料需要准备外,我也不需要修改早就写好的论文,所以其他的时间,我都呆在了图书馆,梳理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
读了这么久的书,即便我不是纯正的唯物主义者,也更相信科学的力量,如果说我去海底城那个地方走了一遭便治好了绝症,那带出了阿寻,不就相当于给了现代医学一张免死金牌,重病的人一批一批抱着阿寻的大腿去那里走一回,都可以重新迎接新生命了吗?
虽然场面想想还挺可乐,但是理论上也是不可行的。
那么杨子说的话大概率就是真的,我和王子是一个大计划里的两枚棋子,被欺骗得了绝症并被引导去了海底城。
至于为什么选择王子,现在我只能认为是巧合,而选择我则是因为杨家跟李家的密切关系,使他们相信了李老爷子的话,而李老爷子可能也跟我家有某种关系,所以他们这三家达成了某种协议,甚至代价是可能牺牲我的生命,我家里的人也同意了。
李老爷子的动机现在我暂时只能猜测是因为收到了姬家的地图,或者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引诱他。
但是最关键的几环都很难解开,首先是李老爷子已经死了,无法问出这三家的协议和我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从目前来看,所谓的姬家势力太强大,甚至连李悟都不能查出一星半点的线索;第三是很难从我家的大佬和杨子那里套出真话。
我叹了口气,即便梳理一遍,事情也杂乱地找不到最初的线头,现在只能确定他们各方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阿寻的帮助,所以我还算是掌握着解开一切谜团的钥匙。
只不过我转念一想,觉得其实我大可不必追问到底,人生糊涂着过一过,到最后也挺快乐,想得太通透了也许才会有很多清醒的痛苦。
正在我纠结于这种没有正确答案的哲学问题时,突然一通电话打断了我飘忽的思绪。
我看了看手机,来电显示居然是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甚至很少碰面,常年呆在部队的三叔,一想到我三叔严肃的表情,我有点紧张,清了清嗓子接通了电话,还没等我开口,我三叔率先说话,嗓音带着浓重的哀伤,“小霍,明天回老宅,你爷爷去世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只剩我举着手机愣在当场。
尽管我最近几天确实被杨娃娃的话影响到了思绪,对他们有诸多抱怨,耍着小性子故意没有回家。
但我们毕竟还是家人,我还计划着过两天就回家看看,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没有见到我爷爷的机会,明明在我印象里,他老人家身子骨非常硬朗。
我半晌才反应过来,内心悲痛地消化着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我默默离开了图书馆,在校园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无声的眼泪止也止不住,突然就明白了人们常说的“家不是一个你想回就能回去的地方,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操场的台阶上,望着即将坠落的夕阳,眼前闪过了一幕幕我爷爷照顾我的往事,悲更从心来,我蹲在那里大哭着,释放我的情绪。
哭了很久,我随意地擦了擦眼泪,径自往家走,我现在必须回去跟爷爷见最后一面。
以前我老妈总是跟我唠叨,人死了以后,他的亲人都要哭泣,是因为死去的人,他们的魂魄还滞留在人间,他听到亲人的哭泣,才能明确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人真诚实意地爱着他,才能了无牵挂。
此刻我很相信我老妈的话,心里急着赶回去,想告诉老爷子的灵魂,我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也可以把家人照顾好,还有我真的很爱他很爱我的家人。去他喵的唯物主义,涉及感情只能唯心。
我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宅,到了门口,看到挂起的白幡,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下来。刚进家门,便听到我家里人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尤其是我老妈的悲声。
我走进大厅,我爷爷的灵堂就设在那里,我爸爸和几位叔叔神色悲恸,低头烧着纸,我老妈看我出现,抹了抹眼泪,站起来拉着我去隔壁的房子换衣服,顺便叮嘱我,“小霍,你爸爸和你几位叔叔商量,等你爷爷下葬以后,有些话要对你说。现在先去守灵吧。”
我忍着眼泪,点点头,给她擦了擦眼泪,扶着她回到灵堂,陪着我爸妈和几位叔叔守灵。
停灵期间,李悟、杨娃娃和王子他们都来吊唁过,不知是不是李悟把消息告诉他们的。
葬礼很顺利地结束了,最后的骨灰撒向了大海,据说是按照我爷爷死之前最后一刻的遗愿,让他自由。
所有的身后事都办完了,还没等大家从悲伤的气氛中缓过来,家里就聚集了很多人,来人的大多数都说是本家的人,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刘家是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家族。
争论的焦点无非就是刘家的掌家大权,他们也不顾我爷爷刚刚死去,尸骨未寒,在会客室中争得面红耳赤,最大的一股势力是我所谓的二叔公带领的,他们仗着是我爷爷唯一还健在的兄弟,要求把掌家大权和家族的财产一并移交给他掌管。
他们脸红脖子粗的,要不是我老爸在其中周旋缓和着场面,他们大有拳头下见真章的意思。
我几位叔叔倒是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但在我二叔公的孙子推了我老爸一把的时候,我三叔手疾眼快地扶住了我老爸,并且顺势给了年轻人一个蹬踢,将他一下子踢翻在地,疼得直哼哼。
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我二叔公看着他的人受到了欺负,生气地将拐杖使劲点点地,声音之大让整个场面都安静了下来。
他一把站起来,指着我老爸就开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大哥没教过你们对待长辈要尊敬吗?你们这种做法是要造反吗?我大哥现在死了尸骨未寒,我身为刘家唯一的长辈,为了刘家的发展,理应把掌家大权交给我,这样也心服口服。你们现在这样跟我僵持,是想让刘家四分五裂吗?!”
我老爸看老人家动了怒,怕他气急攻心猝死过去,刚想做和事佬,我三叔一把拉住我老爸,微微摇了摇头,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下一秒我二叔便把茶杯摔在了桌子上,坐在那里,对所有聚过来的目光视而不见。脸上挂着一丝瘆人的冷笑,不怒自威,即便不站在他身边,我都能感到我二叔的气场压制了整个房间的人,我甚至看到了二叔公的身体似乎都禁不住抖了一下,“二叔,我看您老带了这么多人来,以为您是老糊涂了,忘记了我那个老爹刚死没几天呢?!您说您这个阵仗,不怕我老爹晚上找您聊聊吗?”
二叔公一听这话,气得身子都在颤抖,手紧紧拄着拐杖才勉强站稳,哆哆嗦嗦半天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二叔也没有给他辩驳的机会,脸上笑意消失,表情严肃,气势压人,但声音却依然不疾不徐,“二叔,说破天这家也轮不到您来掌,法律上明文规定,财产要按照直系血脉的顺序来继承,您也就算是旁系,所以这家必须得我大哥来掌。何况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大可以惬意地安享晚年,犯不着吃相这么难看。说句难听的,我大哥温文尔雅,对您一直以礼相待,您就这么欺他,是觉得我们几个兄弟是摆设吗?且不论您就来了这么几个人,您就算带来再多,也得掂量一下我和三弟的势力不是?趁大家没彻底撕破脸皮,我还好言相劝,您不如回去吧,再闹下去,我可不保证只是跟您说说话这么简单了。”
二叔公盯着我二叔,连连说着“你”,半天都说不出完整的话,胸口起伏得厉害,看来是被我二叔气得不轻,急促地喘息了几分钟后竟然晕了过去,众人手忙脚乱地把老爷子抬去了医院。
看着他们走远,我扑哧轻笑出声,我四叔站在我旁边,小声地问了我一句,“小霍,你笑什么?”
我凑到他耳边,笑道,“四叔,按照我多年的经验来看,老爷子装晕的技术可是如火纯青啊,他年轻的时候要没有点生活,演技都不能这么纯熟。”
我四叔听了,笑骂了我一句,“你小子,行啊。”
我们交头接耳的功夫,我老爸,二叔三叔已经都正襟危坐了,霎时间,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们几个。
我三叔的眼神轻轻飘向了我四叔,我四叔见状,立马闭上嘴不笑了,场面沉默得可怕。我站在一旁,总觉得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他们接下来开口说的话未必是我希望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