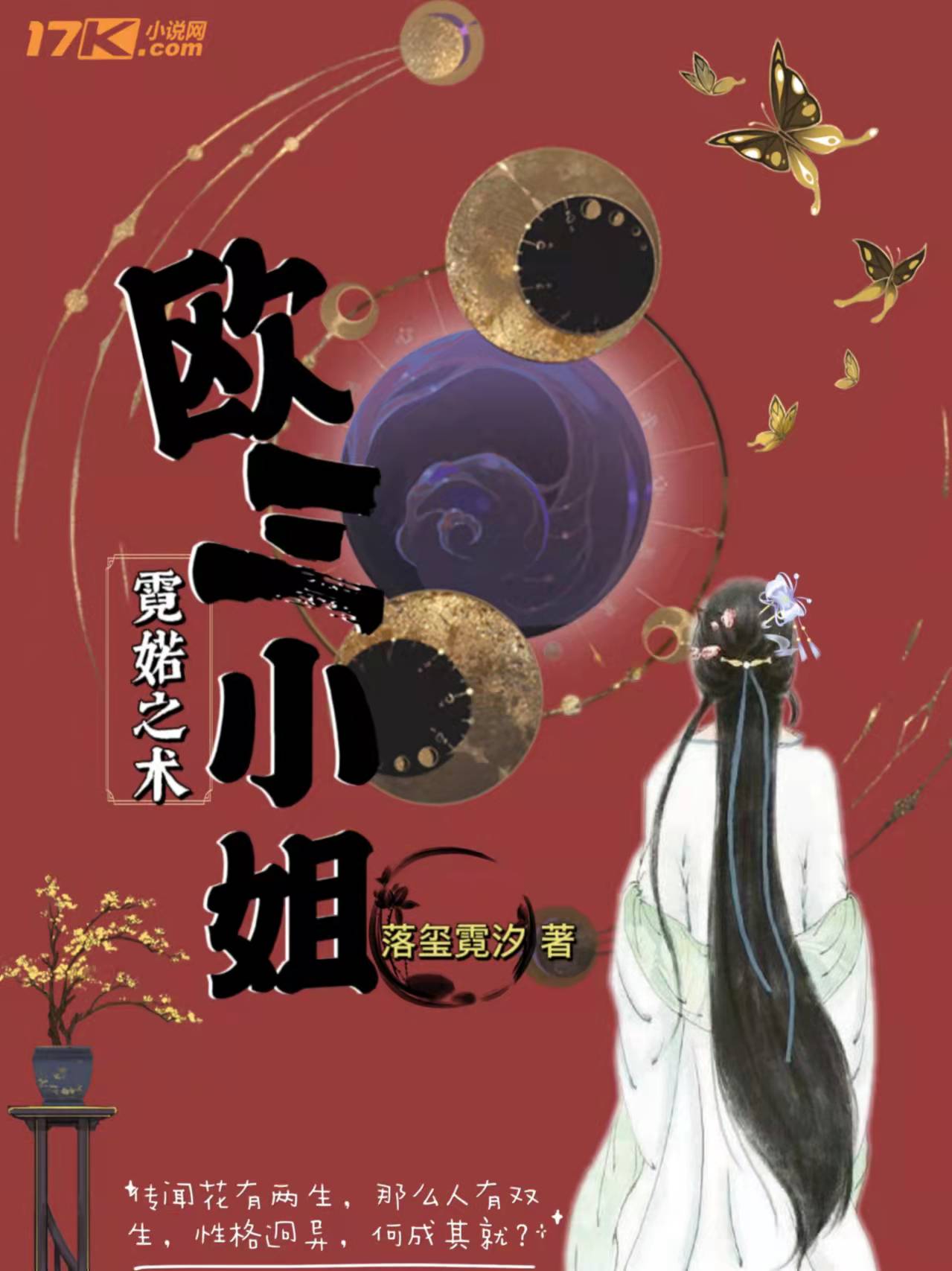回到家后,万如意就直奔房中。“白姑娘!……人呢?”
之所以叫她白姑娘,可能是因为她看上去比较白吧!
街上,女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身体走进了一家医馆。大夫,最近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很疲惫。
大夫把脉后,笑着说道“姑娘身体并无无大碍,就是有些气血不足”!
正想说什么,只见一位妇人冲过来牵着我的手说“雅儿,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旁边的这位妇人,难道她真的是我的亲人?正寻思之际,妇人牵着我的手就说“雅儿!我在京城找了你大半年了,没一点音讯,旁人都劝我别找了,这么大个人散散心就回来了,但我就是不放心”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生了场病,过去的事都不记得了!”我边安慰边说着。或许此人真的是我的母亲。
“跟娘回家!”夫人牵着女子的手,喜极而泣的说道。
于是,便被她拉着从锦州回去京城——永安城。
既然找到了亲人,我便留下书信差人送到万府给万家小姐。只见万如意翘着个二郎腿,嘴里品尝着糕点,慢悠悠的听着小丫鬟急切的说话声。
“小姐!有人差人送信给你”
随着母亲回到了京城。
永安城的繁华不同于锦城,它的街上少了些人气,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人间烟火气息。这里的街上更多的是豪华的马车,或许在看不到的地方,依旧有人行乞,衣裳佝偻。这里的酒楼造型复杂多变,听闻达官贵人多为这里的常客,有人在这里一郑千金,只为寻开心,有人在这里施展才华,卖弄笔墨,只为寻得伯乐,让自己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一跃龙门。也有的人想在这里寻觅知己,只为疏解心中苦闷,总而言之,这里就是汴京人的天堂。它的名字叫做靖水楼。它因为临水而居,因此取与近水楼台先得月相近之意,每当清晨的第一道曙光照进酒楼的房间里,那便是象征着美好一天的开始。
“母亲,我之前叫什么名字?”
“你父亲过世的早,你就随着我姓闵,叫雪雅!”好似她不愿再回想起前尘往事
打开书信,万如意笑着说道“原来她叫闵雪雅!”
身旁的小丫鬟也开心的说“白姑娘找到家人了,这样就不会孤苦无依了!”
母亲经营着一个染布坊,因为其染房是由母亲的祖父传下来的所以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气。同样,过去她们也因此而衣食无忧。
闵母温柔的声音响起“雅儿!自离别多日,你似乎变了许多!倒像是换了个人!你若有心事,可向母亲诉说,可别在做些傻事了!”
闵雪雅思考了闵母的话,估计是自己之前做了些任性的事,让她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每每不说话发呆时,她总是过来询问。可究竟之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对于周遭的事物感觉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就好像是突然闯入了别人的世界一般。
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很难接受,比如作息时间!比如饮食习惯!比如说话方式!
一切都只能慢慢的去接受了!
随后,一阵清脆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小姐,吴妈说让我随你到寺庙去给僧人添些香火!”
我看向她问“何时去?”
“夫人说的是现在!”丫鬟小月把为了把夫人的话传达到位,缓缓的复述了一遍闵母的话。
“等我换双鞋就走吧!”闵雪雅笑着说。
正午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我与小芸就寻了一处亭子准备休息片刻在出发,然而不巧的是竟然下起了大雨。
“看来天有不测风云呀!”看着越来越大的雨就感慨了一下。
片刻后,一男子骑马走到了亭子前,只见他身着一件的玄色直襟长袍,衣服的垂感极好,腰束月白祥云纹的宽腰带,其上只挂了一块玉质极佳的墨玉,形状看似粗糙却古朴沉郁。
他像是在眼前,又仿佛不存在似的。我愣愣的,下一刻好像又失去了知觉。
“他不是那个……那天……”
想起那日在思雅楼的事,此事见到他颇有些尴尬。
之后回想起此事就理了理事情发生的脉络:原来那日我醉酒后,大意的万如意扶着我走进房里休息,不巧送错了房间!谁让客栈的客房长的都一样,而我的房间刚好与此男子房间位置相似呢!想起当时的盛况,窘迫二字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尴尬,更何况这件事一直都没有和别人提起过。
要是向母亲提起,以她的观念,就是女子家的名节算是毁了。毕竟,自从与她回到京城后,没少说过那些关于女子要遵守的妇德。从家里以及染房没有男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可能是目光过于强烈,他转过头来看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真是冤家路窄!”
小芸耳尖听到后就问“小姐!你说什么?”
见我不回答,随即看向旁边男子,不知为何竟然被其冷冽的表情吓退。
小亭子里,三人一马在躲雨,彼此都没说话,许是太过于安静了,这马突然发狂起来,打破了亭子里的安宁。
看着发狂的马,小芸顿时叫出了声来,那知马向是被惊到似的,抬脚就往我与小芸的方向跑来。
尽管表情淡定自如,但其实我心里早就狂喊着“完了!完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男子挡在我们前面,安抚了受惊马。
“小姐,没事吧!”小芸担忧的说道。
他随后看了我们一眼便走向了亭子的另一边,只见他抬头看向了天空,留给我们笔直的背影。
“小姐~!”小芸小心翼翼的叫我。
“你害怕?”我笃定的问。
我握住她的手,示意道“有我在!”
难道他没认出我来?还是故意装作没看见!
此时此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只可惜天公不作美!雨越来越大!
“小姐!我们用不用过去行个礼呀!”
我发了些小脾气小声说“行什么礼!一个登徒子而已!我们不用理他。”
随后,白了那人一眼说!“装什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