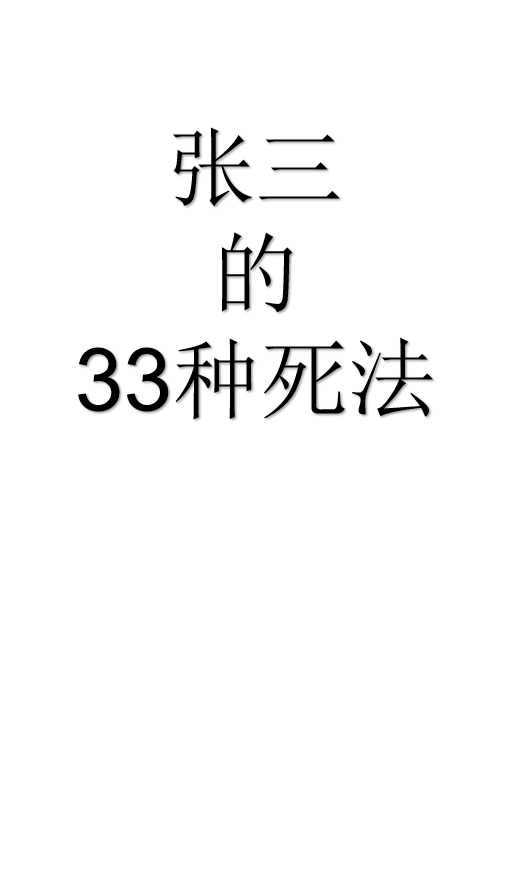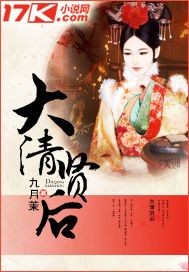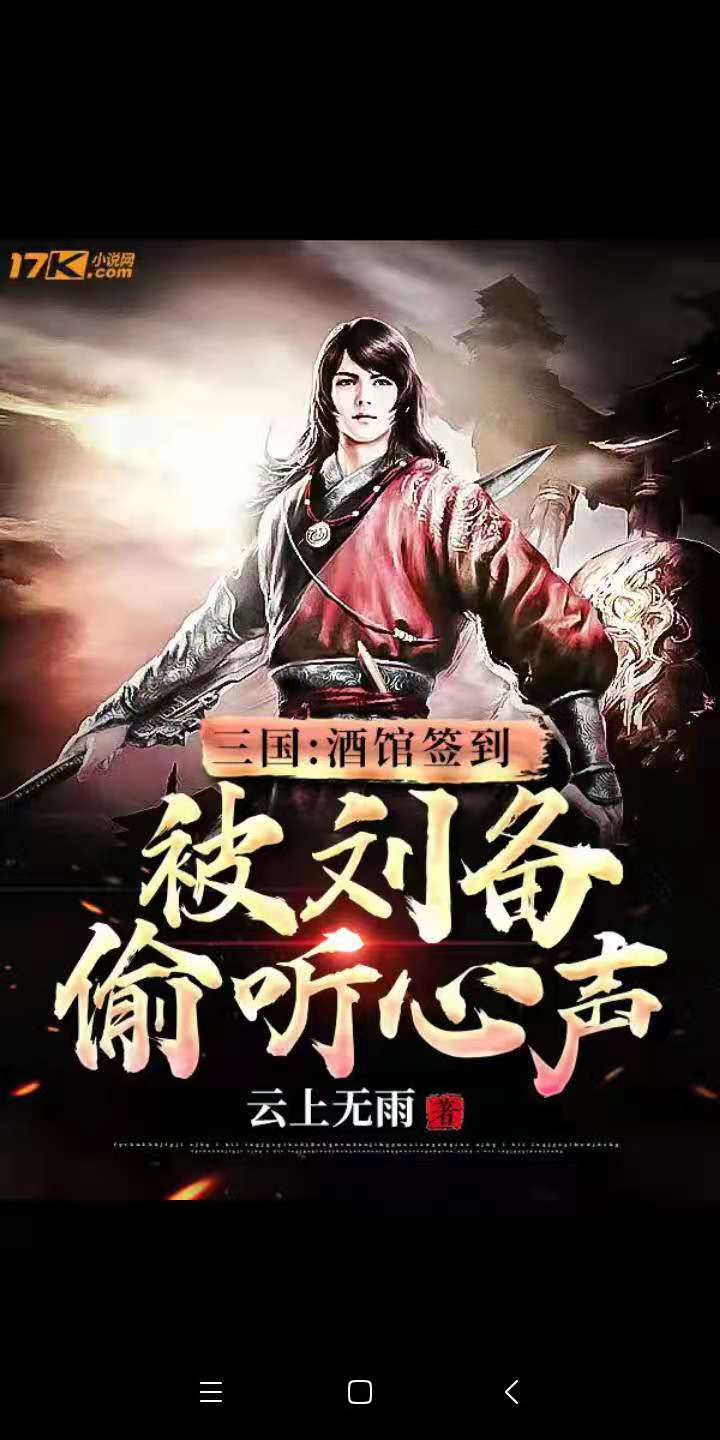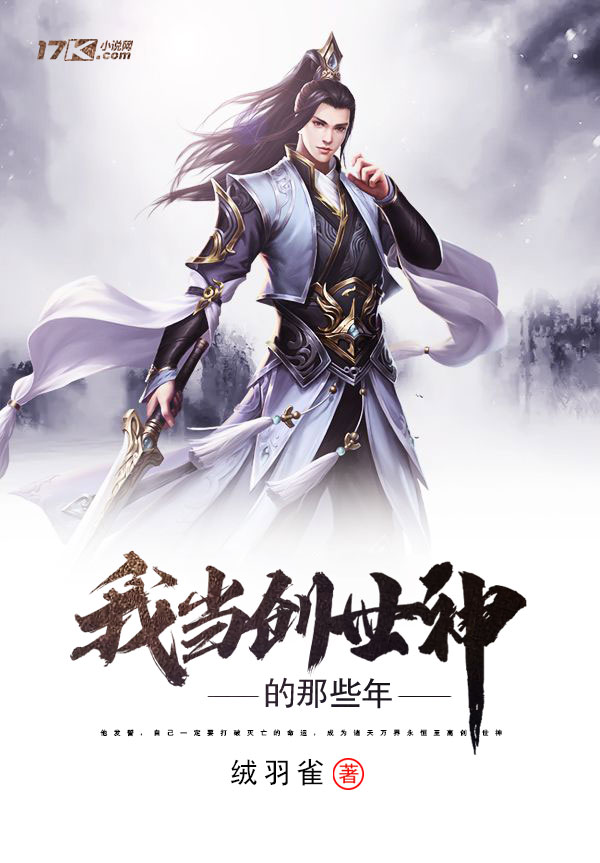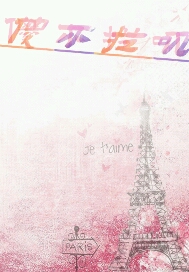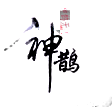以“废都”引出“流氓作家”,合理还是臆测?
近日无意间看到网上的一段文字以及底下的评论,其中不乏有着对废都作者的攻击。而这样类似的现象不单单是“废都”这样单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类似极左或者叫做偏激的现象蔚然成风。
梦回93,作者完成了废都的写作并开始发表。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上有驳于传统文化主流观上的保守谨慎,而是将“需求”直白露骨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两性愉悦的场景更是呈现一种主观上的冲击。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这部作品存在这一定的争议,并一直延续至现今。然而这样的争议早已超越作品的本身(因为谈论作者和情色的部分比谈论作品本身的更多),并且以此来诋毁具体的人身上,这样的一种“无理”显然不行。
一方面,废都绝不是下三流的作品。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指控大多是站在“下三流作品”的观点上,然而这根本不成立。从写作的方面来看,在特定的角度利用冲击性的文字让读者获得直面感从而来震慑心灵并以此埋下伏笔,显然在这方面,作者利用的相当的巧妙。然后,从所描述的深刻角度来说,诠释了当年的时代变迁,写下了当年文人的一种悲壮挽歌(过多的不再阐述)。再者,即使某段时间被禁,但依然获得文化界的认同,季羡林的评价以及费米娜奖项便是佐证。
其次,我们应是理性的公民。我们承认感性是重要的,我们可以情感上不喜欢与自己价值观不相似的人或事,但只能限制在不喜欢和“和平的讨论”的框架上,而不应以此恶意攻击,践踏权利。“理性”赋予我们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我们面对信息繁杂的信息中能够不被带节奏,不会当成韭菜被利用。因为在现今盛行的自媒体中,我们不能保证其中不存在着利用有意无意的情感导向将群众引向他们利益的彼岸的投机者。从这篇文字中就可以看到那种情感导向,虽表面夸赞或表面理性,其实很容易勾起群众反方向的前进。同样,在作品讨论中无论是文学届还是其它,不同的声音总会有,批评的声音也肯定是有。我们应该做的是从这些批评中再次来审视作品,而不是全面否决。因为,我们依然不能确保批评的人是处于什么目的来做评价,是单纯对作品评级还是处于个人利益?过多的陈诉不再谈论,其中涉及的面很宽大。用玩笑的话来说“同行是冤家”,虽不准确但也能反映一部分情形。
理性公民是文明社会的构成,而文明社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便是包容性。个体间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使得大部分人喜欢某个东西,但并不以此来强迫小部分人趋同。我们尊重小部分人的价值,社会更赋予其价值,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的简单分割(当然除了以投资或者其它为目的市场人)。换而言之,即使废都这部作品正如所说的那样不堪,但同样依然有人喜欢它,那么全面否定它的价值是种粗鲁且不合理的专断行为。我们需要尊重这样的作品,更何况还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无论喜恶,应以尊重他人为前提。显然从作品上升到人身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