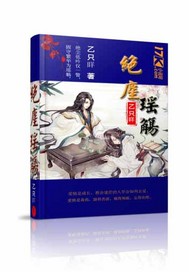林飞燕以五十两银子的价格被卖到剪子街翠柳巷怡红院里,过上了白天睡觉晚上接客的日子。由于她出自名门望族,从小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楚剧京剧黄梅戏样样精通,所以到了这里就好像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张显出她的异常天赋,当即成为县城的名媛,地富官商、三教九流都以认识她为荣都以结交她为幸,如果有人睡过她,那就是顶极大咖了,圈子内外都刮目相看,五体投地。
县令屈振奇将林飞燕接到自家的“下院”里好酒好菜地款待,酒过半巡,屈县令站起来向她拜了一拜说:“林大美人,本官有一事相求,事成之后必当重谢!”林飞燕慌忙站起来回礼道:“老爷,行此大礼,小女实在受不了,有什么吩咐请尽管提出来,一定答应。”屈县令犹疑再三后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我儿屈益智你认识么?”林飞燕愣头愣脑地回答:“久闻屈公子大名,只是无缘相识,县令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屈县令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直来直去了,最近传闻有我家丑,污蔑我家儿子,此事你有耳闻?”林飞燕这才明白过来,心里琢磨着自己接待的客人不多都是人中精品非富即贵,且化名者居多,自称南来北往的人很多,而本地人极少数,能叫得出名字来,知根知底的有几个,就是没有屈公子这个人,心里在打鼓,会不会有人冒充屈公子呢,但是为什么一定得冒充呢?林飞燕突然拍了拍胸脯说:“啊,我记起来了,有一个河南的屈公子,下巴上有一颗黑痣。”屈县令吃了一惊,心想着这不是我的儿子还是谁哟,我儿子下巴上有一个痣,果然印证了外界的谣传,于是镇定自若地说:“我给千金,你寻找机会宰了他。”林飞燕痛快淋漓地回答:“这有何难,他约我今晚在举水客栈相会,必定会喝得烂醉如泥,乘机结果了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么。”她接着说:“万一他今晚不喝酒,我一个弱女子敌他不过,还得请你派人相助。”屈县令说:“行,只要你将他哄到隐蔽的地方,然后退身,我们会有人结果了他的。”屈振奇嘴巴上是这么说,可是心里还在七上八下的,自己的儿子最近早出晚归、神出鬼没的,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家里,虽然做父亲的坚决反对,但是也拗不过儿子,任其胡作非为,如今外界谣传儿子吃喝玩乐、夜不归宿,最近还经常去翠柳巷包养了一个漂亮的妓女,作为县令更是无地自容,所以就起了杀心。林飞燕并没有观察到屈县令脸上轻微的变化,只当是一桩公事公办的任务,所以她不以为然地补充道:“你们可要看清楚啊,我带的这个屈公子可是北方口音,下巴有颗痣。”
当夜,屈振奇吩咐管家带了三个人潜伏在举水客栈的后院内。只听林飞燕暗号一响,冲了出来,将屈公子按倒在地,嘴里塞上破布,头上罩着麻袋,双手反剪捆绑麻绳,抬上轿子,一溜烟地回到县衙。屈县令当即挑灯夜战,严刑拷打,屈公子立即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不停地喊饶命。良久,管家说:“饶你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再不与林飞燕往来,并且不再去那个地方。”屈公子坚定地回答:“你还是打死我吧。”
几个差役掀起大板子使劲地打起来,直打到屈公子没有力气叫喊。管家觉得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县令只是命令我往死里打,可没有说让我打死他,这事还得报告县令。屈县令闻言大怒,“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我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呢?你们说怎么办?”管家说:“屈公子坚定不移地要求非林飞燕不娶,否则再不是到怡红院,而是到能仁寺做和尚。”屈县令愤怒地回答:“让他去做和尚吧,就当我没有生这样的一个儿子。”此时,屈母走过来了,她颤颤惊惊地问道:“我儿回来了么?”大厅内顿时漆黑一团,是管家将灯灭了,大家都知道屈母如果看到儿子被打成这样就会寻死觅活,到时大家都不好看。管家出来打圆场了:“老爷,我看再不能打了,再打就死人了。”“就当我没有这样一个儿子。打。往死里打,打死就行。”管家说:“我有一计,不知行还是不行?”屈县令点了点头。管家说:“屈公子混迹烟花柳巷固然斯文扫地,但是总归是你儿子,打死儿子让世俗人笑话,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屈公子不是说宁可做和尚非林飞燕不娶么,我们也可以让林飞燕去当当尼姑。”
“让去当尼姑?”屈振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你怎么想得出来?”
“有何不可,我们多给些银子将林飞燕从怡给院中赎身后直接送她到大安寺的白圣庵,断了她的念想,也断了公子的念想。”管家若无其事地说。:“此事不由得她干还是不干,反正这大别山的各教头头脑脑都是我的朋友,让她求生不得也行,让她痛改前非也行,让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有辱法门啊,有辱法门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
“法门深似海,进了法门自然有其清规戒律,我就不怕降服不了她。”
“罪过啊,照理说她卖淫也好,我儿嫖娼也罢,我们不能当法海,只听说过‘逼良为娼’,从来还没有听说过‘逼娼为良’,罪过!罪过!”
“老爷说的有道理,只是这林飞燕睡了一万人也罢,跟了一千人也行,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与我们公子有染,染上了就得烂肉。就这么定了,老爷你只装聋作哑便是。”
屈县令摆了摆手说:“将那个不孝的狗杂种关在死牢里,什么时候悔改就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老鸨听到屈管家代表县令驾到,情知大事不好,亲自迎接,听到屈管家口若悬河地一吹一拍:“这林飞燕的父辈哟是我远房的世交,如今他托梦给我助其圆满,我若不来必遭遇天遣雷辟,所以本人虽然财薄气短,但是掂起脚来做长子,明知不可而为之,请婆婆放行。”老鸨听他甜言蜜语之说,又看了看桌面袋子里的银子真的是喜从天降,哆嗦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屈管家必定长命百岁呀。”老鸨当即小声地对屈管家说:“此事虽然谈妥,但是我还得明天放她走。”屈管家说:“这又是为何呢?”老鸨说:“既然她是出家,就直接送她去白圣庵,你今天去与庵内说好,明天一大清早送她去。”
“此计甚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