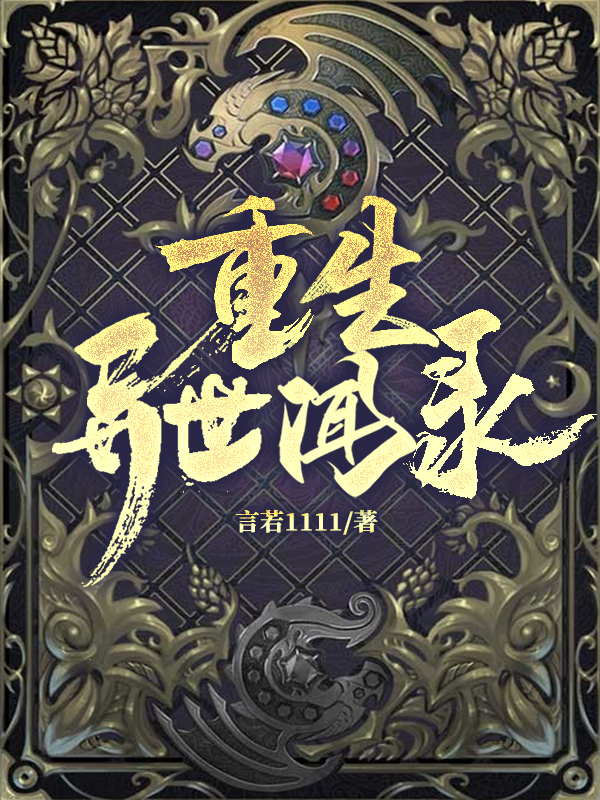丹菲好似被棒子敲在头上,怔了片刻,才低叫道:“她,她还没足月呀,怎么……”
“奴也不知道。”宫婢急道,“女掌娘子是崔家表亲,不妨走一趟吧。如今县中无人,崔家正焦头烂额呢。”
丹菲哪里用她提点,当即就提脚朝外冲去。她今日本就穿着骑装,行动方便,翻身上马就朝县衙后街奔去。
到了崔府,只见里面已经乱作一团。孔华珍的一个陪房婆子认得丹菲,见了她就如同见了救星。
“去请产婆了吗?热水、棉布可都准备妥当了?”丹菲作为宫婢,受过些训练,知道此时该如何行事。
婆子抹泪道:“已经去请产婆了。只是夫人流了许多血,怕是不好。”
丹菲脚下一个踉跄,强自镇定下来,大步朝里走去。
内堂里,仆妇婢子们急得团团转,产房里传来痛苦的**,游廊上甚至还有一滩血迹和一堆碎瓷,触目惊心。
之前见过的那个娇媚的小娘子正跪在眼下,哭得梨花带雨,捏着帕子的手还做兰花状。
丹菲被她堵着进不了门,指着她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婆子唾道:“就是这个贱奴推了夫人!”
兰草嘤嘤哭着磕头,额头也没碰到地砖上,眼泪倒是撒了一地,“奴不是故意的打翻那碗汤的。奴也不知道珍姐会踩着滑倒!奴绝对没有害珍姐之心,求娘子明鉴!”
丹菲她们这些宫婢,平日里无聊,都把后妃争宠当戏来看。兰草这点演技,怕连台都登不上。她当即冷笑道:“这里又没男人,骚成这样给谁看?”
兰草一愣,崔家奴仆却是一喜。
毕竟崔家后院仆妇大都是孔华珍的陪房,奴随主性,都是口不出秽语的斯文人。虽然恨兰草恨得牙痒,却也只知道骂几句贱奴,真是不够解气。丹菲看着通身矜贵之气,骂起人来却是粗俗又直白,毫不客气。
众奴婢顿时看着丹菲无比亲切,一下找着了主心骨。
丹菲也不负众望,对兰草喝道:“夫人生产,你不要在这里添乱,回你自己房中呆着吧。”
兰草被丹菲那话扇了一记无形的耳光,脸涨得通红,死死守在门前,道:“奴有冤屈,怎么可能就此离去?奴求珍姐一句话罢了!若是珍姐觉得是奴的错,那奴就以死谢罪。”
屋里,孔华珍正痛苦**着,哪里有功夫理她?
“还真是给你脸却不要脸。”丹菲冷笑一声,一脚就将兰草踹到了一边。
兰草毫无防备,一骨碌就从门前滚到屋檐下,跌得一身泥水。
旁观的奴婢们轰然叫好起来。兰草惊得都忘了叫,呆坐在地上半天动不了。
后宅妇人争斗,大都是口舌来往,哪里想到丹菲看着矜持文雅,却是不按规矩出牌,上来就动拳脚。而且出招极利落,一看就知道有几分身手。
兰草也是文弱的小娘子,在崔家这段日子里又养得极其娇贵,挨个巴掌就觉得受不了,如今被人踹进泥水里滚了一圈,顿时寻死的心都有了。
她终于回过神,嚎啕大哭起来,“你居然这般欺辱我!崔郎,你可要为我做主呀!”
丹菲懒得多看兰草一眼,点了两个看热闹的粗壮仆妇,道:“把她拖回她房里,一日三餐地看好,别出了岔子,等县令回来处置。崔家的事,我可不好越俎代庖。”
说归说,还不是一脚踢得人家满地滚?众人窃笑不已。
那两个仆妇也有经验,拿了块汗巾堵了兰草的嘴,一左一右地将她架起来,风一般地拖走了。
闹了这么一阵,产婆终于来了。丹菲还是在室女,不便进产房,只好在侧厅里等消息。
孔华珍这一胎怀得不安稳,又早产,孩子头过大,卡着出不来。她自己本也不是健壮之人,拼着力气熬到了后半夜,就已经虚脱,一度昏了过去。
婆子捏着孔华珍的鼻子灌了参汤下去,终于把她唤醒。她睁开眼,只问:“四郎回来了吗?”
婆子和婢女都在抹眼泪,心到主母怕真的要不好了。
丹菲已经派了人进山给崔景钰报信,自己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她本事很多,能文能武,却唯独在女人生孩子这事上帮不上忙。
如果孔华珍和孩子有了个好歹,倒是和她没关系。可是……崔景钰必定会极其伤心吧?
他是那么期盼这个头生子呢。虽然从不说,可一提及此事,他的眼里都会涌出温暖的笑意。那是即将为人父的喜悦。
他这么拼命,运筹帷幄,和各方势力周旋,借着太子的兵力铲除真正的悍匪,还想解决当地帮派恶斗……他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给妻儿一个安稳么?
丹菲一不留神,脚踢着了案几,小腿骨磕得生疼。丹菲抱着腿正揉着,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喧嚣声,似乎有人在外面的巷子里打闹。
正困惑着,就见一个管事连滚带爬地奔进了院子,茫然地寻了一圈,最后选中了勉强算半个主人的丹菲,扑过来大喊道:“娘子不好了!有贼人来攻打县衙!”
“什么?”丹菲震惊,以为自己又在做梦,“这里是县城!早都已经关闭了门坊,哪里来的贼人?”
“真是有贼人,娘子你听呀!”管事急得一头大汗,“大管事已经带着小子们守门了。可是贼人太多。大管事让娘子赶紧带着夫人逃走。”
孔华珍还在里面拼命生孩子呢,怎么逃?
而那阵阵厮杀声果真就在耳边。县衙又不大,后宅也不过是一个左右三进的院落。对方如果人多,用不了多大功夫就能攻破。
丹菲吩咐婆子守好孔夫人,大步奔出了内堂。
外面果真已经乱作一团。外面的贼人在撞门,又在县衙一角放了火。家丁们拼命地堵着门,还得分出人手去救火。
大管事年事已高,指挥了一阵便体力不支。二管事却又受了伤,昏迷不醒。三管事一人指挥不过来,见了丹菲就大声嚷嚷:“娘子怎么还不带着夫人先走?”
都被包围了,怎么走?丹菲又不会飞天遁地之术。
丹菲问:“那起火的房子是哪里?”
“是囚房。”
“可有犯人在?”
“没有。”
丹菲道:“那便不救了!分了人手去守后门!”
“可火势要是蔓延起来……”
“囚房四周都有石墙,一时也烧不过来。”丹菲抓着管事大吼,“要是后门破了,夫人有个好歹,你拿命赔给你家主人?”
管事被她唬住,当即调了人去后院。
丹菲神色如利刃一般盯着被撞得不住耸动的大门,问道:“哪里来的贼人?怎么算得这么准,知道县令不在,便来打劫?”
管事道:“我听着口音像是漕帮的人。之前漕帮内斗,县令帮着镇压,赶走了一批帮众。这些人想必是白日就潜伏进了县城,晚上就来攻打。”
原来是寻仇。
可这么胆大包天,赶在太子眼皮底下找大周官员寻仇,怕韦亨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县城卫军何在?”
“贼人人数众多,怕是把卫军给绊住了。”
这时外面传来一个人声。那人高声道:“儿郎们,这狗官县令砸了我们的饭碗,把我们往绝路上逼,还害得孙二郎断了双臂。如今他人不在,他那婆娘却是在家。咱们杀了他婆娘,抢了他家财,为孙二郎,也为我们自己报仇!”
这人一呼百应,撞门的力量又大了几分。门内家丁就快顶不住了。
丹菲随手抓了一个家丁,抢了他手中弓箭,奔上了县衙正堂的楼上。这里地势最高,可以俯视楼下。只见门外簇拥着好几十人,火把攒动。一个肥壮的大汉正站在一个拉柴的车上,呼喊助威,指挥着手下攻打。
那人也是有恃无恐,站在明处,想必是真当崔府里只有无能妇孺了。
丹菲拉箭开弓,对准了他,手臂稳得就像磐石一般。她上一次杀人,是何时?
刘家院子里,溅在雪地里的鲜血……
她没有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还会再将此事做一次。
利箭划破长空,嗽地就洞穿了他的喉咙。那大汉一声都发不出来,身躯轰然向后倒下。
丹菲一击得中,迅速藏身在柱子后。
领头人一死,门外一阵混乱,攻打大门的阵势顿时弱了不少。
丹菲换了一个位置,再度拉弓,朝门外射去。
丹菲在暗,贼人在明,暗箭最伤人,丹菲箭法又极好,每箭必中,甚至差不多每一箭都能取人性命。贼人仓皇反击,却都被丹菲躲过了。
丹菲并不想杀生。但是,震慑敌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杀鸡儆猴。
筒里的箭射完,小家丁连滚带爬地给她送来新的箭。丹菲又连发两箭,把两个要翻墙进来的贼人射了下去。
“娘子好厉害!”小家丁大声欢呼起来。
丹菲来不及出言喝止他。耳边听到破风之声,她猛然扑到,一支利箭射进那小家丁的胸口。
小家丁倒地,垂死挣扎。丹菲想救他,但是无从下手。小家丁抽搐了一阵,咽了气。
丹菲紧闭了一下眼,匍匐爬行到柱子后,不动声色地朝箭射来的方向打量。那个射箭的人也藏身暗处。
混乱之中,那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是那人手中的箭头折射了火光。
丹菲猛地跃起,身影就像鬼魅一样闪过,却是接连拉弓,三支利箭前后追着对方而去。对方也有一支利箭射来,在丹菲胳膊上擦出一道血花,钉在了柱子上。
丹菲扑倒在地,从栏杆之中,望到那处一个黑衣的男子胸口中箭,从屋顶跌落。
干掉了贼人中最有威胁的弓箭手后,丹菲整个人就陷入最兴奋的状态。她气势汹汹地反攻,一箭接一箭,射得门外贼人仓皇躲避。
贼人们见前门攻不破,又纷纷朝后门涌去。丹菲握着弓又奔去后门支援。
此时夜已过半,孔华珍还未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却是气如游丝,昏了几次。她的贴身婢子吓得嚎啕大哭,一个劲叫着:“夫人你不能死呀!夫人,你一定要把小郎君生下来呀!”
丹菲经过产房门口时脚步顿了顿,心里一沉。
这时厨房里终于把烧得滚烫的油锅送了过来。家丁们纷纷朝后外面的贼人浇滚油,烫得他们皮开肉绽,惨叫连连。
如此惨烈,这些贼人却还是不屈不挠地攻门。这已经不是寻仇。幕后之人必定是许诺了他们重金。
丹菲心里暴躁狂怒,耐性被消磨得一干二净。望着门外在热油里打滚的贼人,她眼神冰冷。为她递箭的家丁不由打了个哆嗦。
丹菲刷地撕下了一片衣摆,包裹住箭头,然后就着火把把它点燃。
“娘子!”管事看出她的用意,神色惊骇,“这……这可……”
“一劳永逸。”丹菲丢下一瞥,大步走上了楼。
“可……可……”管事追上来,想阻止,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生死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两全法。
“若县令责怪,一切责任都由我担着。”丹菲语气如数九寒冰,脸上被暖黄的火光映照着,却依旧没有半点人色。
火箭射出,准确地落入油地之中。火苗飞速腾起,从一个人蔓延到另一个人,很快,小半条巷子就陷入火海之中。
人们发出凄惨疯狂的叫喊声,他们奔跑,打滚,徒劳地想扑灭身上的火,却是点燃了更多同伴的衣服。侥幸没有引火上身的贼人见状,也不再恋战,纷纷弃械逃走。
墙内,孔华珍正挣扎在鬼门关上生产。墙外,那群贼人则已经陷入了烈火熊熊的地狱。
墙内的家丁们看着这副惨状,全都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咣当一声,丹菲手中的弓跌落在地板上。她的身子晃了晃。管事连忙扶住她。丹菲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他,独自走下了楼。
墙外惨呼声渐渐消退,焦臭的气息却随风而来。
丹菲再也忍不住,扶着墙壁,大口喘息,而后呕吐起来。
管事急忙叫来一个婆子,扶丹菲去休息。
丹菲虚软无力地回了内堂,前脚刚迈进门槛里,就听到产房里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夫人——”
她浑身一震,跌坐在了地上,浑身麻痹,却是连话都说不出了。
婆子急忙去扶她,扶了几把都没能把人拉起来,急得一头的汗。
院门外突然传来杂乱急促的脚步声,一列卫兵执刀拿枪,小跑着冲进院中来。
婆子吓得尖叫一声,丢下丹菲就跑。丹菲茫然地望过去,就见一个风尘仆仆的青衣男子分开众人大步奔来。
那人奔到面前,弯腰一把将丹菲从地上捞了起来,牢牢禁锢在臂弯里,摇着她,呼喊她的名字。
丹菲嘴唇翕动。她听不清,也发不出声,只能用满是鲜血的手指着产房的方向。
男人一震,松开了她,朝产房狂奔而去。
丹菲再度跌在地上,望着男人的背影,终于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