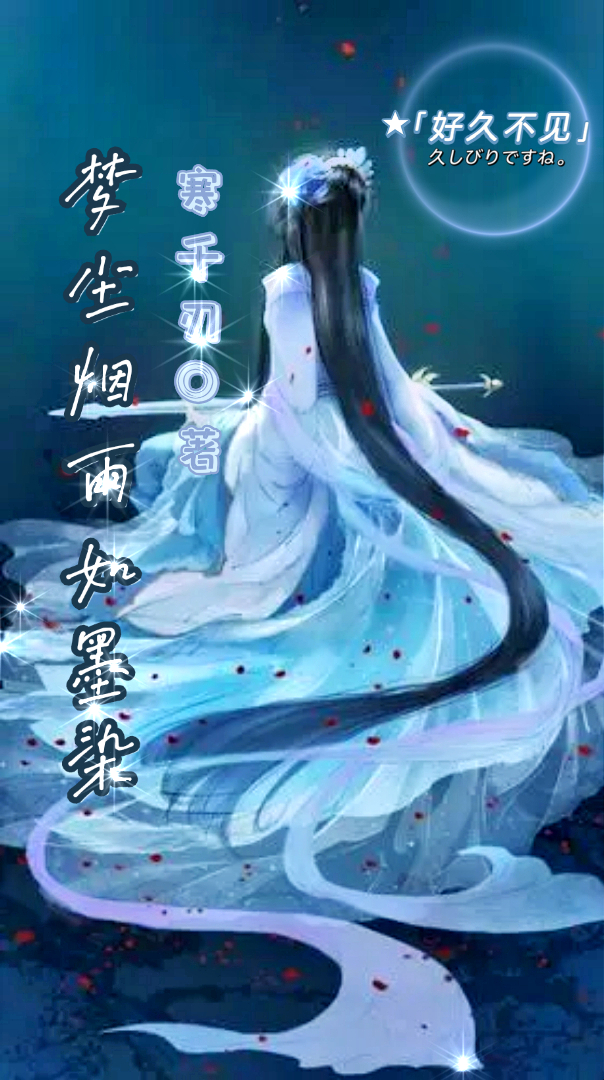“呜呜……,我他娘的太窝囊,呜呜……,”常大爷几口酒下肚,情绪顿时激动,想起伤心往事,痛哭起来,老泪纵横,抽打着自己的耳光,断断续续的哭着说:“连,连——,杀、杀父之仇都报不了,活着,活着也是白活了,呜呜……,我这苟且偷生的日子,日子,折磨的我生不如死啊,啊……。”
梅雪急忙上去,拿过酒葫芦,拉着常大爷的手,蹲在他跟前,诧异的看着常大爷哭的鼻涕眼泪一嘟噜,却手足无措,无言以对。
“雪儿啊——,爷爷让你见笑了,”常大爷深感失态,急忙擦着眼泪,哼出鼻涕甩在地上,娓娓说起往事:“啊——,哼——,你是不知道啊,我的好孙女,爷爷这辈子活的无能,活的太窝囊,我恨我自己啊——。
在我十六岁那年,依照祖上遗训,随着父亲来到这里,那是一个月亮风高的晚上,吃过晚饭你老爷提着大刀出去了。我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已经是深夜,月亮偏西,我就摸索着出去找他。”
常大爷又拿起酒葫芦猛喝一口,放在桌子上,皱着眉头,万分痛苦,用手朝后墙指着说:“就在咱这房后的山顶,两个黑影手持东洋野太刀挥舞的呼呼生风,把你老爷围在中间,团团厮杀,步步紧逼,可是那俩贼人占不到上风,他们身上依稀可见都有刀伤,想必是你老爷要活捉他们,问个究竟。”
常大爷十分懊悔的再次抓起酒葫芦,狠狠的喝了一口,好像只有辣酒才能惩罚自己的过失一样,说:“嗨——,我本就不应该去,我他娘的太混蛋,一看这种场面,顿时大吃一惊,没见过啊——,从来就没见过这种血腥的场面,忍不住喊了一声爹,谁会知道这一喊,你老爷一分神,只顾看我,硬是被那贼人乘机刺中他的胸膛,你老爷的武功虽然不是盖世,也属武林高手啊,即便是受伤,功力不减,挥起大刀,腾空旋起,飞腿踢翻一个,又挥刀扫向另一个贼子,那贼子急忙翻身夺过,可是他的脸上给划过一道伤痕,瞬间血流满面,你老爷已经身负重伤,身负重伤啊——,那俩贼子也不敢恋战,仓皇逃跑。我夺过你老爷的大刀追到岭后悬崖边,却寻不到这俩飞贼的踪影。”
“昂、昂……,”常大爷说到伤心处放声大哭,梅雪缓缓站起身,战战兢兢的伸出手,用袖子擦拭着常大爷的泪水,常大爷张着大口,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说:“我把你老爷背回来,流血太多,不到天亮他就这样含恨去世了。”
“爷爷,那后来脸上有刀疤的你没见过吗?”梅雪擦着眼泪,恶狠狠的问:“见了,我要亲手杀了这畜生。”
“见过,后来前来这里寻矿的都是蒙面人,我杀过七个人,可是没有一个是带刀疤人,”常大爷瞪着眼,目光充满杀气,说:“他们这些贼子就是霸占咱这梅花玉矿而来,个个身手敏捷,轻功非常了得,他们勾结咱本地高手,图谋不轨,为了寻找藏矿图,滥杀很多无辜。”
“我知道应该咋办了,”梅雪把嘴对在常大爷的耳边,轻声的嘀咕着,常大爷边听边点着头。
梅雪安顿好常大爷,拿来***锤和一根錾子,领上两只雪豹,踏着厚厚的雪向那乱石岗走去。梅雪用錾子尖很巧妙的把石头上的字迹改了,“非”改成“菲”,“昼(晝)”字改成“书(書)”,“夏”改成“厦”,“和”改成“积”。然后,她用泥土烂叶涂上做旧,感到非常满意后,用腐殖土薄薄蒙上一层。
她刚要离开,突然,附近的树林里一个人影晃动,待她定眼仔细看去,却不见踪影。她领上雪豹,急忙飞快的向树林方向追去,只见地上有从树上掉落的坨坨雪外,没有一丝脚踏的痕迹。
她抬起头巡视着四周的树上,没看到有啥可疑地方,她不由的吃了一惊,好奇心的驱使,她便顺着雪坨一步紧似一步的追了过去,两只雪豹紧跟其左右。她追了大约有三四里远,连树上掉下来的雪坨也不见了。
她就疑惑不解的要折回来,这时身后噗噗嗒嗒又掉下一连串的雪坨,只见雪豹“雪弟”嗖的一下,蹿到树上,她仰脸望去,一个穿着邋遢,蓬头垢面的大胡子,从树上跳跃着向远处飞奔而去,梅雪不敢怠慢,一咬牙施展轻功紧跟其后,她的轻功追赶速度极快,动作优雅,身姿曼妙,就像是一只轻盈的燕子。
她越追越远,翻过了两个山头,使她感到越发感觉其中蹊跷,她驻足向四周望去,树林深处,阴森恐怖,不由得心里紧张起来,她急忙抽身离开,这时四周的树下陆续掉下来大块的雪坨,她不敢多想立即掉头离开。
两只雪豹一见也急忙跟在后边,越是这样雪梅越感到害怕,握着拳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越感到身后追赶的脚步急速,她就拼了命往回逃,心里后悔不已,咋会这么粗心,竟然被诱惑到这么远而可怕的地方,她甚至害怕的连回头看的勇气都没有了,尽力施展所有能脱离危险的本领,摆脱这群魔鬼一样的强盗。
雪梅脚蹬树枝,跃过沟壑,跳上山顶,翻过大山,望见家时,已累的气喘吁吁,回过头气的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