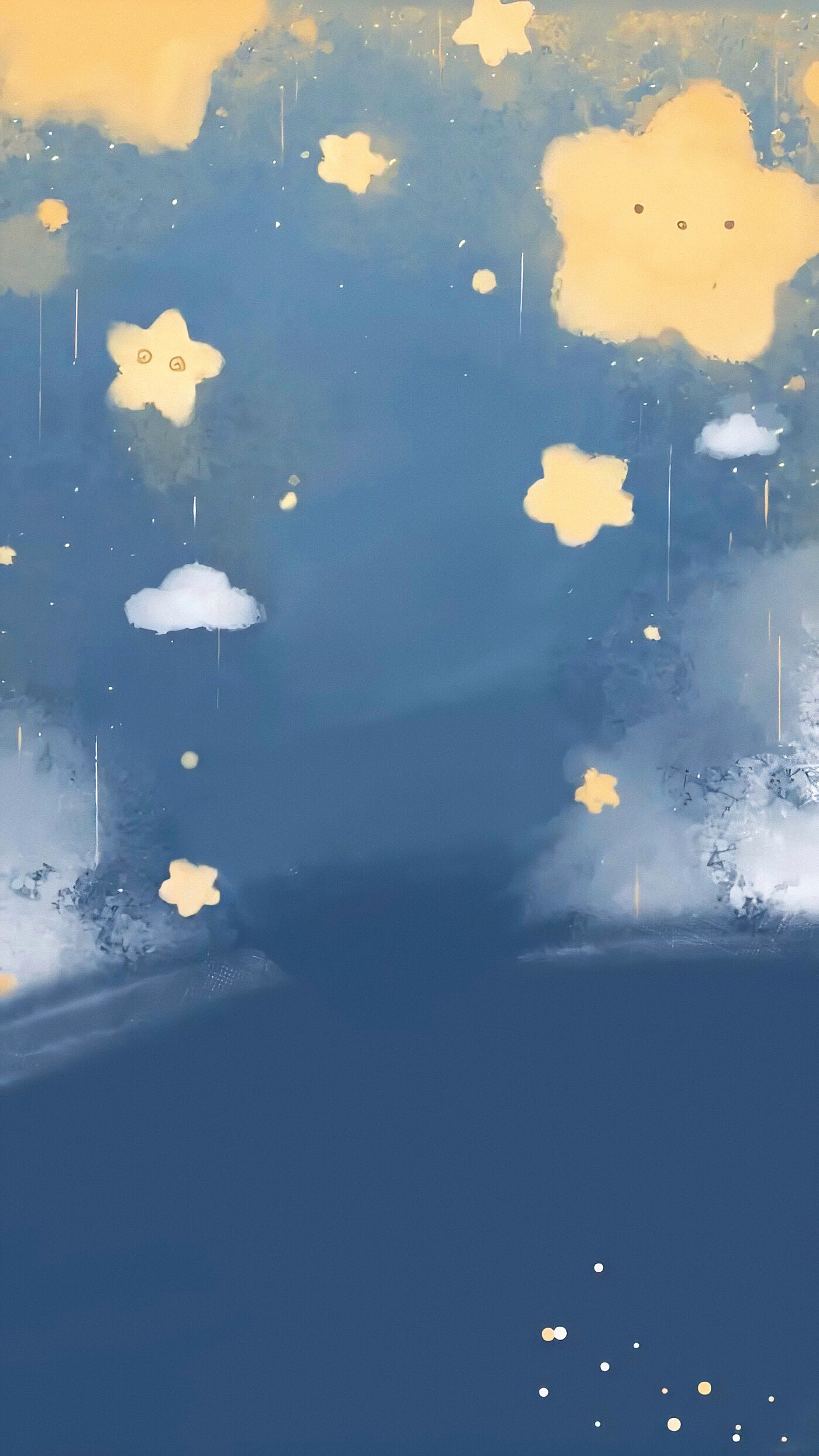何久醒来已是第三天傍晚,陈默和王静怡照例吃喝玩乐赏夜景去了,只有张凤燕端茶倒水的在他旁边伺候。见何久醒了,她露齿一笑:“看来这酒后劲很足啊,睡了这么久。饿不饿,我出去买点东西给你吃?”
原来,三人找不到他,便一直打电话,无奈深山里没有信号,这电话始终打不通。直到深夜,电话才传来一个生硬的声音,告诉三人何久喝醉了,现在在排寨的一家旅店里。
“你都戒了五六年的酒了,怎么突然间又喝起来了?跟谁喝成这样,伤身体的知不知道?”
张凤燕的语气中全是责备,但眼神中透露出来的,哪里有半点责备之意。她对自己有意,何久不是不知道,张凤燕的身材虽然不如王静怡那么前凸后翘,却也是有些肉的,但他就是不来电。几次想要明说,就是拉不下这脸,于是就这么耗着。何久心想,也许时间久了,她会明白过来。
他叹了口气,尝试着摇了摇头,不晕,不痛,不吐,酒,应该是好酒,好多年没喝了,这酒量果然退步了不少,按照六年前的自己,他相信如今在自己身旁的,多半是香香了。
“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见他置之不理,张凤燕有些生气。
“静怡呢?”何久下意识地问了一声。
“你眼里除了她没有别人吗?”张凤燕气得脸都绿了,“嘭”的一声重重的关上门,留下一脸懵逼的何久在床上发呆。
过了一会,张凤燕端着一碗面走了进来,塞到他手里,板着面孔说了一句:“爱吃不吃!”
只不过话音未落,何久就已经狼吞虎咽起来了。张凤燕倒了杯水递过去,嘱咐他慢慢吃小心噎着,望着他胖嘟嘟的面容,她嘴角挂起淡淡的微笑,哪里还有半点生气的模样。
“咦,你银坠呢?”张凤燕看到他的脖颈上空荡荡的,不由吃了一惊。
“丢了吧。”望着远处的青山,何久淡淡说道。
“那还不去找?”张凤燕大吃一惊。两人从小玩到大,这根银坠的底细她是知道一些的。那是何久的苗族外祖母出嫁之物,后来外祖母把它送给了出嫁的杨妹久,何久出生后,杨妹久把它交给了儿子。这么重要的东西,何久平时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怎么说丢就丢了!
“当时真不是故意的,现在想想,或许还真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到这里,何久的心莫名的痛了一下,眉头紧皱,捂着胸口,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别担心,有我呢,就说你借给我玩,被我不小心弄丢了。阿姨要打要骂,我一人承担。”
“你……该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何久似笑非笑。
“做你的春秋大梦!”张凤燕嗤之以鼻,脸上却莫名的红了一下。
“我想……”望着远处的青山,何久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这几天,他都心不在焉,时常望着远处的青山发呆,要么问一些关于夯吾寨的生活习惯,但生苗毕竟不与外族人联系,导游也是知之甚少。张凤燕疑窦丛生,却也不好多问,默默地陪着,至于王静怡,正与陈默打得火热,哪里还管何久的死活。
旅游回到家,杨妹久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说儿子是个马大哈,这几天多亏张凤燕照顾。妈妈的心思做儿子的岂能不知,无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何久与张凤燕多接近接近,争取早日让两家并成一家。
张家父母对于这门婚事显然十分高兴,所以,杨妹久发出邀请,张家父母欣然接受,席间,特意让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两大家子说说笑笑,原本其乐融融,哪知风云突变,张凤燕哭着离开,而起因,是何久的爸爸何所惧说起了自己年轻时如何力战排寨苗王迎娶杨妹久的光荣事迹。
张凤燕正听得入迷,突然何久冒出来一句话,许是喝酒的缘故,他的音量比平时明显高出不少,而这句话,无疑就是炸药包的***!
“老爸你可不知道,我上周去挑战九十九碗拦门酒,特么的十碗就倒!”
何所惧“啪”的一声重重地搁下筷子,板着脸怒道:“胡闹,拦门酒是随便能挑战的么!”
何久哪里听得出父亲的言外之意,点着头自顾自的说道:“老爸说得没错,那米酒后劲真是大。早知喝不过,还不如挑战武王苗王,也许还有机会带香香回家!”
虽不知香香是谁,但张凤燕思前想后也能猜个十之七八,当下脸色一变,指着他的鼻子愠怒道:“二十年青梅竹马的感情比不上你一次外遇么?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何所惧见苗头不对,赶紧端起酒杯岔开话题,杨妹久暗踩偷掐,示意儿子不要再说了。可何久犹如开了闸的洪水,再也刹不住车,如何遇见香香,对其如何倾心仰慕,乃至最后互赠信物,添油加醋,说得滔滔不绝,神采飞扬。许是说得动情,末了,一边有节奏的敲着碗,一边附上心情感言即兴诗词一首:
落霞渐欲褪残红,暮云重,月朦胧。数点星灯,明灭几霓虹。相思悄然上眉中,风已起,夜微浓。
这无疑是一首相思阙,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此刻却突然变得那样陌生,想起自己的情路历程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毫无结果的单相思,张凤燕忍不住掩面而泣,接着泪如泉涌,哭着跑开。张凤燕父母怕女儿有事,赶紧道别紧跟而去,虽言语得体,但脸上已写满了不满。
“那个女孩是谁?”何所惧压着火气问。
何久如实回答:“余仰香香。”
“你知不知道那银坠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她。”何久有些答非所问。
“你们不合适。”何所惧的结论简洁明了。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何久的回答让何所惧一时语塞。一旁的杨妹久一直没说话,皱着眉头注视着儿子,听到这句话,突然拍案而起,坚决反对他和香香在一起。没想到何久激动起来,迎着母亲愤怒的目光果敢地顶撞,只不过才说了三句话,突然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
“什么时候底子这么弱了?生病了?”骂归骂,何所惧还是一脸关心。
“不知道,这段时间总是感觉身体里好像有只虫子在撕咬……”
“什么时候开始的?”杨妹久心里“咯噔”一下,猜测了三四分,心里默默祈祷着,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胡思乱想成真,因为那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被人送到排寨之后……不对,好像是进入夯吾寨以后就得了这毛病。”
“你一定是隐瞒了什么!从你踏入夯吾寨的那一刻开始,给我仔仔细细的说出来!”
何久嘿嘿一笑:“撒尿要不要说?”
杨妹久面孔一板,怒道:“你要是想活命,快点说!”
不就咳嗽了几声,便要人命了?没这么严重吧?但他还是将救香香的遗漏情节补充了进去。哪知杨妹久听了后脸色大变,永远从容的何所惧也不淡定了,夫妻俩互视一眼,突然一人一脚抓住儿子倒拎起来,从未如此的默契配合让何久防不胜防,拍着地面大声求饶。
杨妹久问:“是不是感觉心口痛痛的,痒痒的,想吐又吐不出来?
“是……妈,爸,你们饶了我吧,我要恶心死了……”
夫妻俩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松手,反而不停抖动双脚,何久像是一条鱼似的不停扭动,开始不断呕吐,脸色逐渐发白。
“现在什么感觉?”何所惧的声音有些发颤。
何久梦呓般的哼哼了几声,已经说不出话来,接着,他如一条死鱼一般的被扔到床上,不省人事。
望着昏迷不醒的儿子,杨妹久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担忧的说:“果然被人下了蛊!”
何所惧小心翼翼地问:“下得什么蛊?”
当年杨妹久虽非排寨蛊王,但苗族人大多会下蛊,眼见这情况,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她叹了口气,告诉丈夫儿子多半被人下了“同心蛊”。
“你也会下蛊,自然也会解蛊……”
“解铃还须系铃人,没用的。”杨妹久无奈的摇摇头。
何所惧道:“相信科学的力量!去开刀把蛊虫拿出来!”
“那你怎么不去开刀?”
杨妹久的这句话让何所惧惊愕莫名,呆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直到杨妹久洗漱完了他还愣在原地,她不禁“咯咯咯”的笑起来,半嗔半怒道:“傻不愣登的,我需要用同心蛊约束你么?”
何所惧一下子瘫坐在地,这玩笑开的……差点没被吓死!不过,这同心蛊究竟是什么玩意,为什么连老婆都这么惧怕?
杨妹久告诉丈夫,“同心蛊”又叫“情蛊”,有点类似于“桃花蛊”。但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同心蛊”是双方同意,爱的死心塌地,一旦有一方变卦,那么两个人都会死。而“桃花蛊”则是单方意愿,下咒蛊惑,一旦被破解,就会反噬,下咒者死。但通常,桃花蛊无人能破。因为自己察觉不了。
“一定是何久不喜欢香香,而香香喜欢何久,这才偷偷给他下蛊!明天去趟夯吾寨,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老子打残那苗王!妈的!”
也是气极,生平第一次,何所惧飙出了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