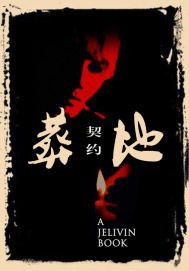其实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只有我和小花,冲出去应该不是多难的事情,但是刘东西和格格却没有我俩的本事。而我是绝不会舍他们而去,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哪里都稀松平常,有些时候也不乏无耻,但是这点底限还是有的。至于小花就不好说了,他本来就算不上是个人类,我们在他的眼中恐怕就如同蝼蚁一般,他会不会不管我们独自冲杀出去,尚在两可之间。
短短几百米却如同千万里一般。身周的格迦如同灰色的海浪,扑上来又退去。我们则像是海岸的礁石,虽坚硬不足但停步不前更胜,鲜血浸透黄土,竟然是橙色的泥泞!
我的胳膊已经不知挥砍了多少次,早已麻木不堪,定光剑却愈加轻巧,像是黏在我掌中一般,随心意而动,轻灵难言。但是人力怎可与海洋相抗,在刘东西等人的呼喝声中,我感到远处的天光尽失,视线里只剩下一片灰色。
冷寂的灰色!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道缝隙在我的视线中一闪,一个什么东西快速向我跑来,我感到了这速度对我的威胁,当头一剑就砍了出去。
小阿当曾经两次这样扑进我的怀中……我脑中一下闪过这个念头,手上的剑不由得缓了一缓。
一头羊脂玉石般的白发撞进我怀中,荏反手拦住我的腰,大喊一声:“滚!”
这一嗓子极为清亮,竟然将一片狂吼乱叫都压了下去,那些格迦一下子全都停住,颇有些滑稽的保持住刚才的姿势一瞬,便像是报完时的木偶一般退去,隐入地下。
我低头看看荏的头顶,心想果然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会又不用死了。
荏朝前走两步,转过身来很有些可怜兮兮地说:“对不起……”
我笑了起来,一步过去摸了摸他的头顶,“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该谢谢你才对,是你救了我!”
刘东西和格格早就撑不住了,此刻已经坐在了地上,小花自然没事,拄着洛阳铲站在那里很冷酷地说:“谢他做什么?都是他招来的!”
荏说话不太熟练,但是听显然是没有问题的,闻言小嘴一歪好像要哭。我心中一软,瞪了小花一眼,这事谁不知道啊,用得着说出来吗?
“别听他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安慰荏。
“狗……?”荏好像很好哄的样子,很是疑惑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陌生的词上。
“呃,那是种动物……”我解释道,但很快发现气氛不对,“咱们快过去吧,别让那边担心了!”
刘东西坐在地上哼了一声,“让他们来接我,老子走不动了!”
我踢了他一脚,“老个屁,你不是说这里是是非之地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刘东西仰着头反抗。
“管你说没说过,赶紧起来!”我骂道。谁知道荏说的话能管多久,那些格珈可不是凶性难去的凶徒,它们是正儿八经的野兽,说不定什么时候凶性发起来,我们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时候我们的车已经开过来了,就在不远处驶下路基,碾碎黄土,车轮惊心动魄的伸缩着滚过地穴,停在我们前面。
小阚哭着跑了下来,一头扎到我怀里,我使劲朝后缩,“脏不脏啊,这么多血!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爱干净一回?”
小阚却没理会我,哭了一会才冒出一句,“吓死我了你!”
“这点事就害怕了?之前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你还不早就被吓死了?”我拍了拍她的头。
“去你的!”小阚扬起脸来,“你以后注意点……”
我只能在心中苦笑,我还不想注意吗?可是事到临头又有什么办法?
卢岩迎面走过来,“你还是来了!”
我点点头,“跟这事无关,我想我还是来了!”
卢岩笑笑,“没有什么是无关的,你在里面,就不可能出去!”
我有点发愣,卢岩说话老是像个和尚,里面全都是古典哲学。
回到车里,我撕开一根能量棒一口吞了半截,刚才的恶战使我心神俱疲,脱了光了外衣,坐在座位上一阵腿软。
荏跟着我坐在我身边,我看了看他,“那些格珈不会再找我们麻烦了吧?”
“不会……”荏想了想说,“他们不愿意跟我接触……”荏又想了想,“我不知道怎么说……”
“算了,你说不会就不会吧!”我靠在靠背上闭目养神。
刘东西也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小阚开车,荏又说:“可以休息一下,它们不会再来了!”
小阚回头看我,我挥了挥手示意她开车,强打起精神对荏说:“我们现在只求稳妥,不能有失,这个地方离它们太近,在这里休息,不放心!”
后来这群格珈再也没有出现在望远镜的视野里,但我知道,它们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
经过这件事情,我对荏的想法发生了一点变化,之前的时候我一直把他当做一个值得可怜的孩子,而今天才发现了他真实的力量,如果他当时动念,那群格珈完全可以把我们彻底消灭,在我的想法里面,这绝不是一个格珈的孩子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像是一个农夫的孩子只能是孩子而已。能做到这一切的,只能是一个王子,那种生来就躺在所有人头顶上的金羊毛中用同样黄金做的勺子吃着上天赐予的乳汁的人。
在路上,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止一次地从我身边袭来,让我不禁深深的怀疑,这一切全都在荏的掌握之中,他能够让我们的世界灭亡,也能够让它重生。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幻觉,不过我一直在发烧,这种热度不同以往,仿佛是有种东西在我的心中灼烤,让我如同一个颗星球,炙热的像要裂开,却又孤寂的行驶在一片空寂之中,周而复始,不知其踪。
过了四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依然是日落出发,日出而息,日子仿佛一直在重复,道旁的黄土却越来越厚,沟壑纵横如同千年的岁月。
午夜的时候,刘东西对我说,前面就是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