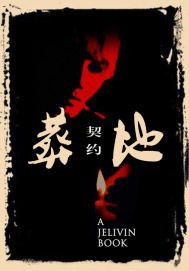我并没有感到多奇怪,虽然并不知道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卢岩既然就是当年的卢源,那他和张国庆认识也不足为奇。毕竟曾一起出生入死,各人境遇不同,只能说是各自的造化了。
卢岩手拄鹿角,面对那张国庆跳出去的院墙默立不语。我走到他背后,试探着问了一句,“卢源?”
卢岩猛地扭过头来,“你怎么知道?”
“冯教授的信里提到过会再见到卢源,之前我们推断过张国庆应该就是这个怪物,从冯教授的语气中我们觉得又好像是卢源。但是我和刘东西都觉得卢源这个名字和你的名字很像,而且你对这里太熟悉了,所以我们怀疑你就是卢源!”
我们这个推断是十分武断甚至说臆断的,此刻说出来自己都觉得漏洞不少,但是卢岩并没有出口反驳,而是把头转了过去,仍然沉默地看着墙头。
“我不是!”半晌之后,卢岩淡淡抛下一句,转身就走。
你不是?不是卢源难道是张国庆?我紧紧跟上,心中疑惑不已。行不几步却突然释然,凭什么卢岩就得是当年三人之一?卢岩不能就是卢岩吗?
我觉得自己又陷入了那种自己很讨厌而又无法摆脱的阴谋论思想之中,一定要把来历神秘的卢岩纳入非人类的范畴。
卢岩信步走上台阶,进了正屋。我跟在他后面,心中很有些发毛。这家伙难道要打开地下的暗道吗?然后是不是我们就再次进入暗道,通过小楼和井,重新到那个广博的地底世界,然后在一连串的死生经历之中,再次回到一个建木上的夏庄?这一切是不是会像看画的儿童一般,将无数的自己纳入画中,形成无数的微观世界?
果然,卢岩进来之后直接将一个兵器架子放到了那个方方正正类似于塌的座位上,歪着头想了下子又把手上的鹿角插了上去。这才是发动了机关,一阵喳喳声之后,那个熟悉的暗道口又出现在我面前。
“卢岩你干什么?这地方通哪里?”
卢岩似乎有些茫然地抬头看我一眼,“通地下!”
“地下什么地方?我有些犯晕,地下不就到了下一个平台了?”
“还是这里!”
“还通到这个地方?”我感到心中的猜测变成了现实,难道路卢岩要我下去,将余生托付给这个永无尽头的死循环吗?
“你不要去,卢岩,咱们上去找到石骨就回去!”
卢岩回过头来道:“这里就有,骨场已经毁了,只有到里面的骨场去找!”
我这时候脑子有些晕了,听到他说能找到石骨,答应了一声就要跟着进去。那种阴冷潮湿的空气就要扑到脸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卢岩,我们进去之后还能回来吗?”
卢岩停住脚却没有回头,只有声音传过来,“不能!”
不能回来那我取得石骨还有什么意义?
“卢岩,我不去了!”
“为什么?”卢岩依然没有回头。
“这边我还有老婆和朋友,刘东西还在这边!”
“他们也在那边,那边就是浩劫之前的世界!”
浩劫前的世界!离开人世这么久,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外面的人类世界正在遭受一场浩劫,城市、农村和狂野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无数灰白色的幽灵在之中游荡。
那个浩劫前的世界!那个充满了生命和语言的世界,那个日出后和夜幕中都同样充满生机的世界,那个充满了欲望和丑恶嘴脸的可爱世界,那是多么美好!
常监、王哥、老曹、乔大路……这些早就离开的人,难道还好好的活在这里面的世界中吗?这一瞬间,我心中被一种极为迫切的情绪所充满,恨不得马上就过去,回到过去的生活之中。
但是这边怎么办?小阚还在省城生死不知,刘东西和王大可还在那山壁的石洞中等我们回去,难道我能就这么放下他们,如此自私地去那个世界中吗?
不知不觉,我已经下到了楼梯转折之处,地窖中点点长明灯光就在眼前了,我感到这光里的异世味道,猛地警醒过来,停住了脚步。
“卢岩,我不能去!这个世界我放不下!”
卢岩一下站住,静立了半晌却没有回头。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虽有不安但却绝无忐忑,我绝对不会跟着他去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虽然我的世界已经破碎,但我绝不能离开!
过了很久,卢岩才缓缓道:“你想好了,我们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想好了……”
卢岩转过身,脸上竟然好像还带着一些笑容,“那我们回去!”说罢快速越过我步上台阶。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通往新世界的通路一眼,回身步上台阶。
卢岩看我出来,飞起一脚将那扇兵器架踢走,那座椅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兵器架翻滚过后竟然毫发无损,暗道口等了一会又缓缓合拢,地面上严丝合缝,一如从未打开过一般。
卢岩重新抄起那柄鹿角般的兵器,大踏步走出门去,背影带着与他的沉静气质毫不相称的豪迈之气。但我还是在其中看到了一丝不同于以往的疲惫甚至是委顿,不知道他到那个世界中是不是就可以复原,他是不是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拖着伤体,跟我留在了这个破碎的世界。
从上的这个小山来之后,我所经历的一切只能以匪夷所思来形容,之前那些所谓墓兽,地质结构等等等等都可以用世界真奇妙来形容,而现在这些时空方面玄之又玄的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该不该将其归结到这个世界之中。
出得正房,穿过已经变成一片石子地的庭院,走出高大的门楼向主干道的方向走。
“卢岩,我们怎么上去?”
“飞上去!”
“这个地方你怎么这么熟?你真的不是卢源吗?”
卢岩不再回答,只是一味朝前走,手中沉重的鹿角将脚下夯的坚硬如石头般的白膏泥地面犁出一道浅沟。
我也不再说话,在这鹿角犁开地面的细小声音中默默地向前走,这声音沉默而又决绝,在我耳中,像是割裂了什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