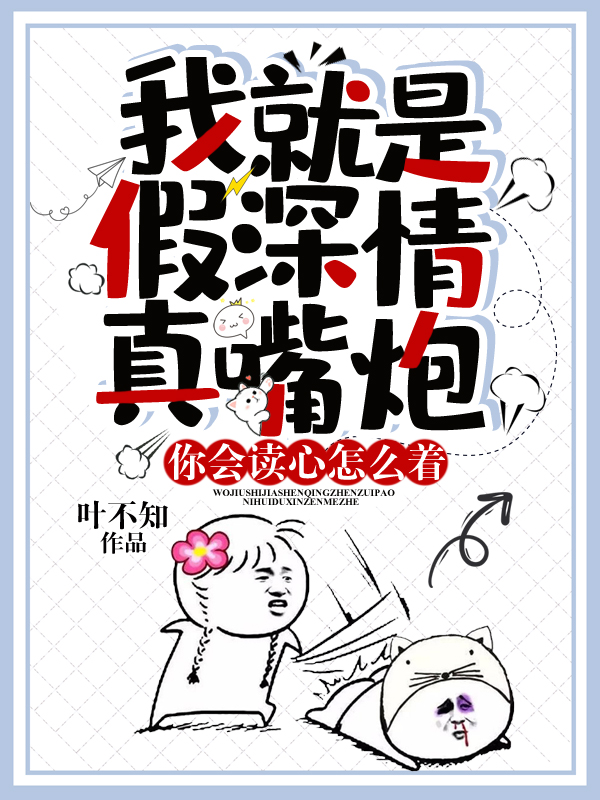秦禾在主屋一连住了五天,直到江天佑休沐回家那天才搬到西院。
因着她被秦家虐待的事,江天佑发了好一顿火,赶着夜色还去秦家砸场子。容氏也不制止,看着相公套马车,她就抱着秦禾站在一边,眼睛里亮晶晶的,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容氏迫不及待的到秦家去闹一出,当年唐家夫妇如同天神般把她解救出来,如今赶上自己做英雄的时候,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可激动坏了。江家老太太破天荒的没制止,反而借口头疼,把这事划过去了。
“昨日在学院里接到爹捎的口信,话里话外还是生大姐的气,这次去是想让我把大姐接回来,等他忙完了少不得一顿家法伺候。”江天佑对这个姐姐感情深厚,只是因着耳聋,每每上秦家的门就被调笑一番,大姐也就不让他再上门了。
只是,这江家不敲秦家的门,秦家也不见有人来敲江家的门,姑娘嫁过去六、七年,过年过节没有侍奉就罢了,就连闺女的面都见不到,女婿每年初二只带着外甥女来拜年,寒暄两句抬脚就走……
因着这事,江老爷子每每都气的吹胡子瞪眼,江老太太就在一旁抹泪。
“舅舅,我娘秋天里死了,死的时候流了好大一摊子血,姨娘怕我回舅舅家告状,就五两银子把我卖给隔壁县的春风楼做丫鬟了。”秦禾窝在容氏怀里,听到舅舅提起娘,这才开口告状。
“我婆说,我娘死了不要紧,还把弟弟害死了,这样的女人不能入祖坟,还是我爹跪着求我爷,才把我娘安葬了。”
“春风楼的妈妈对我们很好,给我们饭吃,还给我们做新衣裳。我跟她说我外公是清江县衙的师爷,她还派人把我送出了城门,让我回来寻亲。”
秦禾平淡的说着往事,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江天佑越听越心惊,手里的马鞭越挥越快,迎着冷风,眼圈也红了。
容氏捂住秦禾的嘴,偷偷的给她使眼色。
从秦禾的话里,容氏猜测大姐是难产而亡的,大姐夫是庶子,在家里没有话语权,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卖去妓院。
春风楼可不是什么好去处,那可是十里八乡最出名的妓院,每年从楼里抬出来的女尸数不胜数,大多是被有特殊癖好的恩客们玩死的,衙门去调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那才是真正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笔银两买断性命的地方。
“你这个混蛋!”江天佑停稳马车就冲进了秦家米铺,一拳就挥上了秦六郎的脸。
秦六郎是庶子,家里的好买卖无权沾手,整日里就坐在米铺里守店。此时他已经准备收摊了,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打蒙了。
“幺弟,你怎么来了……诶诶……这是要干什么?”秦六郎双手抱着头,防备着江天佑的拳头。
“秦六郎,你这个窝囊废!你还好意思说!一个大男人,护不住妻女,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
“幺弟你说什么,我都听糊涂了。”秦六郎面色如土,却还是装傻充楞。
“姐夫,你就别瞒了!阿禾五两银子就被你卖了,得亏这孩子机灵,报出了爹的名讳,这才被那不想惹事的人家给放了出来。容氏拉住丈夫的手,一脸气愤的指责:“小小的姑娘靠着一双脚从外县走回江家,冰天雪地里穿着破烂衣服倒在江家门口……”
容氏说着说着就带上了哭腔。
秦六郎见状也捂着脑袋蹲下来,双手扯着头发,激动的说:“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要是不把阿禾送出去,我姨娘就要被太太发卖到窑子里了。”
“你闺女被卖到窑子里就不心疼?你那人老珠黄的姨娘卖到窑子里就心疼了?还是你的生母做了花娘,丢了你这个秦家六郎的脸了?”江天佑听到这话,一脚就踹到了秦六郎的脑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们要把阿禾卖到妓院去,我真的不知道……”秦六郎被踹到地上,捂着脑袋蜷缩在一起,呜呜的苦。
“舅舅,算了吧!从今儿个开始,就当我没有这么个爹吧!”阿禾从马车上探出头来,泪流满面却是不愿往秦六郎身上多看一眼,像是眼前有什么腌臜物一般。
阿禾不知道春风楼是妓院,也不知道妓院是什么地方,只是听舅舅说起“花娘”,心里一突突。想起秦家老太太平日里就是这样骂娘的,什么不要脸的花娘,躺在床上就勾的***不住脚的货色……
每每遭了秦家老巫婆的骂,娘就是一副羞愧欲死的模样,整宿整宿的流眼泪。
阿禾再联想起春风楼里妈妈教的东西,那身躯扭动,表情管理,喉咙里压制的声线……恨不得立刻死在马车上。
“你以后别踏上我江家的门!”江天佑向来是温文儒雅的样子,此时眼圈通红,面目狰狞的样子,显得可怕的很。
“大姐夫,我们受老爷子的托,也得把这件事办妥。你也别磨蹭,快些把断亲书写好了拿来,我们就当没你这门亲家。”丈夫唱了白脸,容氏就唱起了红脸,一软一硬,哄得秦六郎二话没说就写了断亲书。
回家的路上,雪渐渐停了,积雪齐齐整整,把道路照的亮亮堂堂。
江天佑脸色铁青的赶着马车,心里盘算着把阿禾的卖身契赎回来,以免夜长梦多。容氏搂着阿禾唏嘘不已,这小小的姑娘遇到这样大的事,却是一声不吭,实在让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