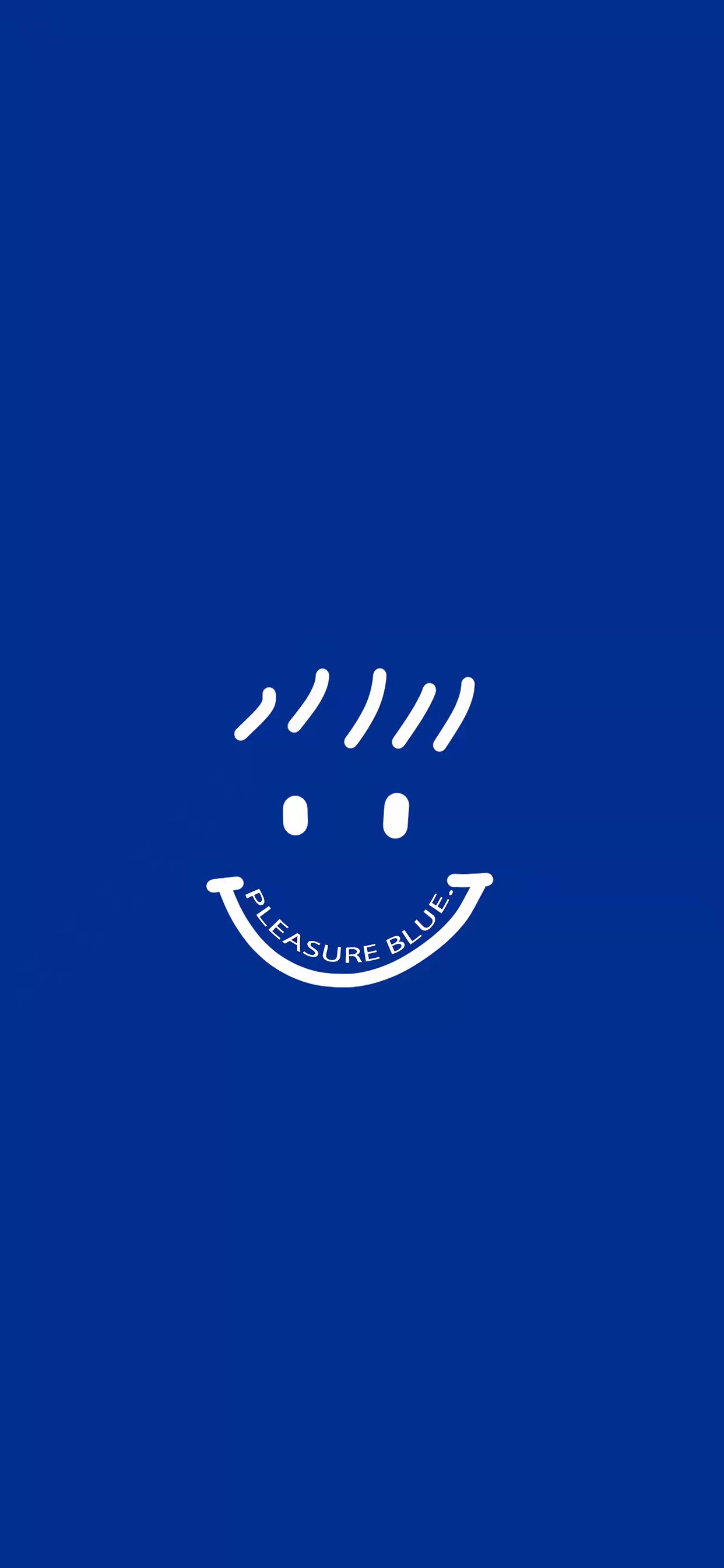易天辰微点了下头:“她应该都知晓了,但她并没有从中干涉。”
我用余光看他,问道:“其他几位干爹干娘也知道了吗?”
他淡淡道:“这个臣不知,不过她应该还没有告诉他们。”
宣室中并并无他人,二娘斜靠在椅子上,左手撑着下巴,听到开门的声音,掀了掀眼皮,懒懒的向门口看来。
“馨儿,你回来了,过来给二娘捏捏肩膀。”她边说着边打了个哈欠。
我屏退了左右,随即走到她身边,很是听话的帮她捏起了肩膀。她若是暴跳如雷将我蹂躏一番,我倒也觉正常,但她如今竟这般冷静,这般严肃正经,我反倒是有些不习惯了。
“馨儿,”她轻拍着我的手背:“你也好久没有出过宫了,这趟出去玩可还开心?”
不等我回答,她便偏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皱眉道:“不过看你这神情似是玩的不怎么尽兴啊?”
我低垂着眼眸,没有回答。
“难道是莫逸城没有照顾好你吗?”
“不是。”
我心下一沉,手中的动作也慢了很多,不知为何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想要为他辩驳,也会因二娘无意间的轻慢而替他感到心疼。
“馨儿,不用捏了。”二娘拉着我坐到了她的身侧,椅子本就宽敞的很,即便是我们两个一同坐下也不会觉得拥挤。
“好久没有这么早起了。”二娘捏了捏眉心:“当皇帝的也够累了,馨儿登基这几年,怕是早就将你累坏了吧。”
我淡淡道:“已经习惯了。”
“二娘这些年虽不在朝中,但对朝中的事还是有所而闻,这些年你打理的也还算不错,百姓安居乐业,百官各司其职,即便地方发生灾祸,你也会派人及时营救,将损害降到最低,先帝的一朝臣子,贬谪的贬谪,外调的外调,如今就剩国师和太傅,一朝天子一朝臣,你这么做并没有错,你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很好,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不伤及百姓,二娘和你几位干爹干娘都会配合你。”
我出声打断她:“若是我做错了呢。”
二娘执起我的手,语重心长道:“对与错从来没有个标准,何况你都没有做又怎会知道是对是错?”
我又道:“那你们会阻止我吗?”
“我们若是拦着你,日后你有了不顺心怕是要怪二娘当日的阻拦,”
她说着轻拍了下我的手背,目光柔和的看向我:“馨儿如今已经长大了,也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了,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二娘都不会拦着你,即便是错的,你还年轻,改也来得及。”
我低下头,余光瞥到案板上摊开的奏章,上面写的是将被问责的人员名单,低至各部门小吏高至三公九卿,皆在其中。
我伸手抽出奏章,扫了眼上面的名字,听二娘说:“别人都以为这满朝文武皆是丞相和国师的人,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不动声色的培养了这么多完全忠于自己的人。听说还有人都潜伏了整整五年。”
“是啊,”我附和一句:“整整五年……”
五年的时间让莫逸城和尚清跃居一品,也让如易天辰这样的人韬光养晦,静待时机。
那年的进士国师笼络了近半的好利者,剩下的则归在了太傅门下,那一届进士里凡是国师看上的,我都提拔了;凡是我看上的我都尽力打压,安置在最能磨砺品性却又最不起眼的位置上。
甚至还将一部分人外调到偏远的地区历练,直到这些人慢慢的淡出所有人的视线,学会耐住寂寞,收敛锋芒。
离开帝都之日,我便让易天辰暗中一一接触这些人,将他们组成只听命寡人的王党,如今时机已到就待他们将莫党,楼党乃至国师取而代之。
“馨儿,你不仅像你父君掌控欲强,同时又很向你二爹能隐忍。”
二娘揉了揉我的发心,轻声叹道:“没有想到你为了夺回掌控权,整整五年的时间竟能做到引而不发,但其实你一点也不开心是不是,整日活在算计中,能有几时的笑容是发自真心的。”
我放下手中的折子,缓缓闭上眼睛,依偎在她的怀里,这几日的发生的事情让我倍感倦怠,父君说过御臣之道便是要先学会疑才能学会信,江山社稷并非儿戏,我还没有学会完全相信一个人,又怎会轻易托付他人,即便那个人是枕边人。
二娘看了我一眼,问道:“你现在还打算废了莫逸城的丞相之位吗?”
“他既要为凤君便不能在当丞相了,陈国的祖训,后宫不得干政,寡人虽是个女帝,但也不能有违祖训。”
二娘手中的动作一顿,笑道:“其实我想问的是,你可还打算立他为凤君?”
“二娘为何如此问?”我疑惑道。
“方才见你神情不悦,二娘还以为是他惹恼了你,”她说着一顿,挑眉看了我一眼:“你若是不喜欢他,可会改变主意不再立他为凤君?”
我摇了摇头:“如今已是昭告天下,寡人一言九鼎,岂能失信于天下,而且如二娘所言我已长大,不能再向儿时一样依靠自己的喜恶行事。婚期会如期举行,只是……”我小声嘟囔着:“心态怕是已无法向从前那般了。”
二娘道:“你喜欢他吗?”
“喜欢与否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别过脸,低垂下眼睑:“并非所有人都如二娘那般幸运,有二爹一生宠爱与陪伴,我既生在了帝王家,就不应该苛求太多。”
二娘沉默的看了我一会,想要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而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念了声:“馨儿,你啊……”
二娘走后,我吩咐小银子将易天辰召进了来。
易天辰躬身道:“果然如陛下所料,密室中的资料是被楼御史销毁,如今漕运亏空的证据,除了丞相和楼御史怕是再无任何指向了。”
我问道:“朝中现在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