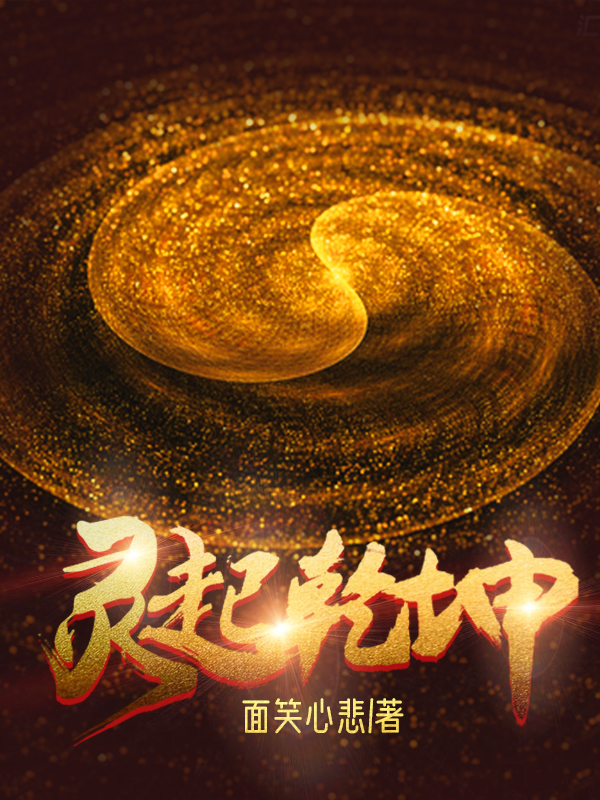次日一早,白肚霞红,轻风浅霜,屋中面憔体虚的母亲,喝了一碗开水,眼睛湿润,看向怀中的熟睡的我,难心的流着眼泪。
父亲在往院中的木推车上搬着家当,姐姐在封着窗纸。
“不能哭,眼睛会落下病的”。父亲朝母亲说道。
“三柱,我们真的要走么?我们要去哪里?”
父亲顿了顿,没有说话。
我们又能去哪?沿街乞讨?寒冬腊月又不比春夏天暖,更何况还有虚弱的母亲和刚经过一劫的我。
在村子里是呆不住了,父亲说。
要不我们报警吧,让公家出面解决,我们走了大妞去哪里上学啊,她还那么小,就跟着我们流落街头,更何况还有二狗子。
话音刚落,门外闹声迭起,只一会拍门声变成撞门声,赔偿声夹杂着咒骂声,还有几个正趴在土院墙上向院内张望。
小三子要跑啊,一人急切的叫着,话音才落人群就撞开了院门,“噗叉”一声,半扇门倒向院内,灰尘飞扬,熙攘的人流拥到院中看着推车上的家当,不由分说抢夺推搡,抛扔抽拽,抢夺后的院子一片狼藉,没有抢到东西的冲向屋内,搬抬背抱,敲踩磴跺,尽显人性之恶极,长彰世道之沦丧。
父母相向而视,没有言语。
后到的人看到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敲窗踢床,污言秽语。
看向狼藉的家,母亲望向父亲,说道:“走吧,三柱”。
父亲没有说话,点上一锅烟。
姐姐也没有贴窗纸的必要了,也坐在床前。
父亲抽完最后一口烟,在地上敲了敲烟斗,说了一句:“走。”
就把母亲背到没有轮子的推车上,之后把我抱到母亲怀里,把仅剩的一床被子盖着娘俩。
苍白的言语无法形容父亲那刻心中的滋味,是无奈,无助,酸薄,冷漠,还是人性。或许都不重要了,或许对父亲来说母亲和我都活着仅这一点就够了,仅这一点就足以支撑父亲的心。
父亲拉着没有轮子的推车,木车过后黄土地上留下两道清晰的车痕,好像是这个家跟这里的一切划上界限的印记。
姐姐帮着父亲一起拉着绳子。走在村路上更有甚者向这刚刚经历磨难的一家扔着烂瓜坏菜。眼中充斥着对待囚犯的鄙夷。
父亲没有停下,一家人艰难的往前走。
姐姐委屈你哭着,肩膀上的绳子依然紧绷,母亲蒙着被子,紧紧的抱着我。
“不能让那个妖怪跑了”,有人叫道,路边众人听后,开始来扯被子。准备把我揪出来,父亲见状慌忙停下,扑向我和母亲。众人见状对我父亲拳打脚踹,我父亲始终纹丝未动,任凭其毒手。
“全都住手”,一女人,歇斯的吼道。
众人一惊,循声望去看到秀芹站在推车前面,面色凌厉。
“你们真是一群畜生”。秀芹切齿怒目。
“谁敢阻拦,我秀芹此生绝不对其施以针药。”天地作证,我说到做到。
众人皆惊,纷纷退去,只因她是村中唯一医者。大灾小病,谁能逃过。
“三柱”快起来。秀芹急切的叫着父亲,父亲没有回音。
母亲也推推父亲,父亲如同一个雕像,没有回应。
“三柱,你别吓我。母亲快急哭了”。
秀芹手指探向父亲的脉搏。
“你们全都站住,把人打死了,就这样走掉么?秀芹朝着见势不妙,想要逃跑的众人吼道。”
“哇~哇”婴童哭声骤起。
母亲急忙往怀里看,婴童已被惊醒。秀芹也看向婴童。
众人见此空档,立时做鸟兽散。
“无知刁民,哪里跑!”一个熟悉的声音吼道。
这声音村民都很熟悉,知道是瘸子孙来了,虽然害怕,但是好像出人命了也顾不得许多,慌不迭的跑回家中,掩门插栓。
瘸子孙正要前追,秀芹向瘸子孙叫道:“快来救人。”瘸子孙倒也识趣,收住脚步,他也细身思量过,他也没这个能力把一群众人怎么样。
瘸子孙回过头,正要开口。“拉车”秀芹对其说道。
瘸子孙悻悻的走到车前,麻利的套上绳索。
母亲搂着父亲,叫喊着,父亲依然没有回音。母亲急得哭起来。
“行了,三柱。人都走了。”秀芹趴在父亲耳边轻声的说道。
父亲睁开眼睛,说:“都走了?”母亲破涕为笑。
正要起身,秀芹按着父亲说:“此地不宜久留”。瘦弱的她拖着父亲,艰难的前行。
村路上只留下两道赤luo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