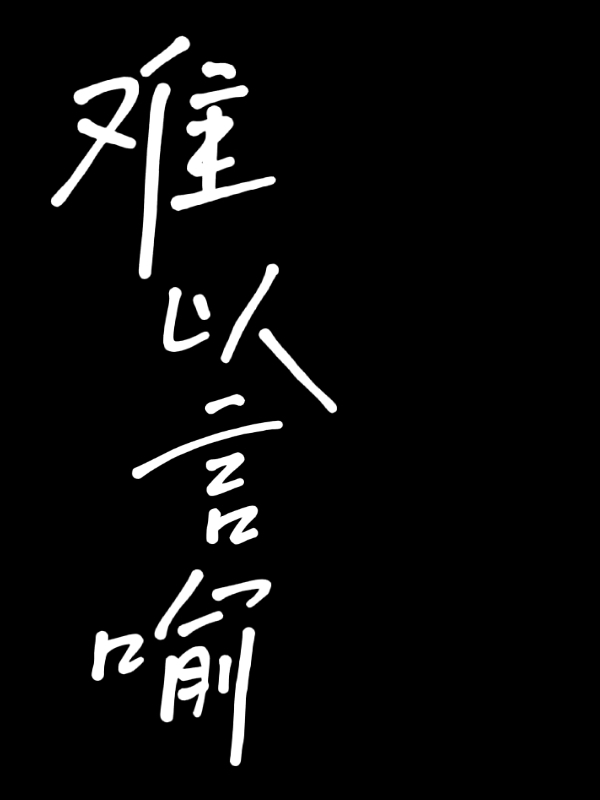窗外已是天光大亮。
林璧月怔怔地望着那片明光,许久后才恍觉自己已经醒了。
怀里的汤婆子已经是冰透了,她哑着嗓子唤了两声“扶春”,却没有得到回应,无奈下穿着单薄的中衣就坐到镜子前梳妆。不久后她的丫鬟扶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却发现她已经醒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来,拿起梳子为她梳洗。
主仆两人都没有说话,四下里寂静无声,但外面却隐隐传来热闹的欢笑声,显得“此时有声胜无声”。扶春觉得这屋里头清静得就像广寒宫,森森的冷,却不知道要不要出声打破。
璧月倒是没觉得有什么,看着铜镜里的扶春一下一下地为她梳着头发觉得有些无聊,打算戴上一个桅子花耳环的时候却被扶春拉住了:“小姐,今儿是小侯爷休休的时候,您第一次见小侯爷,纯白不合适。”
璧月听了便取出一只石榴石的耳环对着铜镜戴上,一边问道:“今儿已经是除夕了?”扶春拿起几只簪子麻利地为璧月簪上:“是啊,小四他们被夫人指使得团团转,府里到处都是窗花和对联,可热闹了呢。穿夏看那边热闹欢喜得不得了,也跟在夫人身边瞎凑热闹,还折了好几朵开的正好的腊梅簪在鬓上,结果得意过头了,一不注意滑了一跤,鬓发都摔散了,好不凄惨。”不巧穿夏正好进来,闻言拔下一只木簪便追着扶春跑:“扶春你在小姐面前胡说八道些什么!看我不戳烂了你的嘴!”
室内一阵欢笑声,仿佛外面的冰块都要化了。
忽的外面又来了人,看着璧月只着中衣就皱着眉将身上的衣服披在璧月身上,沉声呵斥道:“你们两个简直胡闹!主子没穿好衣服,你们不知道先给主子穿好,反而先顾着自己玩闹!看我不禀明了嬷嬷,重重地罚了你们的月钱!”扶春和穿夏自知理亏,停下动作赶紧去把璧月的外衣斗篷等拿来。璧月这才觉得有些寒,咳嗽了几声,穿得整整齐齐了之后,软绵绵地央着那女子:“横秋姐姐,这次就不要告诉嬷嬷了吧。也是我不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纵着她们玩闹。今日毕竟是除夕,稍稍放纵一下也没什么不好。我看她们平日为了我都憋坏了,今日就松一松吧。”横秋沉吟了一会儿,妥协了:“下不为例。”转身便麻利地打开了汤婆子添热水,一边絮絮叨叨地念叨着璧月。璧月也不烦,安安静静地听着。穿夏偷偷摸摸地对着横秋的背影做了一个鬼脸,对扶春做了一个“老气横秋”的口型,对璧月抱拳感谢,两个人都被逗笑了。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进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只水头极好的青色玉簪。璧月奇道:“获冬姐姐,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获冬走
到璧月的跟前递给她:“这是小侯爷身边的无惮给我的,说军中尚有些杂务未了,恐怕午后才能到呢,这只岫玉簪先行奉上。”璧月见了爱不释手,直接把它簪在了最显眼的地方上,又在梳妆镜前坐了好一阵,这才带着四大丫头去姨母谢孟氏处请安。
到了谢孟氏所居的同安堂,璧月与谢孟氏和谢孟氏之女谢十鸢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
不多时便到了午饭的时候。谢孟氏第一个坐下,她的三个丫鬟从贤、从恭和从俭分别为主子们准备碗筷,林璧月和谢十鸢侍立在谢孟氏两侧准备为她布菜,从德站在谢孟氏的身后正在为她按摩肩膀。鹦鹉阿柯还大声地叫唤着“夫人吉祥”, 让谢孟氏很是欢喜。想到今天是儿子回家的大喜之日,眉间的那些深愁便如山间岚烟一般消散了,只是享受着下人的服侍,一心一意地等着小厮来报小侯爷的消息。
林璧月正和谢十鸢说着话,忽听见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猜是去拿花雕酒的赵小二回来了,就侧身看去,谁知却正好与一双清亮、陌生的眸子相撞。
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长得极高极瘦,英气逼人。璧月愣了一下,随后想到这人该是小候爷,连忙施了一礼。小侯爷看着璧月倒是愣得更久,回过神来的时候耳根都红了,匆匆忙忙地还了一礼,再随随便便地和妹妹打了招呼,便蹑手蹑脚地向谢孟氏走去。
那厢谢孟氏正让从德再用力些,从德见了小侯爷便告退一旁了。谢孟氏还以为这姑娘使脾气不肯干了,便柔声道:“好姑娘,让周嬷嬷给你发两倍的月钱,你就多下些力罢,我今日肩疼得厉害。”话音未落“从德”便揉捏了起来,等到谢孟氏舒服了的时候才开口道:“夫人说的双倍月钱可不能反悔。”谢孟氏听声音不对,回头望去,顿时惊喜得不得了:“我儿回来了!快让母亲抱抱!”十鸢看着兄长抱着母亲,本也想上去抱抱他们,想到这里只有林璧月的亲人不在,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转头看她。
璧月看着那对母子欢喜极了的样子,显得有些落寞和局促,一双手在身前轻轻地绞着帕子。十鸢看着她的模样很不忍,就拉过她的手开心的说:“大哥回来了,我们可就有的玩了!斗蛐蛐儿捉蚂蚱,扎小灯笼做点心,就没有他不会的!待会儿我就叫他给你扎个灯笼,再捉几十只灯火虫放里头,给你夜晚读书用!”
看着十鸢如数家珍的模样,璧月也稍稍放下了那点心事,含着笑说:“这样看来,这位小侯爷居然是无所不能了?”十鸢学她大哥的表情皱着鼻子说:“那倒也不是。大哥最怕读书。他幼时侯爷就是请出家法也没能让他规规矩矩地读书。侯爷若是骂他,他就敢呛回去!娘亲常说他是‘混世大魔王,如来都压不住的齐天大圣’!照我说,他喜动你喜静,你俩真真是绝配,娘亲当聘了你做儿媳妇,这才压得住他!”一旁不住地往这里瞥的小侯爷登时害羞了,说:“谢十鸢你是不是欠收拾了!什么胡话也往人家姑娘身上编排!待会儿我就在我同营的兄弟里找一个,把你嫁出去!”
谢孟氏心里头乐的不行,想着“十鸢这孩子,想法倒是不错”,为着侯夫人的身份还是强作矜持道:“十鸢,你哥哥说的是,要不是阿月脸皮厚些,羞都要被你羞死了,快别这样说。陵儿,这位是你珍姨的女儿,闺名叫做璧月的。”又上前来握着璧月的手,柔声说:“这位是你的陵表兄,大名叫玉陵,托着先侯爷的福,在燕京军里头做了个骠骑将军。厚着脸皮说,也算在军队有个一锥之地了。要是有事情,就去找这个大哥。都是一家人,不要客气。”
两人互相行礼,璧月含笑称是,谢玉陵红着脸不住地瞟着她,感觉心脏砰砰地发着热,谢十鸢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暗自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