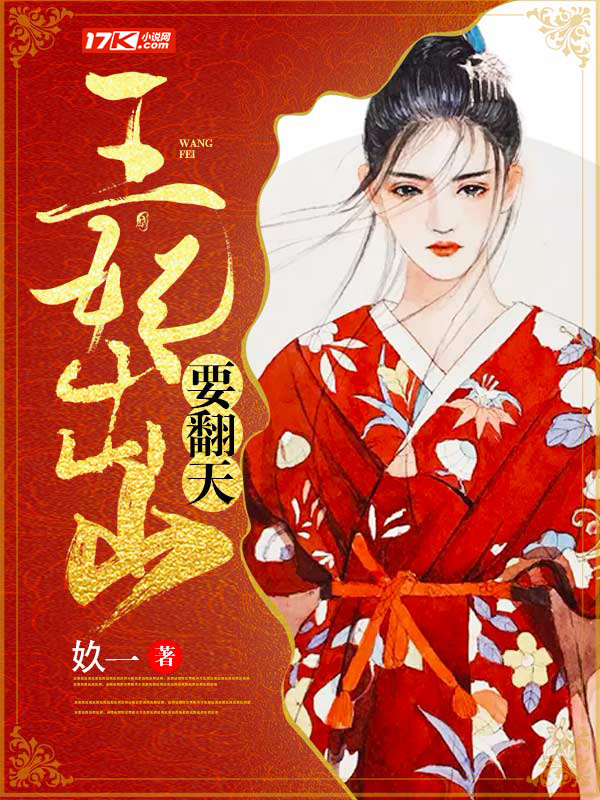宁州城中,政府与学生拉锯数日,局势愈发混乱,街头巷尾处处戒严,教授学生们仍无畏无惧地上讲演,游行的学生与军警的马队冲撞,时不时有朝天鸣枪的声响,学校门口常常硝烟弥漫,大批大批的学生被抓捕进监狱,又激起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反抗中……
春日回暖,正是牡丹盛开的时节,陆府中一派花红柳绿的安宁。陆青沐的小院里,扎了许多花架子,又在廊前檐下摆了许多瓷盆,处处供着牡丹花,黄蕊点金,叶若翠羽,花瓣艳丽,娉婷怒放。
这日,陆青沐正邀了沈涵初在府中赏花。她一面哄着怀里的婴儿,一面对沈涵初笑道:“别的倒也寻常,就那株二乔,同株同枝竟开出了两色的花朵,实在是新奇;还有那株玉楼春,这绿色的牡丹我是第一次瞧见,看那色泽,可真像块翡翠。”
沈涵初见这满目争奇斗艳的花儿,赞道:“怪不得古人有诗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秦夫人这儿的花,可名动宁州。”
两人赏完花,吃了下午茶,陆青沐又约她去买衣料。
车子开到一家叫玉祥绸缎庄的店铺前,那店门却是半掩着。
那玉祥绸缎庄和陆公馆常做来往,对陆家的人,自然是相熟的。陆青沐一进门,绸缎庄的几个伙友便簇拥而上,将新进的料子都捧了出来,一色铺成开来供她挑选。
那绸缎的颜色热热闹闹的,像是被陆府中牡丹群花洇染,青沐挑着衣料,几个伙友鞍前马后,陆青沐见沈涵初只在一旁淡淡地扫了几眼,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致,便道:“想来这里的衣料入不了夫人的眼,咱们要不去永安路逛逛?”
沈涵初道:“怎会,这里的衣料挺好的,只是现下也不缺衣饰,倒不知买些什么。”
“那我就斗胆替夫人挑些了……”青沐捏着帕子轻轻一笑,挑出一匹淡湖色春绉道,“这颜色很配夫人的气质呢,做单衣一定好看。”
“天气还没大热,秦夫人想着做单衣了?”
陆青沐笑:“这宁阳的天气,春短夏长,要热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还是得趁早备着。”
两人正说着话,那绸缎庄的掌柜已迎了出来给陆青沐请礼。
陆青沐问道:“钱老板,你们今日怎么半开着门做生意,是不欢迎我这老主顾了吗。”
“呦,夫人你可别冤小的……”那钱老板叹了一声道,“还不是那些学生们给闹的,鼓动着这几条街的客商都罢市了,偏偏政府又强令我们复市,不然就增加税赋,嗨,难为我们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好半开着门做生意了。”
青沐闻言,蹙了蹙眉道:“这些学生,三天两头地这样闹,真不安生。”
那钱老板做着陆府的生意,此刻自然要站在陆家这边,帮嘴骂道:“可不是吗,一个个的不好好上学,尽是添乱,咱们这儿还算好,宁丰铁路那边,几千个工人被鼓动得齐齐罢工,搅得铁路线都瘫痪了。”
沈涵初闻言,却心神不定了起来。她心不在焉地与陆青沐挑了些料子,那绸缎庄的伙计便忙络着去包,她二人在一旁坐下等着,早有伙计奉了茶点上来。
二人正喝着茶,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之声,沈涵初不由得往外看去,喃道:“怎么突然间这么多游行的学生?”
“早就见怪不怪了,夫人莫担心,咱们逛咱们的。”
沈涵初收回了目光,忧虑之色已显现到脸上。
没一会儿,竟又跑过一大片荷枪实弹的警卫兵,街上顿时又躁动起来起来,一时间人仰马翻的,这会儿子连青沐都忍不住瞧出去了,却见为首骑马的那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她心下一惊,跑了出去,朝着那边叫了起来:“爸爸,爸爸!”
陆德全勒住了缰绳,目光往这里一扫,纵马往这里跑来。
“沐儿,你怎么在这儿?”
青沐道:“我出来买衣料呢。”
陆德全忽然脸色一变,道:“赶紧回去,现在街上乱得很。”
“爸爸,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连您都出动了?”
“今日各大学校联合了几千人的总游行,据情报说是去公署大楼前闹事儿了。”
青沐诧异道:“他们也太大胆了吧,怎么闹得这么厉害?”
“必是有南方乱党的人混在其中煽动,顾督军下了令,领头的乱党分子一旦抓获,当场击毙。这帮学生,越来越胡作非为了,非得死几个人才能平息!”陆德全说着纵马往回跑,一面嘱咐道,“不与你说了,你赶紧回府去,千万要小心。”
青沐忙点了点头,一面也喊道:“爸爸,您也小心!” 陆德全已纵马跑得老远。
沈涵初虽未走出铺子,陆德全的话却听得清清楚楚。
青沐转身回到绸缎庄,转达了陆德全的话,又道:“今天没陪夫人尽兴,改天再约夫人。”
两人分别后,各自坐了汽车回府。
沈涵初坐在汽车上,看着街景飞快地向后退去,她心里却发阴郁起来,那游行的队伍中,想必会有许多她昔日的学生,而下令要抓捕他们的,又是她所谓的丈夫。
汽车缓缓驶着,转过一条街,与那游行队伍只隔了一条巷子,沈涵初的目光频频往那边看去,只见浩浩荡荡的队伍,学生们一个个举着标语旗帜,振臂直呼:
“解除报禁!释放被捕学生!”
“反对内战!废除密约!”
“反对专制!卫我国土!护我国权!
忽然她觉得胸口猛然一窒,三魂顿时去了两魄。
队伍前方,楚绍南赫然在列。
陆德全的话一下子跳到脑中:“非得死几个人才能平息!”
她再定睛看去,汽车却一拐,什么也瞧不见了,那一瞬间,她怀疑自己是看错了,她恨不得马上跳下车去确认。
她强行镇定下来,只闭眼沉默了一会儿,心中生出一计,悄悄摘下戒指往口袋里一塞,忽然叫道:“呀,我戒指不见了!”
那司机闻言便将车靠边停下,帮着她忙满车厢地找戒指,却连戒指的影子都没看到。
她只作出快要急哭的样子,道:“那可是婚戒,若是掉了,被督军知道了,可怎么是好……”
司机问急道:“夫人您再想想,是不是出门时没带?”
“不会的,这戒指我从来没离过手……”她说着顿了顿,恍然大悟地道,“定是掉在绸缎庄了!”
司机望着一路游行的队伍,道:“夫人,那边街上乱得很,我先送你回府,再派人出来寻。”
“这一来一回太耽误时间了,被人拾去了可不行。”沈涵初顿了顿,道,“你快回去寻戒指,我在这儿的咖啡馆等你。”
司机显然很为难,道:“可是夫人,那您……”
“那些人都是往公署大楼去的,这咖啡馆乱不起来,你再啰嗦,丢了戒指唯你是问!”
那司机也知道那枚戒指极其贵重,急忙驱车驶回。
等那车子没影儿了,沈涵初飞快地跑了起来,穿过一条条巷子,直往游行的队伍跑去。
那队伍浩浩荡荡的,如涌动的海潮,见不到头也见不到尾,她一面跑,一面喊:“同学们,快回去同学们!太危险了,你们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周围人声鼎沸,她的声音如她得人一样,被淹没在义愤填膺的海浪中,微弱如丝。
她一遍遍喊着,无力地喊着,终如滚滚长流中的逆行者,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劭南,劭南!”她沙哑的嗓音地喊着,她阻挡不了滚滚洪流,但可以就拯救她的爱人。
她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着楚劭南的身影,可就像她的梦里一样,人影幢幢,拥挤又混乱,她遍寻不得。
她不管不顾地在人群里往前冲,固执地嘶吼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张熟悉的面孔终于回过头来。
仿佛在黑暗中见到曙光,她浑身一激,一把抓过他,飞快地跑了起来。
耳边全是呼啸的风声,风声和着激昂的口号交缠在一起,起起伏伏,楚劭南被她牵着手,只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般,在浩浩人流的背景下,只有他和她在跃动。
等他回过神来,已然进了一条小巷子。
楚劭南僵立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沈涵初。她穿了件和她脸色一样苍白的绸衬衫,一条桃灰色的细格子裙,一直垂到脚踝,因为瘦极了,衣裳显得空荡荡的,风迎面吹来,都往后飘着,显得人更加单薄。
楚劭南这段日子颓然至极,人已消瘦了很多,可她竟然比他还瘦,他看在眼里,心里徒然生了一种震撼。
离上次见她,已经过去多少时光,那时的她昏醉不醒,可此时此刻,她却是清醒的,鲜活的。
因跑得太剧烈,沈涵初此刻气喘吁吁,却仍急着朝他道:“你快回去,军队马上过来了,你会没命的!”
她在关心他?
他心里涌上一阵痛楚的喜悦,可随即被理智压制下去,他已经发傻了几次,不能再为她的几句话再乱了自己的心神。
他目光无声地一顿,冷言道:“我会不会没命,与你又有什么干系……”
她强忍酸楚,继续道:“我没跟你开玩笑,顾北铮下了令,领头闹事的人当场击毙,你真的会死的!”
楚劭南不为所动,转身往巷口走去,缓缓道:“若能以我辈之鲜血,唤醒民众之觉醒,拯救国家于危难,我楚劭南心向往之,虽九死而无憾!”
沈涵初闻言一颤,朝他的背影直喊道:“楚劭南,楚劭南!”那身影却离她越来越难,终是她留不住的。她跌跌撞撞地跑上前去拽他,却怎么也拽不住,她急得快要哭出来了,颤抖着道:“劭南,劭南……不要去!求求你不要去!”
这一句亲呢的称呼,牵动了他心底的柔软,过往的一幕幕涌上脑海,“劭南……劭南……”记忆里那些琐碎而美好的时光,她总这样温柔道唤他;她亲手为他构筑的美好,又被她亲手毁掉,那样残忍而决绝,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黯然与痛楚更甚。
“顾夫人!”他低吼着打断她的呼唤。
一声顾夫人,如刀刃剜心,沈涵初木然而立。
他终于转过身来看向她,眼里渗着一丝雾气:“顾夫人当年雨夜决绝之言,劭南铭记于心,一刻也不敢忘怀,顾夫人当初让我别再来找你,如今又为何一次次出现在我面前!你走吧,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他说着,直往回走,似乎不愿意再多看她一眼。
艳阳天里,她却通身起了寒意,他脸上那种决然的神色,仿佛真是要去赴死!她相信他做得出来,这是她一贯认识的楚劭南。她绝望地颤栗起来,只一瞬间,她下了什么决心似地冲了上去。
“啪”地一声,楚劭南忽觉腮颊上一阵火辣。
他终于止住了脚步,惊愕地看着她。
沈涵初浑身哆嗦,连嘴唇都变得雪白的:“楚劭南,我告诉你,你的命是我救的,你想死,也得经过我的同意!”
他怔怔地看着她,似乎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是我,那时答应嫁给顾北铮,他才肯放你出狱!我牺牲了自己才将你救回来,你真要让我的牺牲都白费了吗!”她朝他嘶吼着,声音带着一种悲怆的颤抖,眼泪珠子似的滚了下来。
那声音如雷鸣贯耳,楚劭南震惊万分,呆若木鸡地站在了那里。
“我本来打算瞒你一辈子的,我想你恨我,便就忘了我,忘了我,便能开始新的生活。可你呢,你就这样糟践你的命,楚劭南,你连基本的理智都没有了!”
那巷子斑驳的白粉墙上,长着青晃晃的霉苔,一阵穿堂风吹过,那风似乎有着巨大的重量,吹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他有些不可置信,耳边唯有嘶嘶的啸音。
他冲怔地站在那里,过了许久,他忽然哆嗦着伸出手,抓着她,唤道:“初儿……初儿……你……”
他有千言万语要说,有千言万语要问,可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句也问不出来。
她泪光莹莹,只手足无措地去推他,道:“你快走,回家去,回家去,我求你了!”
他仍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僵硬地点点头,一面默然地伸出手,想要去安慰她,她抗拒地转过身去,不住地抹眼泪,道:“我要走了,我是设了计偷跑出来的,不能离开太久,他们会找过来的。”
她转身便跑,等到了巷子口,似乎又不放心,脚步一顿,回过头来。
那巷子里似乎变得特别逼仄,有狭长光线从她身后射进来,明晃晃的,又似乎是晦暗的,他看不清她的脸,只听她在远处喊道:“劭南,答应我,要好好活着,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