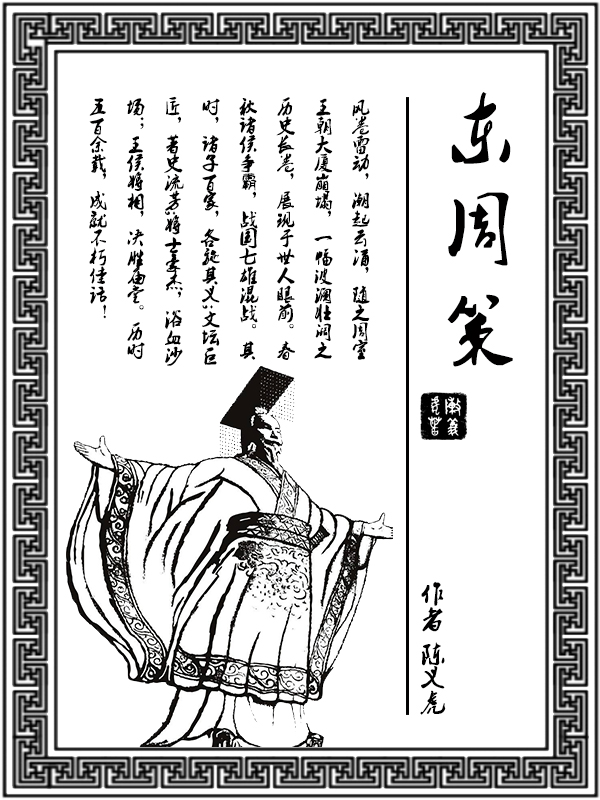撰写史书,是胜利者的特权。而历史便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任何一个政权取得胜利之后,总会给自己寻找合法的理由,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
而抹黑前朝,则是最有效的办法。毫无疑问,陈胜所见到的秦律是非常苛刻的。但实际上,这种苛刻的律法,经过百余年来的演变,很多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执行下去,执法者也会从中变通,使得法外显露人情的味道。而从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从一开始就无法彻底执行。
原因很简单,不是秦国执法不力。而是不能执法有力。
秦国地处西陲,严重缺乏盐、铁以及各种货物。这种缺乏,导致了对山东六国的依赖。但随着秦国的崛起,六国对秦国采取的是封锁的态度,寻常商人根本无法和秦国进行正常的贸易。而秦国必须从外得到货物的输入,于是一些走私商人应运而生。这些人有山东六国胆大包天的商人,更有秦国人。面对这些商人,秦国执政者采取的并不是打压,更多的是扶持。
所以秦国表面上虽然禁商,但实际上却支持商业的发展,以弥补与山东六国的差异。所以经过百余年的演变,才会导致咸阳如此繁华。
而秦灭六国之后,秦国的富人更加集中,咸阳的商业自然更为发达,造成了今天繁荣的秦国……至于后世所抨击的暴政秦国,很多是抹黑,还有更多的是……那些并没有发生。比如传说之中劳民伤财的阿房宫,陈胜来到咸阳,并没有听说它的存在……
“最后,这是来自万里之遥以外的胡商的特殊货物。”秦无霜提及“货物”二字的时候,语气显然有些变化。不过身为风尘女子,最善于的便是隐藏自己的情感,很快便把自己的情绪掩饰起来,说道:“色目人奴隶一百五十人!底价一千五百金!”拍卖台下,十来个壮实的奴隶一字排开,作为这一群奴隶的代表,身上只围着一条破布遮丑,虽然精神有些颓靡,但平均一米八高的个子,看上去还是让人感觉到震撼。
秦无霜似乎对奴隶买卖很有抵触,拍卖场给她的拍卖台词,并没有说出,便让下面的众人竞拍。
“一千六百金。”在拍卖之前,所有的货物都被过目,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奴隶的总体质量很好,别的不说,买来当搬运工便不错。但对于十金一个健壮奴隶,这数目明显不算高。
“两千金。”识货之人不少。
陈胜看了看这一批色目人,脸上露出了讶然的神色。因为他发现,这些并不是西亚人种;高鼻碧眼、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雅利安人。
陈胜忽然对这一批奴隶很感兴趣。想了想,他说道:“素韵,我想买下这一批奴隶。”知道凌素韵不喜欢奴隶买卖,所以他首先先和凌素韵交代了一声。
“嗯?”凌素韵在之前已经被陈胜说服,说道:“好啊,这些奴隶看起来还挺壮实的,你可以把他们训练成护卫。”
陈胜微微一笑,说道:“正有此意。”
敲了敲案桌上的小铜钟,守在门外的吴管事连忙进来,询问道:“小姐,有何吩咐?”
凌素韵大手一挥:“把这些色目奴隶全部买下。”虽然是在自家的拍卖场里,凌素韵也得遵循拍卖场的规则,价高者得。
吴管事心里纳闷,自家小姐如此反感奴隶买卖,此时却要把奴隶们买下,行为如此反复,着实令人费解。不过他不敢多言,连忙出去,报价参与竞拍。吴管事乃拍卖场的实际经营者,对于如何报价竞拍,自然熟悉无比。而小姐没设下低价,那更说明对这批奴隶的志在必得,价钱他自己把握。
但片刻之后,这一批奴隶的价格,便提升到了五千金。而出价的,不再只是普通贵宾坐下商人,更多是贵宾厢房里面的贵客出价在竞拍。
秦人世居陇西边陲,见过不少色目人,所以对于色目人对于秦人来说,并不稀罕。但是是在场的秦人,却是没有见过这种身材高大白皙的色目人。若是家中蓄养着这样的一群奴隶护卫,走到外面,前呼后拥,岂不是倍有面子?不少达官贵族都怀着这样的心思,才把这一批奴隶的价格捧得如此高昂了。
吴管事出价很实在,只按照价位最低幅度地递增,却表现出了决不放弃的信心,很快便让不少竞争者知难而退,只不过这一批奴隶的价位,却已经翻到了七千金的价目上了。
吴管事脸色平静如常。但是内心里却已经颤栗无比,因为看着旁边贵宾厢房里的那些管事们的报价,他知道七千金,远远不足以买下这一批奴隶,在场的人里,最开心的莫过于那胡商安迪满了。这一百五十名奴隶,本是希腊城邦斯巴达人。这些斯巴达人不知何故,竟然以雇佣军的身份,加入了塞琉古帝国的军队里面,后来因为战败,他们的头目被俘虏,这一批雇佣军竟然找上门来,以两百名精锐雇佣军作为替换的代价,换回他们的头目。
这个方案得到阿尔沙克二世的批准,并且把这些斯巴达人贬为奴隶,编入了安迪满的商队之中。安迪满却担心这些斯巴达人过于强壮,无法控制,最终会成为他商队里面的安全隐患,所以才要把他们卖出去。不过安迪满本以为,这些斯巴达人顶多也就卖出两千金左右,想不到却比他预想的多了数倍,让他欣喜无比。
“乙号房出价八千五百金!八千五百金第一次!”
“八千六百!丁号房出八千六百金!八千六百金第一次……”秦无霜很惊异,这一百多个奴隶,竟然拍卖出这么有一个天价来,而且价格还在往上涨着。不过眼下,大多参与者都已经偃旗息鼓,只留下最后两个财大气粗的主儿在竞价了。
乙号房内,公子高一脸阴沉,问旁边的侍卫:“丁号房里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