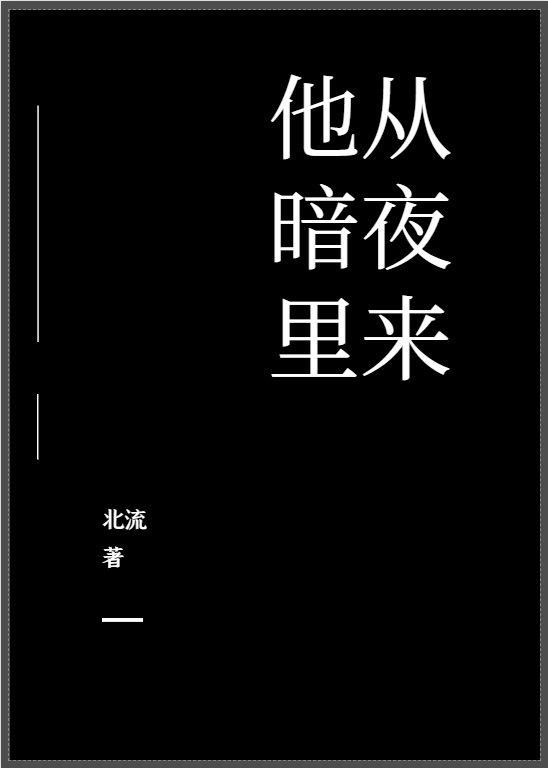他是个猎人。
每年候鸟迁徙的时候,他都会守在候鸟途径的千年鸟道上狩猎候鸟。
在一个大雾天,他在山上捡到了我,失忆的我。
他带我去医院,治好了我的遍体鳞伤,却治不好我失去的记忆。
他又带我回家,每天用他打下的珍贵鸟类煲汤给我滋补身体,虽然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死活喝不下去那喷香的肉汤。
他待我极好,温柔又体贴,有时看着他的眼睛,我常常会有种我是他的爱人的错觉。
可是我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因为他有的我都有,他没有的,我也没有。
是了,他是男人。我也是。
他很喜欢小孩子,每次看到小孩子都会捏捏他们可爱的小脸,可是我生不出孩子给他。
不工作的时候,每晚他都会抱着我入眠,温温的呼吸徐徐洒在我的脖颈,总让我痒得想发笑,后来我们就换了姿势,他把我拥在怀里,我静静靠在他的胸口。
H城晚上常大雾,每当大雾的晚上,他都会带着近距离照射可以让人暴盲的强光照射灯和猎枪上山工作。
没有他怀抱的晚上很难熬,我总是抱着枕头坐在床上等他满载而归,不过有时他也会整晚不归,熬不住的时候我也会先睡去,不过我能感觉到凌晨他回来的时候在亲吻我的额头。
今天打完猎,他回来给我带了吃的后又出门了,他说要给“上面的人”交货,然后就提着装满各种他晚上打到得鸟儿的麻袋走了。每次打完猎,他都会这样离开去交货。
我又睡了一会儿,早上起来吃了点他给我戴的小粥小菜,估摸着他快回来了就进厨房给他煮面条吃。
我不会煮饭,只会做某次在电视上学到的简易到几乎寒酸的面条,连我自己都忍不住嫌自己没用,但他总是吃得很香。
正在煮面时,一只大鸟突然恶狠狠地飞向我厨房的窗户,他呼啸而来,用尖长的嘴巴凿破窗户,冲进了我滚烫的锅里。
我愣愣的看着自己被玻璃渣划破的手臂,再愣愣的看了一眼混着面条、玻璃渣和死不瞑目狠狠瞪着我的被烫熟的死鸟的锅,缓缓挪动脚步走到落地镜子面前,用布满血痕的手抚上自己的脸。
镜子里,一个满手血的少年正颤抖地抚摸着自己被烫的有星星点点红肿皱皮的脸。
咔——
门锁转动个,他回来了,但却定在门口挪不动步子。
我慢慢扭过头看着他,他正看着我,满眸的惊恐。
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声音颤抖地文:你这是怎么了?
我抬手指指厨房:一只鸟冲进了家里。
他疾步奔进了厨房,锅里那只死鸟依旧死死地瞪着他。
他又看看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脸埋进了手掌里,哭了出来……
我又一次被他抱着送进了医院,经过急救和一个多月的调养,还用了最贵的祛疤药膏,但胳膊上和脸上还是留下了淡淡的粉色痕迹。
我们回了家,窗户换了质地坚硬的有机玻璃,外面还围了紧密的铁网,厚厚的窗帘遮住了阳光。
我站在幽暗的房间里看着他的脸:我是囚犯吗?
他把我紧紧抱进怀里,流着泪不停呢喃:对不起…对不起……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一行了?我这样问他。
他沉默,然后第一次吻上了我的唇。
那晚我们做了,他温柔的扩张我没有被开拓过的后穴,然后一遍遍进入我的身体。他说让我等,他说不久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只要等他攒够了重新开始的钱。
他说,那时他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
他说,他要我成为他的妻子。
……
之后每到大雾的晚上,他开始整晚整晚的彻夜不归,他不再把打来的鸟带进家里,而是直接连夜交货给别人。他每天出门前总会一遍又一遍强迫症般检查着门窗,生怕有丝毫的疏忽。
慌。慌。慌。
这晚他出门前,他吻了我额头说:这是最后一次,等这次以后,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靠在他的胸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不行。他坚决地说:太危险了,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我执拗的看着他的眼睛:带我去,不然我不跟你走。
他终于拗不过我的固执带我上了山。
山上的雾很大,能见度只有两米,他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山上爬。
我被他裹得像个粽子,头上还戴了头盔,从头发丝到脚拇指都全副武装。
我走不动的时候,他就背着我,一步一步往上爬,毫不喊累。
他跟我说,雾大的时候,鸟儿会低飞,而且奔着光飞,所以我们只要在猫眼洞里开着照明灯,鸟儿就会来自投罗网。
到了高些的山腰处,我惊了。山上到处是猎人的猫眼洞,在这浓雾下,大山奇异地被一束束非自然光照得灯火通明。
他背着我到他的小山洞里,里面储备着毛毯和食物。他打开他的强光灯,又是一束强光撕破了黑暗。
这山可能潜伏着十几人,但却没有丝毫的声音,安静的诡异。
我们都知道,这片安静之后,将是一场残忍的屠杀。
几声鸟儿的鸣叫声响起,过了一会一群翅膀扑拉的声音,枪声开始接连响起。每声枪响都让我的心脏一阵抽搐,鸟儿的鲜血好像蒙在我的眼睛上,四周一片血红。
我苍白了脸。他关切的问我:你没事吧?
我勉强笑笑:没事。你怎么不开枪?
他摸摸我的头,轻轻一笑:这些鸟不贵。
我这才想起他以前每次带回家的鸟大多都是电视上曾放过的保护级别鸟类。
这时天空中飞过一只大概是落了群的白鹤,聪明地隐藏在大雁群中。他眯了眯眼,拉了枪的保险栓,对准了天鹅扣动扳机,“砰”地两声,天鹅哀鸣一声掉了下来。
握怔了怔,看向另一声同时响起的枪声的方向。
那是一个一脸凶悍的光头男人,正阴阴的看着我们。
他转头也看了那男人一眼,放下枪去捡了白鹤走到男人跟前,淡淡地说:老规矩,算打中翅膀的。
白鹤中了两弹,一弹在腿上,一弹在翅膀上。
光头男人讪讪地笑:不用看也知道是你的,你拿走吧。
他毫不谦让,淡定的提了哀叫的白鹤回洞里来。
白鹤的凄哀的叫声让我心痛难忍,他于是找了根细绳把白鹤的嘴拴了起来。
我别开眼,努力想无视那只白鹤。
这一批的屠杀结束,山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批候鸟的入网。
他把我搂在怀里,一根一根把玩着我的手指。他说:你若困了就靠在我身上睡吧。
可我睡不着,我被身后那只白鹤盯得脊背发凉。
我忍不住又看了看那只白鹤,它虚弱的歪在石头上,但是眼睛却怨恨的盯着我,和上次那只冲进家里的死鸟的眼神如出一辙。
那眼神,就好像,我是一个背叛者。
我心里乱糟糟的。
———————————————未完待续———————————————————
这回先更到这里,太晚了,下次再更,应该会只有一篇正文,这是短篇哦~
嗯...先说这篇文的灵感来自最近的新闻“千年鸟道变候鸟死亡之路”
然后是更新问题,盐巴最近很苦逼,不能常上网,所以更新问题无法保障。关于《夜殇》是绝对不会弃坑的,其实我在纸上都已经快写完了,但是苦于没有办法上网码字更新,等盐巴有机会一定会更的,不过就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了,唉~~~~~~
就这样吧,各位亲,晚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