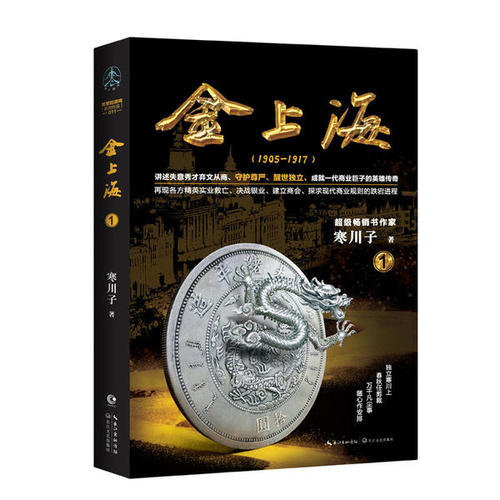系团委通知陈望春,下午三时在博雅楼404室,参加一个座谈会,什么内容没有说,说了也白说,因为这种活动,陈望春根本就不会参加,系团委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但是,午休起来后,按惯例,别的同学去图书馆,陈望春则去教室,不知怎么的,他却推开了404室的门。
当时,座谈会已经开始,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长发男子,他的身份是学校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他在黑板上出了三个题目:
你心中最大的阴影是什么?
你心中最疼痛的是什么?
你心中最爱最恨的是什么?
座位上稀稀拉拉地坐了二三十个学生,陈望春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他扫了一眼黑板上的题目,然后,把忧郁的目光投向窗外。
春末夏初,窗外高大的雪松生出了嫩绿的新芽,茂密的枝桠,给教室投下了一片荫凉;一根树枝上站着两只长尾巴喜鹊,喳喳地叫着,追逐嬉戏;一只蜻蜓,飞上了窗台,像一架小引擎的直升机,悬停在空中,嗡嗡地响着。
前面一阵骚动,有个同学和心理师在对话,陈望春这才留意到,在座的学生,一个个面色沉郁,形容消瘦,穿着灰色或蓝色的衣服。
他们表情木讷、反应迟钝,在心理师一二再再而三的启发下,才会挤牙膏似的,说一半句话,而且文不对题,简直是对牛弹琴。
这是一堂心理疏导课,每年高考之后,各地的状元如愿以偿地进入了A大学,但令人遗憾和震惊的是,这些从小就被誉为天才的学霸,从小学一年级时,就被灌输了一种理念,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他们的终点是高考,金榜题名是他们一生当中最耀眼最辉煌的时刻。
他们考上了最顶级的大学,却失去了自己该有的人生,迷惘、痛苦、低落、失眠、焦虑,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融入最基本的生活、进行最简单的人际交流、一个自然的睡眠,对于他们而言,都艰难万分,需要靠吃大把大把的药物才能勉强完成。
心理学硕士把这些症状称为心灵感冒。
他说:“感冒,是一种最常见的疾病,吃不吃药都是一周左右痊愈;但是,心灵的感冒,却要严重得多,因为你的心受伤了。你们之前的十八年人生,被你们最亲近的父母,以爱的名义折磨,你们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考一个好分数;你们的心灵长期承受着重压,且有深深的负罪感,你们在努力奔跑,当到达大学这个终点时,你们的使命便完成了,人生也到达了终点,内心一片空白,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一切归零。”
心理学硕士挥舞着手,滔滔不绝,而台子下的众学生却呆若木鸡,他们好像不在同一个空间里,甚至不在同一个教室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陈望春看着黑板上的三个题目,心里暗自斟酌。
我心中最大的阴影是什么?他的思绪飞回了油坊门,想起了很多往事,给他心灵蒙上阴影的,无疑是他的父亲陈背篓,当着全村人的面,让他光着屁股拉磨。
我心中最疼的是,母亲何采菊躺在月季花刺上,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随后逐出家门,至今杳无音信。
心中最恨的是谁?是他的父亲吗?最恨不确切,应该是最怕,他梦里都怕他。
至于心中的最爱,陈望春咧嘴一笑,有点羞涩,那是个不能告人的秘密,得珍藏好,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时,突然有人吹起了口哨,是一首苏联歌曲,开始是一个人吹,后来大家都跟着吹
陈望春突然兴奋起来,也跟着吹起来,令他惊讶的是,这首完全陌生的曲子,他竟然无师自通地会了。
陈望春不知道的是,今天404室的全是和他一样的、行为怪异、心理异常的学生,他们在考场上所向披靡,而在生活中,却和正常人拉开了距离。
夏天来了,宿舍里好多学生都光着膀子,陈望春却穿着长袖,扣子扣得紧紧的,大伙让他脱了衬衣,凉快一下。
陈望春犹豫着,解开了几个扣子,他似乎感觉呼吸通畅了,身体轻松了许多,他拿起一本书,扇了几下,凉风亲昵地抚摸着他禁锢多年的肌肤,令他愉悦舒服。
他鼓足勇气,脱去了上衣,坐在电风扇前,瞬间,他从炎热的夏季,到了凉爽的秋季。
舍友看见了他背上的秘密,他们好奇地端详着,询问着,陈望春讲了1992年夏天,那场怪异的龙卷风,舍友们惊讶不已。
这是陈望春入学以来,第一次和他的同学坦诚的交流。
陈望春请室友们帮忙,将他后背上的印记除掉。
这个来历不明,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印记,剥夺了陈望春多年的自由和快乐,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舍友们和他一样,对此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
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除去这个讨厌的印记,但他们很快失望了,那些广告上吹嘘去污能力超强的洗涤剂,居然没有让它褪一点颜色。
他们能想的办法都试了,一点用也没有。
陈望春提出用浓硫酸,他们吓了一大跳,这是万万不敢尝试的,那是要出人命的。
陈望春说水攻不行,改用火攻,他的意思是用火,将皮肤烧成疤痕,印记自然就看不清了。
室友们咧咧嘴,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酷刑,他们可不能用在自己同学身上。
陈望春有点恼火,他不满地瞪着眼睛,意思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一群高智商,还不如几个臭皮匠。
最后,大家友好协商,分析了利弊得失,在把伤害降到最大限度的条件下,打算用一根绣花针,一针针剜掉这个印记。
这是一项耗费时日的工程,需要多个夜晚才能完成,于是,每天晚上,室友们轮番上阵,对陈望春一个小时的刑罚伺候,一针一滴血珠,开始大家心颤手抖,到后来,就习惯了。
一天下午,陈望春罕见地去逛了一次大街,以往,大家约他一块出去时,他从来都是拒绝的,他似乎觉得,呆在学校的四堵墙里面,才是安全的。
晚饭后,陈望春回来了,他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家杂物店里,买了一把钢刷子,大家不明白他买刷子何用。
直到晚上,他脱去衬衣,把他的背亮出来时,舍友们才明白了,他嫌绣花针太慢,他要用这把钢刷子,刷去他脊背上的印记。
大家面面相觑,钢刷子刷在皮肤上,那是啥滋味?大家不寒而栗。
陈望春却坦然地笑了,说:“拜托了。”
大伙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肯上,最后,采取抓阄的方式,偏偏是最胆小的小朱,这个倒霉鬼,哭丧着脸,哀求大伙,放他一马,他愿意补偿,请全宿舍的吃一次大餐。
大家断然拒绝了他的诱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陈望春鼓励他:“你眼睛闭上,用力刷几刷子,就结束了。”
为以防万一,大伙儿去买了云南白药、碘伏、酒精、药棉、绷带,像要做一个大型手术。
小朱拿起钢刷子,他的手抖抖索索的,陈望春说:“闭上眼睛,用力挠,就像挠痒痒。”
两个舍友,抓住小朱的手,在陈望春背上挠了起来,一共挠了四五刷子,背上一片血肉模糊,印记自然看不出了。
陈望春咬牙忍着,舍友用碘伏消了毒,撒上云南白药,用绑带缠了几圈,大功告成,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晚上,陈望春破例买了一扎啤酒一大包零食,感谢舍友,这是他大学四年里,唯一一次与室友同乐。
之后,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午夜之后,他的哭泣、惊叫,如期而至,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陈望春不断收到陈背篓的信,每一封信,陈背篓都关注陈望春学习如何、有无获奖,如果获奖了,及时把证书的复印件寄回来,油坊门急用。
陈望春每封信的后面,都是三个大大的惊叹号,类似于过去乡间传递紧急情报的鸡毛信。
然而,收到信的陈望春并不着急,看完后,他就撇在一边,他从不回信,如果他回信了,不但会被陈背篓拿着到处炫耀,还会贴在荣誉墙上示众。
除了信,陈背篓每月寄给他500元生活费,对于社交空白、社会活动等于零的陈望春,500块已经足够生活了,他大概是班上花费最少的学生,因为除了吃饭,他不知道该把钱花到哪里去。
这天下午,陈望春坐在花园边,读陈背篓的最新来信,厚厚的五六页,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村里的最新情况:谁家买了一台大彩电、谁家买了一辆摩托车、谁盖了五间大瓦房、谁打工赚了多少钱、谁从副科级升到了正科级;这一月,哪个学校来参观了魁星楼、谁留了言等等。
陈望春一扫而过,当他看见刘麦秆和刘爱雨的名字时,他慢了下来,细细品味。
刘爱雨在广州打工,工资很高,给刘麦秆寄了两千块钱,因为这个,刘麦秆和刘爱雨在村里的地位大大提高,很多人将刘麦秆奉为座上客,认为高考状元不如一个打工妹。
陈背篓大声疾呼,儿啊,你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你要争气,快点把获奖证书寄回来,我有急用。
急用两字是红的,是陈背篓咬破手指写的血字,可见他的心情相当地急迫。
陈望春一直坐到黑夜来临,然后去食堂吃饭。
第二天,他找出自己的获奖证书,装入A大学特用的信封,寄回了油坊门。
北京来信了!陈背篓翘首期盼的陈望春的信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是来了。镇邮电所的小王,第一时间把信送到油坊门,并亲手交给了陈背篓。
陈背篓右手高高举着信,像举着一把火炬,穿过油坊门,边走便喊,北京来信了!北京来信了!
陈背篓将信给人们看,牛皮纸信封上,有红色的A大学的字样。
陈背篓将手在衣襟上蹭了蹭,小心地撕开信封,取出里面的证书,展示给人们看,上面有A大学红色的印章,老百姓就认官印,红坨坨就是王法。
陈背篓眉飞色舞地向人们炫耀,根本就没意识到,信封里,除了证书,一无所有,没有给他一句话一个字。
第二天,陈背篓专程去了镇上,复印了获奖证书,他希望人们能关注一下来自A大学的获奖证书,但开店的小媳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操作复印机,根本不看证书的内容,这令陈背篓很扫兴。
陈背篓将证书的复印件,贴在荣誉墙上,为了招揽观众,他放了一挂鞭炮,然而,只有寥寥几人出来,看见是他,又缩回去了。
证书的原件放在魁星楼一个紫檀木的木盒子里。
关于这个盒子,有一个曲折的来历。
一次,陈背篓去村长牛大舌头家,看见他桌上有一个盒子,很旧很老了。
这个盒子陈背篓熟悉,在大集体时,上面发了红头文件什么的,队长牛大舌头给大伙一传达,就装进了这个盒子里,锁上锁,谁都不让碰。
那时,这个盒子的神秘,使陈背篓想入非非,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盒子打开看一看。
后来,集体解散了,红头文件也失去了它神秘的光环,有时候,村长牛大舌头就把它撇在桌子上,谁都可以看,有人还撕了卷烟。
再后来,村长牛大舌头就用盒子装香表,放在祭祀祖宗的神龛前,算是派上了用场。
陈背篓看见紫檀木盒子,触动了他的心思,他想,这个盒子用来装陈望春的获奖证书,是再合适不过了。
陈背篓当即提出这个要求,村长牛大舌头歪着头想了想,居然答应了,说:“陈望春是咱油坊门的招牌,这个盒子,我无偿地捐献给你。”
村长牛大舌头连盒子带钥匙和锁,一并送给了陈背篓,陈背篓过意不去,给村长牛大舌头买了一包五块钱的兰州烟,表示谢意。
陈背篓将获奖证书放进盒子里,锁上锁,当有人来魁星楼参观的时候,他才会打开,让他们一饱眼福。
徐朝阳校长成为陈望春的铁杆粉丝,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着陈望春的勤学和优秀,陈背篓对此感激不尽,尽管徐朝阳校长一直以陈望春的伯乐自居,而淡化了陈背篓家庭教育的作用。
每学期中期考试后,徐朝阳校长都要雷打不动地组织一次向陈望春学习的活动,有时候是优秀学生,有时候是差后进学生。
对优秀学生,徐朝阳毫不留情地敲打他们,你们比起陈望春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要虚心,要夹紧尾巴。
对后进学生,则鼓励他们,说当初陈望春也是一名差学生,在老师的教育感召下,端正了学习态度,努力追赶。其实,每个人都能创造出奇迹来。
徐朝阳校长带着学生,清除了荣誉碑周围的杂草垃圾和人畜粪便,用抹布将碑子上胡写乱画的痕迹擦掉,然后,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一行字:每天晚上,我们仰望星空,默默注视着你这颗最耀眼的恒星,和你对话。
在魁星楼里,徐朝阳校长指着墙上的奖状,如数家珍,他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每张奖状颁发的细节;他让学生们传阅陈望春做过的试题、记过的笔记本、摸摸他用过的笔。
在新学年的教师会上,徐朝阳校长勉励新调入的教师,要狠练教学基本功,只要能教出陈望春这样的学生,这一辈子就没白干。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正是读书无用论和知识改变命运两种论调斗得脸红脖子粗、难解难分之际,在油坊门,这两种论调的代表人物是刘麦秆和陈背篓,油坊门人像看对台戏,一会往东一会往西。
陈背篓说,陈望春又获了奖,还发了奖学金,发表了论文。
刘麦秆必针锋相对,说刘爱雨又涨了工资、升了职,她们厂子的待遇好,每顿饭都有羊肉泡、四菜一汤,每天发新鲜的水果,每周旅游一次,连擦屁股纸都是厂子里发的。
刘麦秆炫耀时,马上有人出来声援呼应,说:“真真的,我们丫头来信说了,厂子美得天堂一样。”
就在年初,村里有三个女孩去了广州,在刘爱雨的介绍下,进了工厂,两个月后,给家里寄回了钱。
这个现象在油坊门有九级地震的效应,这些土里刨食吃的农民,一辈子打着牛屁股,春种秋收,早起晚睡,把日头从东背到西,幸苦一年,未必能收一把满意的粮食。
而女孩子一去工厂上班就发工资,太快了,种子撒进土里,不一定都会发芽,即使发芽了,还需要雨水、肥料、阳光和风,最终才能长成一株禾苗,结出果实。
刘麦秆所说,有人证物证,相比之下,陈背篓说的,看不见摸不着,谁知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