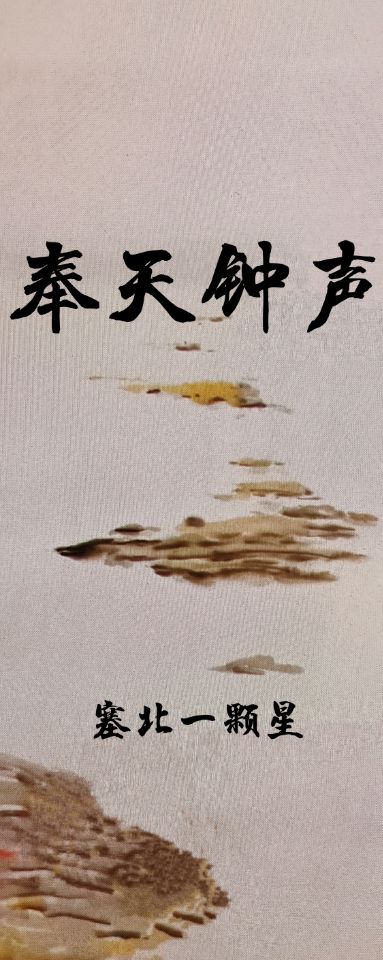隔壁的疯女人总是在不停地敲打着什么东西,那种叮叮当当又毫无美感可言的音律像把锯子,硬生生的锯开了所有人的脑袋。
老头子的烟斗不耐烦的敲打着桌子上的石块,接着把烟草添了进去。
“丫头,去叫那个疯女人安静一点。”
我透过玻璃瓶看见他扭曲滑稽的老脸,又继续着将手里的机器拆开,假意听不见他的话。
“喂,我知道你听见!”他很暴躁,但奈何他残缺的腿不允许他起身收拾我。我把最后几根电线连起来,按下电源的一瞬间,电光“呲啦”一声把最后的灯泡送入了地狱。
“呵。”老头看见冷漠的电光,把烟斗点燃后发出不屑一顾的笑声。我懊恼的拆下发黑的灯泡,将其丢进了布包里,道:“我去再找点材料。”
还没等人说话,我已经自顾自披好了外套,用纱巾把口鼻捂的严严实实的。
“别费力了,”那老头缓缓吐出一口气,道:“这里不可能再找到有用的东西了,因为这里可是——”
我把门“唰”地打开,顿时满眼枯黄一片——这里可是,遗忘谷。我裹紧了纱巾,冒着卷杂着沙砾的风摇摇晃晃地行走向不远处那个发出巨大声响的屋子。
望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建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门。
我怕风声会迷惑屋里的人,但当噪音稍微停歇的时候我摇摆的心开始紧张跳动。紧接着破败的木门“咯吱”一声开了,我的心沉了下来。
“您好,我想……”“进来吧。”那个人说话的音色像老式风箱,干涸难听。我进了门,发现这是那个疯女人——她蓬乱着自己的头发,明明面容看着才到中年,但是她的身体居然极度地佝偻变形,活生生把她压榨成一个老太。
之前我们听着她“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以为这个屋子会非常的脏乱。结果现实是,这里虽说对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却被很整齐的摆放起来。
老妇人年过半百的样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像生了锈的机器。
“沙子,还是沙子……”她抬起透明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细腻的黄沙,不一会儿她机械般扭过头,用她苍老的目光扫视我一番。
“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不需要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她颤巍巍地向前走去,她的工作台上是一些扭曲得不成样子的零件,“这只是一座孤城,你要的,这里都没有。”
她伸出干枯的手指,摩挲着那些零件,最后又高高举起锤子恶狠狠地砸下去。桌子吱呀摇晃了两下,我一时竟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站立在原地,摘下帽子露出里面脏乱蓬松的头发。现在我一定很肮脏,很狼狈,不小心跌落到泥坑的狗也不过是我这样。
她难得把目光投落在我身上,说道:“屋子后面有个水井,洗洗脸,脏小子。”
我听闻,不由得愣了一下。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阴阳般的存在,富庶的地区把贫穷地地区吸干,抛弃——穷人走在沙漠里,最后的尸体连被蓬草都滚过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资源匮乏,水比金子更加珍贵。
“我不需要。”
她没有再说话,手指却十分灵活地往零件里面放入钢珠,随后听见“叮”地碰撞声,她居然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条机械手臂。
看得出她在造一具机械躯体,她可以熟练地安装各个小部件,最后组合成躯体地各个部分。我看着她敲敲打打后又不断矫正,忽然觉得她似乎不是什么普通人。
“我需要一个脑袋。”
这个要求让凉意顺着我的脊柱下滑,一个激灵刺激我后退。她说她要我的脑袋我都信,因为没有下线的人我见的太多太多了。
“我还没有找到。”橘黄色的油灯奄奄一息,火苗跳跃两下归于沉寂。这个人,有些可怕……我后退了两步,正要逃开却听见重物撞击大门的声音,心陡然被提起。
女人的面色更是恐怖阴沉。
只听见木板断裂,有人抓紧我的手腕往屋子更深处赶。“哐”的一声宣告门的寿命已结束,几只瘦骨嶙峋却面露凶光的野狗破门而入,它们的背上都有一个类似于驼峰的鼓包。
女人似乎很惧怕这些东西,而它们……凶恶的野狗撕裂着地上几块破布,然后把目光锁定到了我们逃跑的方向。
我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就被那个人摁着脑袋塞进一个地窖里。她跟着跳下来,把门拉上又带着我继续往下赶。
“你……”
“闭嘴。”
“我师傅!”猛然间想起那个老头还在不远处的建筑里,我不由得紧张起来,“那个老头还在外面!”
“我的女儿也在外面。”她的回答很冷漠,也很让我震惊。她的女儿?什么女儿?我从未在这里遇见过其她女孩,更不要提她的女儿。
她挺住了脚步,我同她一起屏住了呼吸。外面犬吠的声音被皮靴踩踏地面的声音所替代,不一会儿我还听见了子弹被发射出去的声音。
“怎么回事?”
“这里不能待了。”她面色凝重,她紧皱眉头叙述着她的绝望。我不想过多理会,一把甩开她的手往出口走去,没曾想她却这么对我说:“你逃不出去的。”
我逃不出去。
“你逃不出去的。”那个男人跛着脚,艰难地扶着一切能扶住的东西行动。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只看见他恶煞般的脸就忍不住瑟索。
蒸馏瓶,试管,各种各样的药剂在烧瓶里“噗噗”地叫嚣着。
这个男人把我从父母身边带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喝酒,抽烟,从不与别人交流,我与他的关系也就仅仅只是师徒那么简单。
他告诉我怎么从坏掉的电器里挑选合适的零件,又带我逛遍了大大小小的废物堆。我们出生在贫瘠的土地,要靠所有能依靠的资源去生存,那也是他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