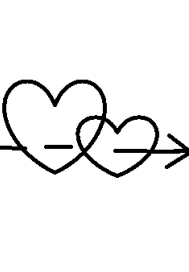抢救室的门开开合合无数次。不时有其他医生神情严肃地从走廊那头飞跑过来,紧张的护士们不停地进进出出。院方下了五次病危通知,医生要少暮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可少暮完全没听明白医生在说什么,只看见医生的嘴巴一张一合。他好像还礼节性地对医生笑了笑。
“不要救我,让我死去才是最好的安排。任何人没有权利替我做主,逼我承受。成全我,让我死去……”
少暮想起小汪对她男友的嘱托。那么,自己又有什么权利替她做主?有什么权利逼她承受痛苦?对,成全她。他甚至希望医生们就此放弃抢救,放过纯子。他宁愿她不再为人,也不想她再经历地狱般的磨难。她一路走来都是血迹。
如果这次纯子就此放手,选择回头,他不怨她,他会为她高兴,她本该自由的。自己实在没有能力保护她。不能替她死,不能替她疼,甚至不能替她恨。她不属于世间,是他打破了她的平静。他和她,注定只能相忘于江湖。
手术已经五个多小时了。少暮看着手中一叠病危通知单,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有新的。
几个医生先后从抢救室出来。
“意义不大。无能为力之下也只能放弃。”
“唉,干这行最怕的就是这个时刻。那种受挫感真的能让你怀疑信仰,挺崩溃的。”
“我也是刀尖上行走多年的人了,心理素质自认为还算过硬,谁想真正面对时,还是会接受不了。”
“还花一样的年龄呢。”
各科室医生边说边各自散去,走廊又恢复了安静。
陆明贤看了看时间,还是不太愿意相信。他缓缓走出手术室,对外面守着的男子说:“对不起,病人没有挺过来,死亡时间是……”
这次少暮听清楚了。他脑袋轰一热,什么东西飞出了身体,心里全空了。
她还是走了。
在那个血色天空的海边,纯子躺在他怀里,断断续续道:“阿原,我一直在等你,我要永远陪着你,我没有忘记,我不后悔……”
少暮浑身发软,却又生出如释重负的轻松来:她早该走了的。这时插在口袋里的手触到了兜里的项链,他猛地死死攥在手心,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突然,少暮感到手心有一股强大的气流往外冲,小小的项链像是充足了气使劲挣扎着要挤出来,随时都会从指间突然飞走。少暮咬牙紧捏拳头,额头上青筋暴起,渗出点点汗珠。他在心里大喊:
纯子,不要走!
他仿佛听到自己的声音穿过长廊,飞出医院,漂到海上,穿透波涛,直抵云霄:
纯子,不要走……
这时抢救室里传来一个声音:“主任,快看!”
陆明贤一听刷地转身,一扫刚才的疲惫憔悴,飞一般冲进抢救室去,摔得左右两扇门噼噼啪啪来回晃个不停。
少暮慢慢松开手,只见那串熟悉的贝珠此时正静静躺在掌心。他闭上眼,任泪水淌满面颊,“对不起,纯子,回去吧。”
少暮等着抢救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他要让她戴着贝珠离开,却好久也不见念寻被推出来。
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少暮迷迷糊糊又听到了纯子给他唱歌,看到了海边火一样通红的天,村民们背着锄头急急奔来,海水冲垮了城堡,又好像听到身边有人在跑动……
少暮睁开眼睛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一个激灵坐起来,只见抢救室显示灯依旧是“手术中”。念寻还在里面?还是已经换了别的病人在抢救?他揉了揉眼睛,站起来朝门里探,什么也看不到。长廊里是他和他瘦长的影子相守成双。
凌晨五点左右,抢救室里面陆陆续续有医生出来。少暮一抖,等着有人来向他宣布。可是并没有人朝他走来,一个个都自顾离开,消失在了走廊尽头。隐约听到:
“神奇,太神奇了。”
“真是想不到。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案。这不是医学的作用,无法解释。”
少暮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多会儿,陆明贤走了出来。他眼里布满血丝,沙哑地对少暮说:“不可思议!接下来就看她自己了。未来几天是危险期,病情随时会突发,做好心理准备吧!”说完拍拍少暮的肩走了。
念寻被推出来时浑身缠着厚厚的绷带,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随后就被人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
学校来了一波人,伊利哇啦一顿嘈杂之后又走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教育局相当重视。这年头家校关系紧张,一直都是社会敏感的焦点,处理不好就会被骂上热搜,各级领导自然是谨慎又谨慎。
后来事情定了性,与学校干系不大,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念寻父母都不在了,也不必顾忌家长会闹到学校里来。渐渐地学校便没有之前那么紧张尽心了,公关工作也只是隔几天派老师代表去医院露个脸走个场。少暮无心理会这些。新闻过了保鲜期,你要允许别人转移注意力。他巴不得学校老师不要来,整天叽里呱啦完全帮不上什么忙。没人来反而更清净。
念寻没有直系亲属,只能由班主任老师代为临时监护人。陆珍珍一开始还算热心,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学校领导一再交代要尽显校方的深切关怀。后来渐渐地便来得少了。她一直以为少暮和念寻家是世交,就拜托少暮多多关照念寻,之后就很少出现在医院了。
ICU门外是家属休息室。里面很安静,大家说话表情都很克制。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撕心裂肺。都是带着心理准备来的,凶吉也都心知肚明。
紧闭的大门有时会被拉开一条缝,医务人员探出脑袋对外面喊某某某的家属在吗?那是病人情况危急,要喊家属见最后一面。守在外面的家属战战兢兢。既想知道里面的情况,又不愿被叫到自己亲人的名字。
这时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医生从门里探出半身向外喊:“陈明明家属在吗?”
休息室一阵沉默,大家互相看了看,只见一个中年人站了起来。起身到ICU病房门口只有几步路,他走过去竟然踉踉跄跄走歪了,差点撞到墙上。病房门口的医生对他说了几句话后,他没站住,身体一偏,倒在了门上。旁边的医生马上伸手去扶住他。少暮的心猛地一揪,手捏紧了口袋里的项链。
他还没有准备好。
二天后,少暮被安排进到ICU探视。他在护士的带领下在一张病床前停下。只见上面的人全身被纱布包扎得严严实实,一动不动。少暮一时很难将眼前的人与念寻联系在一起。
他去握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毫无反应。他俯下身碰着她的脸,好久好久注视着她的睫毛。没错,就是她!当初为她治疗面部过敏,他曾多少次抚摸过这张脸。她脸上的每一个部位,他闭着眼睛都能勾画出来。可如今,她不再勾嘴浅笑,不再明眸生辉,不再睫毛微颤。
少暮低头去吻她冰凉的睫毛,嘴唇划过她耳边,轻声说:“不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