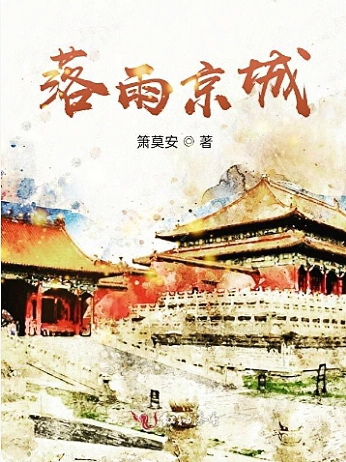容光抚摸过一张张有些泛黄的信筏,慢慢读过后将信收在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子里。小木盒子被上了锁后放在了抽屉深处。容光轻轻呼出一口气,小声嘟嚷着什么。
她背着画架走出院子的时候,容妈妈正巧在院落里浇花,容爸爸坐在院子角落的梨花树下和她说着话。看见容光出来,笑着招招手唤她过去。
“容许这小子,都几个月不来信了。这个月的信还没来?”
“没呢。可能军营里任务太重了。”容光摇摇头。跟容爸爸容妈妈说了一声后就出了门。门外的车已经等了许久。导师也在上面,跟着容父容母打过招呼后,便叫着容光上车。
容光自幼学画,还算有点天赋,得奖不少,受过不少赞誉。近来有一场不小的国际比赛,她答应了导师去试一试。却因为心神不宁老是画不出想要的效果。导师想着去采采风,也许会好一点。
车开得不是很快,窗户大开着。近来天气不好,总是阴沉沉的天和乌云,风刮得也大。容光的头发被吹得有点凌乱了。她看向窗外飞速闪过的景,思绪慢慢飘远。容许在做什么呢?
她近来总是做梦,梦见很多以前的事情。就像行将就木的老人一般,可明明她还很年轻,却已经开始在回忆和时光的长廊里慢慢地往前走,想起很多记忆的碎片。梦醒时总是泣不成声,却也总是记不住黑沉沉的梦境里她到底是望见了什么。她有些心神不宁。
到了旅馆,容光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架好了画架,调好颜色,开始构思。却怎么也没有办法集中思路。想放弃了啊。如果是容许,会怎么办呢?容光想了想,笑了。容许从不会这样,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应定的任务,就像哪怕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走,他也能趟出一条笔直通向目的地的道路。
他总是这样。就像他决定了要去军营,不顾容父容母的阻拦,就真的去了。其实并说不上阻拦。追根究底,容父只是问他,“你真的决定要去吗?”容许沉默了一会儿,容光在旁边不知所措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容许说,“嗯。我想好了。”容母轻轻叹了口气。
容光的生日过后不久,容许就出发了。那些日子里,容光赌气不理他,容许只是笑着哄,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离开得很突然,容光去了培训营上课,没来得及回来。等她气喘吁吁跑回来时,容许已经走了。容光红了眼睛,眼泪还是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直到今天,她还是很后悔自己当时赌气,没有见到容许出发前最后一面,没有对他说一声多保重。容许一去就是好几年都没有归家,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他。只不过每个月会来一封信,告诉他们他一切都好。因为容父的原因,她知道一些容许没有在信里说出来的事情。比如,容许刚开始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受到优待,但最后因为肯干能吃苦,训练最好,很受重视,被多次派遣出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大家都很敬畏他,不像一开始总有嘲讽之意。
容光当时坐在客厅地板上,翻着书在漫不经心的看。其实更多是竖着耳朵在听容爸爸和容妈妈的闲聊。容爸爸知道她的小心思,也不揭穿她,只是笑着和妻子讲话。容妈妈笑着瞟他一眼,也不说话,就听着他讲下去。
他说,容许出任务太拼命了。好几次都受的重伤,好不容易才救回来。身上的疤痕多的,他一个也上过战场的人看了都觉得惊骇。容爸爸喝着茶摇摇头,容许心里的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容光好像还是在认真看着书,只不过头越来越低,几乎埋进书页里面去。她的眼睛红红的,想起那个干净清瘦的男孩子对着赌气不理人的女孩子说,“我可能还是没有彻底走出来。对不起。”他温柔地摸摸女孩的头发,向来冷淡的面容对着她都是温和亲近的。那天夜里很热闹,窗外烟花一簇簇地绽开,十分灿烂。容光第一次觉得容许离自己那么远。容许说完,对她笑了笑。容光才觉得容许仿佛又回来了。心也慢慢落了下来。
容光回过神来。又想起容许陪自己去买生日礼物的那一天。其实是她先认出的那个女人。
很早很早的时候,容光总是唤她容许妈妈,女人会温和的答应,会给她甜蜜的糖果,会抱着她声音温柔地给自己和容许讲故事,会给他们弹很好听的钢琴。后来好像就不一样了,容许妈妈喜欢钢琴,可是容许的爸爸一直忙,她要照顾容许,要顾着很多事情,她没有时间了。好几次,容光去容许家玩,看见原本在客厅角落的钢琴被搬去了杂物房,黑白分明的琴键上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尘。容许妈妈似乎忘记了她曾经那么喜欢钢琴,整个人慢慢地沉寂了下去。像漂亮的珍珠逐渐失去了光彩一般。
她曾经看过容许妈妈与容许的爸爸爆发出激烈的争吵,两个人疯狂地互相指责。容光听院里的老人感叹,两个人都是理性而重视工作的人,分开来是很棒的人才,组成家庭却不一定完美,只是苦了孩子。容光还记得老人叹息的目光,她不是很懂老人的话,却知道不该让容许听到他们的争吵。他们站在门外,容许温热的手掌覆盖在容光的眼前,还很稚嫩的少年声音寂静,“我带你回去,别怕。”走了很远,容光拉下容许的手,才发现容许已经泣不成声。
她想拉着容许赶紧离开那家店,容许觉得奇怪,笑着逗她,一转眼,发现柜台前美丽的女人。她那么漂亮,蒙尘的珍珠又散发出光彩来了。容许渐渐沉默了。他望着那个方向,默不作声。
那天回来后,容许安静了很久很久。她一直守在他的身边,画着画,偶尔偏过头看他,然后回头继续画画。他不说话,容光也安安静静的沉默着。
不久,容光把自己草草画成的画稿推给他看,容许微微扬起眉,认真低头望去。画稿上是笑着的容许,十几岁的少年面容清俊,身形清瘦,撑着一把大伞回首望来,脸上露出了柔软的笑容,眼睛像星星一样灿烂。仿佛是刹那间的心动。
容许看了一眼,就笑起来了。他搭着容光的肩,看着院外长得繁茂的梨花树,似乎在想些什么,半晌,大力地揉了揉女孩子乌黑的头发,笑道,“会好的。”
容许骗人。容光把未完成了画稿揉的乱糟糟的扔在地上,容许说会好的,最后还是骗她的。生日夜后那一晚,容许说,对不起,我让你难过了是不是。我还是走不出来。容光生气地想要打死他。最后还是乖乖地原谅他,每个月等着那薄薄的信来,对每封信最后容许的求饶嗤之以鼻,容许写,容容最好了,还没有原谅我吗?容光嫌弃极了,是啊是啊还没原谅,气的要死呢。她仔细折好了信,放进木盒中,收在抽屉里。撞上容爸爸容妈妈揶揄的目光,就红了脸。
反正画不出来,容光收了画架,坐在落地窗前看月亮。想着为什么这个月的信还没来。虽然这几天天气很糟糕,晚上还算凉爽,容光坐在窗前昏昏欲睡。
要不,这封信来了,就告诉容许,我原谅他了?容光恍恍惚惚地想,反正本来也没怪过他。就是容许傻傻的,才会当真呢。她埋首在膝盖沉沉睡去。
窗外,月亮干净地洒下光来,落在她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