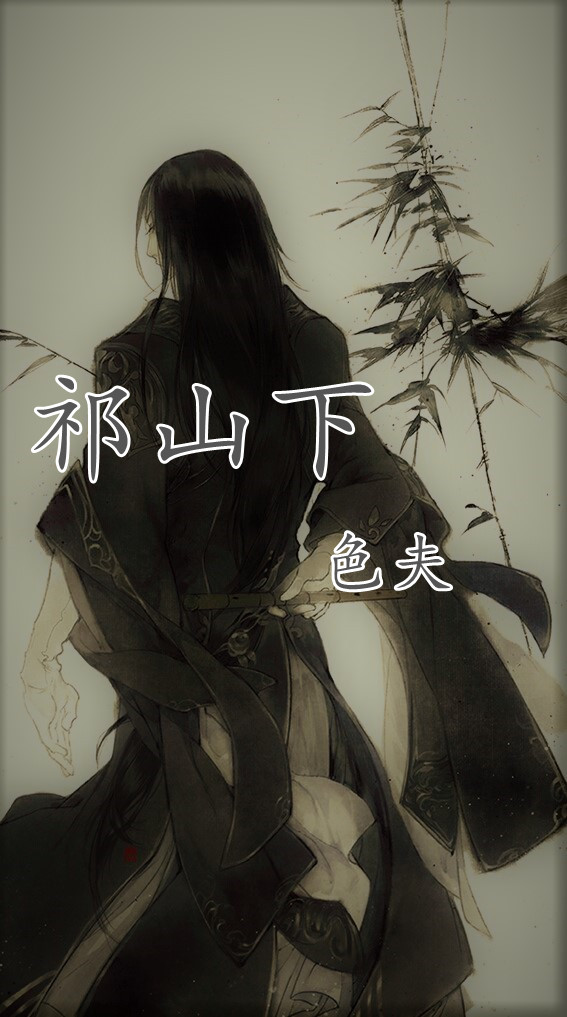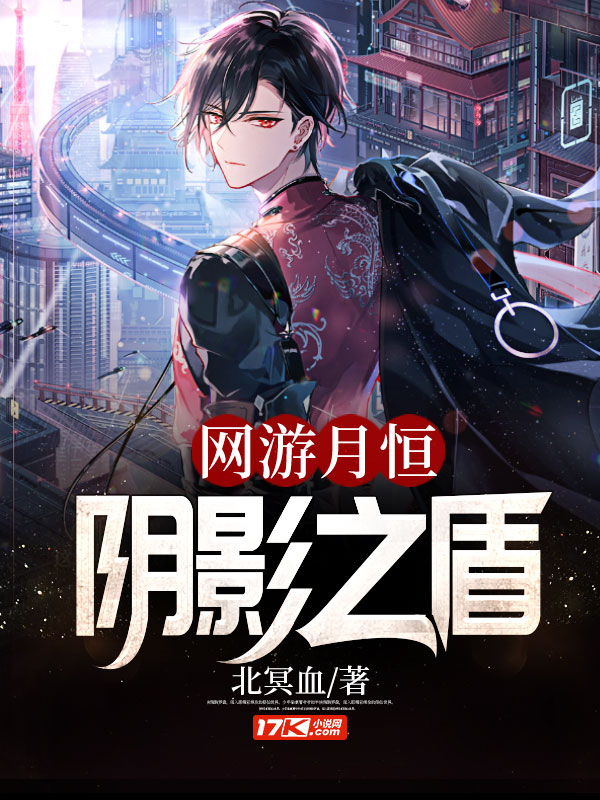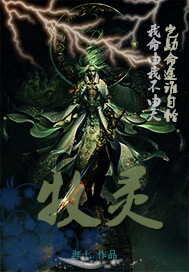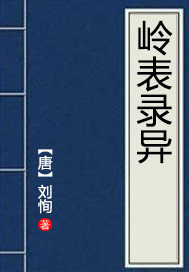江海市城南有座山,当地人叫它方山,方山脚下有一处果园叫福临果园,当地村民偶尔也会在果园里种上点茶树,福临果园尽头有一口水井。这口井年代久远,据说建于清初,开始的时候井栏井台都是用上等青石凿成的,还有个名字叫“山泉井”,一般说来,名字里带有“泉”这样的古井,都会被人称颂其水如何清澈甘甜,但遗憾的是,“山泉井”却没有这个口碑,这个井里的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口味一般,跟寻常井水没有什么差异,后来由于村名的搬迁,这口井也就废弃不用了,平时只是偶尔用于果园浇浇水。
但是今天来果园除草的人们总觉得这口井不对劲,究竟哪里不寻常他们也说不出来。最先感觉到的是一个姓沈的六十多岁老大爷,沈大爷早年在茶馆里当伙计,后来有了些钱就自己开了一家茶馆,如今已经在家闲居,虽说是闲居,但是沈大爷闲不住,平日里总喜欢捣鼓捣鼓种植的茶树,结了一生的茶缘是不可能因此而中断的,沈大爷还是天天饮茶,而且早中晚要各沏一壶。像他这样的老茶客,就称得上品茶专家了。今天傍晚沈大爷给准备收工回家的除草村民工人沏茶时,开水一从壶嘴里出来,马上觉得不对头,说水里有一股异味。村民们互相闻了闻,却没有什么感觉。
沈大爷问了问孙子道:“这水是从古井里打上来的吗?”,孙子回答说:“我们带来的水喝完了,我就去那井里打了些水。”于是沈大爷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古井,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井里跑进去东西了。”村民们都很好奇,忙问道:“沈大爷,为什么这么说啊?”沈大爷没回答,只是径直走到古井边招呼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说:“你们几个把这个压水井挪开。”这几个小伙子本来就好奇,于是几人上前合力将压水井挪到了水井旁边的空地上,此时正值傍晚,借着落日最后的这点余晖,沈大爷躬身探头朝水井深处看去,这也是是他后半生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井底赫然漂浮着一具长发飘飘的尸体,胆子小的早已开始作鸟兽散,胆子大的又往井底看了看后对沈大爷说:“沈大爷,咱们快报警吧!”说着拿出手机拨打了110。很快辖区派出所汪长顺带着几个民警到达了现场,看了看井底的女尸,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要向上级汇报,这就不是派出所民警处理得了的事儿了,因为这得请法医进行尸检以判明死因。于是,邢志国和林毅童真他们就来到了现场。。。。。。
江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负一层的法医室里,林毅注视着已经平放在简易的解剖台上的女尸,蛆虫可能是因为法医室里气温低的缘故,已经开始四处爬窜了,林毅顿觉胃里又是一阵翻涌,强忍着呕吐感,林毅深吸了一口气,作为法医的他,也只能开始硬着头皮尸检了。
有经验的法医尸检过程通常都是由上到下,由外到里顺序依次检查。林毅戴好白色橡胶手套,首先从女尸头部开始,女尸面部肌肉如同被刨子刨过一般,因为长时间水浸,血液基本流净,现在完全是一摊白森森的碎肉,五官面貌根本无法辨认,只留下眼眶内两个残缺的眼球和鼻部破碎的软骨组织。
林毅需要检查尸体颈部破口的创伤情况,这先得将女尸颈部的蛆虫清理干净,于是林毅在房间中找了一个直径约莫两厘米长约十厘米的棍状物,在木棍一头裹上无菌棉,捅进女尸颈部碗口大的创口里,躲藏在尸体深处的蛆虫受到惊吓,一窝蜂似的全部涌了出来,林毅一下一下的将蛆虫扒拉出来,只觉得头皮发麻脑袋嗡嗡的快要炸了,蛆虫一边翻滚着一边被林毅用棍子推出创口,清理了大概七八分钟后,见再也没有大规模蛆虫抱团取暖似的窝在一起后,林毅开始观察伤口,创口高度腐败,创缘特征不明显,无法辨别是钝器还是锐器伤。
想起此时应该拿相机拍照留证,于是走向不远处的办公桌,谁知他刚走两步就觉得不正常,好像是踩在了什么柔软的东西上,低下头一看,满地都是白色的蛆虫,林毅每一次落脚,都伴随着细微的噼里啪啦就像是爆豆子一样的声音,脑海里不禁想起了贝爷吃爆浆虫的画面,三步做两步林毅快速地取来相机用相机拍好颈部创口照片之后,开始向女尸腹部方向检查,由于女尸被发现时只有头部和双脚露在外面,已经高度腐败,但是泡在井水里的大部分躯干并未腐败,林毅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女尸的腹部,发现女尸体表已经僵硬,但是表面湿滑,泡在水里的部分已经开始出现尸蜡化,也就是说死者至少死亡一个月以上,林毅把这个细节记录在尸检报告上,接着是四肢关节,林毅活动了一下女尸的手臂,骨质相互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听在耳里极不舒服,感觉好像锯木头,活动膝关节也是如此,于是林毅断定女子生前四肢发育正常,无残疾,翻开右手掌发现女尸指甲缝里有一个木刺深深地扎进了皮肉里。女尸的林毅轻轻把女尸四肢摆正放好。
女尸外表已经差不多检查完毕了,林毅从装备箱里拿出剪刀,剪开女子身上的裙子准备开始解剖尸体。就在林毅拿刀准备划开女尸腹部时,法医室里的灯忽明忽暗的闪了两下,接着不断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本来气氛安静的解剖室,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歌舞厅,热闹而诡异,林毅委实被这变化吓到了,只觉得后背发凉,小臂上鸡皮疙瘩噌的一下子冒了出来,他连忙放下解剖刀,然后绷紧身体,深深地朝解剖台上的女尸鞠了一躬!法医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法医解剖之前都必须向死者鞠躬,看起来像是一场仪式,但更多的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