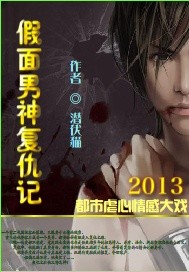“我说,眠你才奇怪吧,哭成这样还能这么清楚地说出话来—只是你的哀伤太过显眼了而已,没关系的。”看看。从来都不直接步入正题这点也很像呐,可是,光是哭着实在是感觉很蠢,所以晴明继续听着我这些含糊不清的唠叨吧,对不起了。
“主人。”迷糊中听到有人轻唤着晴明,我困极的昏昏睡着,只是翻了个身,余下轻微的话语再也没有入耳了,再后来有吵吵嚷嚷的声音大了起来。身边好像有人起身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晴明。”呢喃了一声又翻了个身,挡不住的睡意席卷而来,越发觉得困顿了。
“拭薇。”来人一把揭开身上的薄被,仍不愿睁开眼,只是缩回双手扯近一切温热的物件,于是乎就这么赖在地上和他死命的抢夺铺在身上的被褥。“松手吧,大哥,好困啊。”强夺了半天终是妥协了,懒洋洋挂在被子上,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托住尚且不住眩晕的脑袋,趁着还有睡意赶紧补个回笼觉。
“现在便如此不待见我了吗,拭薇,昨晚的承诺不作数了吗?”听他闲闲凉凉事不关己的语调,忽地就起了一团无名怒火,一个翻身坐起,无奈的懒懒抬起头有些愤恨的看向他,然后又无力垂下脑袋。“你有完没完!好不容易要遗忘的,作甚又要提起这话头,这样,”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声音中得微颤,由不得声音细小了下来,“你便可以释怀了吗?”许是情绪太过激动,心脉霎时间紊乱,胸口闷闷的感到不适连着喘息都沉重了起来。可是抬眼直面他时却又静下了心来,感受着他周遭蔓延来的冷冽气息,完全不一样了那,和在我身边时完全不一样的元炁。已经这样了那,原来是这么容易啊,从此开始学会与你陌路。“冬荆你没有梳洗吗?脸上很是狼狈那。”自己那场痛哭留下的残迹还没消退,苍白的脸映着红肿眼泡格外像是病重缠绵的人,而他似乎也是一样吧,眼尾微微泛起的嫣红颜色很是异样啊。很好,这样就不用担心他冷嘲热讽的,皱皱眉,装作一副轻蔑地表情。“那你,”他眼光流连在凌乱的床铺和我身上的褂衣上,开口问,“昨晚是留宿在安倍这里了。”冲他狡黠笑开,虚伪的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彼此彼此。”他似是不解的摇摇头:“安倍怎么也这般由着你。”我略偏过头,看向院中的荒芜,心中漾开浅浅的的温暖:“因为,他不是你!”
“不要再笑了!”他的声音突然间变得森冷起来,紧紧盯着我眼眸,“这样就开怀了吗?”避开他眼光,只是又伏在了被上:“只要还能笑就是快乐的,再说,给与我痛!苦!的!你!又有何资格这般质问我?”话音刚落两人之间的氛围周跌下来。
“咳咳,似乎是叨扰到二位了?”晴明斜倚在门框看着我们,唇间呷着促狭的笑。“没有的事,请说。”裹紧身上的褂衣,谦恭有礼的回应着他。“眠,有人想见见你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式神呐,要见吗?”“贺茂保宪?你师兄?”接住晴明伸来的手起身,理理衣衫,整整长发却始终打理不齐整。晴明轻拍我肩,说:“蹲下点。”我依言微倾下身,任他拿过木梳梳理起我的长发。终是忍不住感慨了起来:“晴明,你学什么都这么有悟性,真不考虑一下继承我的眼睛吗,若是你的话还不知道会赋予这双眼睛怎样惊艳的能力呐。”“耶~”“啊来,不要拒绝的这么干脆吗?”很是懊恼的皱起眉,我很认真地!眼角余光瞄着冬荆苦笑着不着痕迹的退了出去,好是尴尬啊,不知该怎么面对只好无视他,口中漫不经心地说出:“见见无妨的,可不想让你为难。”
“晴明,虽说你最经在斋戒本不应打扰,可实在是耐不住好奇了—那个真是的惊魂?”来人慵懒懒的端着我刚奉上的茶水如此评价鄙人道。贺茂保宪,贺茂忠行之子,其时与晴明并肩齐头闻名平安京的人物。“是,让您见笑了,正是区区不才。”抬起刚刚行礼弯下的腰身,抬起头刻意亮起眼底深处刺眼的棕红色,彰显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呐,眠可是来自西方之国的,保宪,不要这么无礼的看着小姐。”晴明喝了口茶点点头,装作一副礼貌恭谨的样子做了应答,“一是旧友托付,二来也怕她惊扰到那个男人,所以就收下了,谁知这小姐竟央求着要成为我的式神。”嗯,听着有些炫耀的调调,这个妖孽,好无聊!强忍着要打哈欠的欲望,可是这般围绕自己来历的对话实在是太无趣了。而余下他们那些关于咒术的讨论实在是太高深了,完全地跟不上他们的思维啊。
“因为担心你是不是……啊,看来是我多虑了,你没事就好,就这样吧,还有工作没有完成,我就先回去了。”临行时保宪多看了我两眼:“这是你为她构筑的身体吧,与你平时只爱妍丽女子的偏好可不一样啊。”这算是红果果的鄙视吗!?幸好幸好,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有自知之明,不至于因此动气,所以晴明,敢不敢不要这么轻易地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啊。“神情中掩不住的邪气,过于锐利的眼光,晴明,此人非善类啊,自己小心。”小心你妹!以为一把破扇子遮住嘴就听不见你说的话了!“可是,”你丫还可是,可那男人还是收起戏谑的表情,装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这么依靠式神可不行啊,事情还是亲力亲为才对修行有益。”晴明恭敬一低头:“是,我记住您的教诲了。”
明明已经送到门口,贺茂那竖子还是止不住的回头观望着我,摇摇头皱起眉上了牛车渐行渐远。我眯起眼,咬着牙:“晴明,可以对他下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