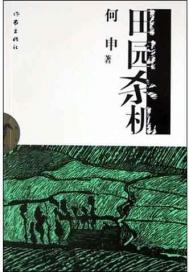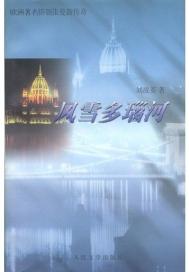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高适(唐代 )
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在雾气缭绕的水池中,盘膝打坐,汗液被他逼出身外,已经不是开始时的乌黑色,经过两年的《洗髓经》淬炼,汗液由黑变灰,由灰变黄,现在已经是正常颜色了,味道也是由一开始的腥臭无比,到现在的无味。几个大周天后,他突然从水池中一跃而出,穿好衣服向悟心壁观的山洞奔去。
“师傅,我《洗髓经》终于小成了,您快看呀!”朱原兴奋地一头冲进山洞,高声叫道。
但眼前的一幕,让他呆立当场,原先师傅壁观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地上一片枯草,他给师傅做的兔毛垫子也没有了。他仰天长叫:“师傅,师傅啊!您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声震山洞嗡嗡震响。他跪爬到师傅壁观的枯草边,抱起枯草痛苦失声,真好似黑夜进港的船只,没有了灯塔,心中没有了方向,四周一片漆黑,师傅我该何去何从呀?
正当他抱起枯草的时候,在地上隐隐约约好像有字,他赶紧拿开枯草,几行用手指在石板上写的字清晰可见。“当徒儿看到字的时候为师已经走了,为师很高兴徒儿能练成神功,虽是小成也实属不易,为师为你骄傲。为师因有少林俗事烦心,这两年功力始终不能寸进,为师是该到了此心魔的时候了,徒儿小成后也要离开此地去江湖历练,切记江湖险恶,不可轻信他人,切记,切记。”
朱原看了多遍,向南叩头道:“师傅,弟子记下了。”说完用左手在石板上一摸,所有字迹化作尘土,一阵儿风吹过,尘土随风飘落尘埃,一切已成过去。
当他走出山洞时,白狼叼着一个长条包袱跑了过来,放下包袱卧在了他的脚边,用大脑袋蹭着他的腿。他轻轻摸了摸白狼的大脑袋,白狼王放下包袱,对他呲了一下牙,一声低嚎,卧在了他身边。
朱原赶紧打开包袱,里面有四样东西,一样是一张孩子的小被,被角有个针绣的“原”字,这张被子悟心已经多次和他说过,是裹着他的小被,是他认祖归宗的信物;一样是一个小白瓷瓶上书金创药;一样是一个小红瓷瓶上书护心保命丹;最后一样是一条腰带,鲨鱼皮的外鞘上镶嵌着十二颗各色宝石,腰带头是紫金龙头,腰带尾是紫金龙尾,朱原见过师傅这条腰带,用手一点龙眼,龙口一张,一把寒光四射的宝剑弹射而出,剑身柔软异常但只要内力贯注这剑身立刻笔直坚硬,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蓝瓦瓦的剑身上“盘龙”两个篆字依稀可见。
朱原把盘龙剑围在腰间,龙头自动锁住龙尾,形成一条古朴精美的腰带,松紧合适很是可心。他收拾好包袱,提着包袱拍拍白狼的头,白狼王不耐烦的抖了抖脑袋,冲他一声长嚎,他已三晃二晃消失在山林中。
春风拂面,野花飘香。朱原正在斡难河打水,突然震耳欲聋的马蹄声打破了这宁静的草原。一人一骑在前面跑,二十多骑在后面追,不时还向前面的一骑射箭,利箭如雨点般从前者的身边飞过。众人越跑越近,已能看到前面是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后面是一群儿如狼似虎的牧民,前面的男孩只能趴在马背上,抱紧马鞍,拼命催马快跑,但胯下的马已经鼻喘粗气,浑身是汗,堪堪不支了。后面追的牧民都是一人双骑,挥舞着马鞭,好似猫戏老鼠一样,戏虐的追赶着。其中一个领头的大汉指着前面叫道:“铁木真的马快不行了,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抓活的,塔儿忽台大人一定会重赏我们的。”众牧民挥舞着马鞭一阵儿欢呼,好似铁木真已是他们囊中之物一样。
朱原本来没想多管闲事,远望了一眼就要打水上山,但当听到铁木真这个名字时,不仅微微一动,打了水站到了河边,看着男孩骑马跑了过来,当看到是他记忆中的面孔时,让过了他,迎着追赶的牧民走去。
转眼间,牧民们已追了上来,为首的挥舞着马鞭大喊着:“走开,快走开。”一边纵马狂奔,一边挥鞭向朱原头上抽去。
朱原一侧身闪开那一马鞭,手中抡起两个硕大的水桶,如车轮般闯入了奔马队中,只见尘土飞扬,桶影飞舞,众马腿纷纷被打折,马儿在哀嘶中前冲倒地,牧民们纷纷滚鞍落马,摔得鼻青脸肿,在地上翻滚哀嚎。尘埃落定之时,朱原提着水桶把满满的两桶水重新倒回了河中,草原上水是宝贵的东西,不能随便浪费。
前面狂奔的铁木真忽听身后的声音不对,拉住坐骑,带转马头观看,只见远处一地的哀嚎嘶鸣之声,部分牧民已经抽刀站起,怒目而视河边的少年,大有一拥而上之势。铁木真刚才没有注意,现在仔细一看,那不是朱原吗!那次虽然是短短的一面,但朱原那力劈雄鹿的神力,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刚想催马上前,却见朱原一声长嚎,声震山谷,紧接着山谷中回应了一声长嚎,过不多时数十声嚎叫在山谷中回荡,听的人胆战心惊。
牧民们大叫:“不好,狼群来了,快跑呀!”但为时已晚,狼群已经包围上来,就是河对岸也隐隐有狼的身影。
上百头的壮狼在白狼王的领导下呼啸而至,泛着绿光的双眼盯着牧民,獠牙已开只待饮血。白狼王跑到了朱原身边,一声低嚎呵住群狼。朱原轻轻拍了下它的头,安抚了下它躁动的心。对牧民道:“马留下,人走吧,不要再来不儿罕山,否则就同这些马一样。”说完一拍白狼的后背,道:“马是你们的了,人放了吧。”
只见白狼王对天一声长嚎,众狼一边警觉着牧民,一边扑向了倒在地上的马,四十多匹战马在狼群的撕咬中痛苦的哀嘶。不一会儿的工夫地上只剩下了战马森森的白骨,空中还飘散着浓重的血腥气,牧民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朱原走向不远处的铁木真,铁木真赶紧跑过来谢过了他的救助之恩。朱原笑道:“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你怎么到这里了呢?”
铁木真痛苦的回忆道:“上次分手后,阿爸带我前往弘吉剌部相亲。按照蒙古的旧俗,两家结亲后,男方要在女方家住一年。也因此,相亲结束后,阿爸便独自回家。在回家途中,遇上一群塔塔儿部的勇士在聚餐。阿爸欣然去吃酒,塔塔儿人在马奶酒中下了剧毒。阿爸死在了回家的途中。阿妈托人叫回了我,我们被族人抛弃了。部落族人追随着曾经的依附者泰赤乌贵族塔儿忽台走了。我家境由贵族沦为贫民,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所幸的是札木合安达不弃,和我们一起打猎、钓鱼,后来我们交换了结盟的信物,再次结为了安达。昨日泰赤乌氏偷袭了我们在斡难河畔的营地,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抓我,就想把他们引开,向不儿罕山逃来,我们约定事了后在不远处的孤山相会。”
朱原听后点了点头道:“你和我也算有缘,来吧,到不儿罕山躲上几天吧,不用担心,长生天会保佑你的家人的。”
朱原见铁木真牵着马,就把他带到了悟心大师壁观的山洞,对铁木真道:“委屈你就在这里小住吧,不要下山,山上有野果、山鸡,山的深处有水源,这里有白狼王保护,只要你不出去是不会有人来的。”
铁木真谢过了朱原的好意,但也表达了自己对家人的思念,道:“我们一家是多灾多难的一家,我和我的家人被部族所抛弃,我们相依为命不能分离,我现在的心理只有家人的安危,这比我自己的危险更让我牵挂。”
铁木真对家人的亲情打动了朱原,这是朱原心中的痛,他太渴望亲情了,他认真的道:“铁木真你听我的安心在这里住下吧,我会下山,去找寻你的家人的。”说完也不等铁木真开口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铁木真还想再说点怎么,但朱原已消失在了山林中,他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栓马走进了山洞。
转眼间九天过去了,朱原再也没有来山洞,山外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人对事情越不知道越往坏处想,几天的思念煎熬着他的身心,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他要出山去寻找他的家人,这个声音一直在心中回荡,挥之不去。他吃不香,睡不安,只短短的几天,人就瘦了一圈。我不能再等下去,我要去找我的家人,我不能没有她们。
第九天的夜是那样的漫长,思念终于战胜了理智。他借着月光牵着马走到了出山口,山口处死一般的宁静,黑暗笼罩了一切,铁木真一咬牙,心一横,翻身上马,打马如飞似箭般冲向了山口。正这时山上传来了一声狼嚎,他先是一愣儿,以为白狼王要阻止他出山,下意识地马上加了一鞭,马儿吃痛,撒开四蹄奔出山口,冲入黑暗。
刚一出山口,眼前就是数十人的马队,在月光下泛着寒光的利箭齐刷刷的对准了他,他立刻拨转马头,身后的山口已经被两排马队挡住了,四周的包围圈在一点点的缩小,火把被点了起来,铁木真已经看到了塔儿忽台那得意的笑容和轻轻划弄胡子的动作,不能再犹豫不定了,战是死,委曲求全可能能生,塔儿忽台自大而好名,阿爸曾经救过他,他不一定现在就杀了我,想到这,他果断的扔了马鞭、佩刀、弓箭,翻身下马,自背双手道:“塔儿忽台大叔,我有何罪,使是苦苦相逼?”
铁木真这一问,使塔儿忽台反而一愣儿,大笑道:“草原上弱肉强食,这就是长生天的安排,念你阿爸曾对我有恩,小子我就让你多活几日,等祭天大典上就拿你祭天好了。来人呀,给他带上枷锁,关进牢笼,好生看守。”
众人答:“是”,一捅齐上,七手八脚的先是一顿毒打,然后上了一个特大号的木枷锁,把铁木真关进牢笼,高高兴兴的回营地吃肉喝酒庆祝去了。
当次日上三竿之时,朱原才一身灰尘的回到了山洞,但洞内洞外并没有找到铁木真,他就心道不好,再一找马也不见了,就知道铁木真一定放不下家人,出山去找了,怪不得山口的埋伏撤了呢。
这几天朱原沿着斡难河寻找铁木真的家人,也去了铁木真说的那个孤山,都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他们受袭后废弃的营地,朱原叫来了白狼王,让它沿着气味寻找,最后在斡难河的一条支流乞沐儿合小河旁边的一座孤独的小山中找到了她们。原来她们等泰赤乌氏走后,不敢在附近停留,那个孤山太显眼,她们只能趁夜色掩护向更远更偏僻的地方迁徙。
朱原把铁木真安全的消息告诉了她们,铁木真的阿妈诃额仑夫人高兴的哭了起来,铁木真的兄弟跪地感谢长生天的眷顾,铁木真的妹妹帖木伦微红着小脸,如星辰般黑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看着他,看着他心里好似有只小兔子,怦怦乱跳,只想早点逃走。
于是朱原对诃额仑夫人道:“现在铁木真也非常想念你们,我要早点回去告诉他你们的情况,也使他安心在不儿罕山避难。”
诃额仑夫人一家千恩万谢地送走了他,在原地安心地等铁木真回来。
现在铁木真大概被抓走了,朱原也不能袖手不管,他只能再次下山,向泰赤乌氏的牧场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