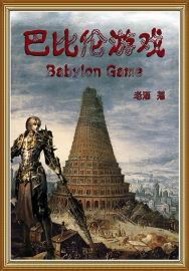这显然不合逻辑,大老远的,又得披荆斩棘,闲的慌的人都不愿干。如果他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岛上,那根据报纸的年限,他们似乎策划了很久,按理说这里离大陆又不是很远,无需筹备这么久时间,而根据他们所带的物件来看,也不像是筹备很久的一只队伍。
我坐在岩石上,屁股下冰凉冰凉,山谷的夜晚着实寒冷,起身又寻了一些树枝,把火添大,引了几把火苗放在岩石下面,没多久,岩石被火焰烘热,坐在上面很是舒服。
接着再想,想的迷迷糊糊,明明毫无睡意,可眼皮居然无法自控的往下合拢,那就先眯一会,我躺在岩石上假寐。躺下没多久,突然感觉有一道电流串到手臂上,跟着顺着我的血液,传输到身提,最后聚在胸口部分形成一股漩涡,漩涡不断的在我体内旋转,接着像是无休止的往下转,我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很不舒服,有种气闷作呕的窒息感。可怕的是,心里明明想着挣脱,四肢却像是让什么东西给压住一样,软绵绵的,一点劲道都使不上来,只是憋着难受。起先我以为这是梦境,可是我的大脑又是异常的清晰,不仅能听火柴燃烧着的声音,手上也能感觉到火苗输送过来的热气,同时,我还听到了同伴们不同频率的呼吸声。
我敢肯定我是清醒的,可是就无法睁开双眼,四肢仍旧一动不能动,感觉被什么东西压的全身乏力,而那股漩涡仿佛越转越往下,搅的我喘不过气,意识清晰的我,心底泛起了莫名的恐惧感,如果再不挣脱,我想我一定会窒息而亡。当感觉死亡笼罩过来的那一瞬间,也不知自己哪来的力气,动了一下手臂,人就恢复过来了。我慌身坐起来,头上已是大汗淋淋,拼命的大口喘息,待人舒服后急忙环视四周,旁边什么都没变,还是一样的火焰温度,火堆旁边扔着一堆吃剩下的骨头,同伴们还是一样频率的呼吸声。这一切让我惊魂不已,恍如梦境。没法解释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难道是鬼魅缠身?还是这个山谷有邪气?
想到有可能是非人文化的东西出现,只觉得背后是阴风飕飕,正在烟盒里掏烟的手也不禁抖了一下,我尽量宁神,不让自己多想,过了好一会,才逐渐让心情平复下来,稍稍积攒点信心的我自嘲,刚才是不是过于胆小了,现在青年怎么还迷信鬼怪这一套,也许这不过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生理现象。
正在我对自己刚才发生的状况东扯西想时,眼前一晃,仿佛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真活见鬼了,一波未平一波又来。我第一反应先回头看了看同伴,见三个身影依旧躺在那里,那就有点不对劲了,这个鬼地方怎么尽是出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我急忙掏出手枪,四处打量,微光中什么都没看到,山谷中静的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又连忙从身旁拿起手电筒,照射四周,环绕一圈,还是空荡荡的,光线经过的地方一如既往的平静,连虫鸣的声音都没传进我的耳朵。
那刚才这人影是?我不敢再往下想,再想下去就是自己吓自己了,我宁愿刚才是我眼花。
我战战兢兢的回到火堆旁,光亮还是能稍稍平伏一下内心的胆怯,但是这种胆怯在漆黑的夜色笼罩下只会无止境的蔓延开来,这样一个人坐着,心理不仅饱受煎熬,对心灵的摧残也太大了。妈的,不管了,叫醒大头,让他陪我一会。欲待起身,突然脖子一凉,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次眼睛一闭,仿佛将我领进了一个虚度空间,只有灰白两色的世界里,有很多张熟悉或不熟悉的脸孔在我眼前飘忽而过,一晃不见。很多听过或者没听过的声音回荡在耳边,呼唤我的名字,还有父亲的背影,一次又一次绝断的远离我与母亲,在我与妹妹撕心裂肺的哭泣下,他才不情愿的转身漠视,在他转过身子的那一刻,看到的不再是父亲那张严峻的脸庞,而是转变成了师傅的脸,和蔼和亲,憨笑着向我走来。
吃了二十三年的饭,我一直想不通父亲为何宁愿常年浪迹在外,也不愿意多点时间留给这个家庭,在他的生命里仿佛这个家就没有值得他眷恋的地方。从小,他就让我从师学艺,师拜木家形意拳,害的发小大头初中都不学了,也被他爷爷送去练武。
索绕二十年的问题,一幕一幕的浮现在这个虚幻的空间里。
等我醒来时,眼角却还残留着泪珠。我看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这是一张放在房间里的席梦思床,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单。
孤岛上怎么会有人家?我现在身在何处?大头呢?于兴旺跟刘旭呢?房间里除了冰冷的墙壁,空荡荡的,怎么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还是我在岛上死于非命已经离开了阳世?不对啊,外面有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难道阴间也能阳光普照?
正在我疑惑不已之际,外头推门进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高挑的个子,纤细的身姿,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虽然是一张陌生的脸,说话却一点都不生疏:“你醒了?”
“你是谁?这又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迫不及待的提了一连串问题。
“我叫孟蕾,这里是湛江,你现在躺着的地方是我父亲开的私人诊所,在你昏迷时,你朋友将你送过来的,看来你挺有钱的,你朋友给你要了一间最好的单人病房。”姑娘很有耐性的一一回答,笑意嫣然,嘴里发出来的每一个字如露水滴珠般清柔,乌黑明亮的眼睛落落大方的看着我。
好美的女孩子,心底的赞誉油然而生,不过现在我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证实。
“湛江,诊所?你是护士?”大脑有点懵,努力回想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记得我们原本是在岛上寻找宝藏的,难道那晚受惊过度?昏迷后大头他们把我送过来的,这么说我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怎么会这样。急忙问孟蕾:“我昏迷多久了?我的朋友们呢?”
“ 我不是护士,我父亲是这家诊所的大夫,我只是凑巧过来,你的朋友昨天下午把你送过来,根据他们的讲述,再算上今天你应该昏迷了八天吧,现在是吃饭时间,你的朋友们都出去吃饭了。”
“王八羔子,太不够意思了,把我一个人仍在这里。”我低声骂了一句,心里有暗暗惊奇,怎么昏迷了这么久?
“你说什么?”孟蕾愕然。
“没,发点牢骚而已,对了,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吗?是不是受惊过度?难道我的心理防线这么脆弱?”
“怎么会是受惊过度呢,”孟蕾微微一笑,“我问过父亲了,他说你这是让人注射了高强度的迷魂药物,所以才会睡的这么深,不过你放心啦,这种药物只是令人昏迷一段时间而已,没有别的危害。”
“我让人注射了迷魂药?”我努力索思当时情景,这怎么可能,难道当时还有别的人在山谷里,就算有人的话,想近我身,我怎么可能毫无知觉?
“是的。”孟蕾干脆会道。
“怎么可能?”我迷惑着自语。
“你不知道有一种枪可以发射针式迷魂药吗?”孟蕾见我独自发懵,解释道:“在你的左边脖颈有过被针插过的痕迹,那你就是你中招的位置。”
我用手摸了摸左边的头颈,什么感觉都没有,疑惑的微蹙眉尖。孟蕾扑哧一笑:“针孔细如发丝,又过了这么多天,只有仪器才能检查的出来,用手怎么能摸得到。”
“那迷魂针呢?”
“据你朋友所说,他们醒来发现你昏迷不醒的躺着,怎么叫唤都苏醒不来,但是当时并没有在你脖颈上发现有迷魂阵之类的东西,可能对方为了不留痕迹,射完之后就取走了。”
我挠挠后脑,不好意思的笑笑。想不到岛上还隐藏着这么一位暗箭伤人的鼠辈,也不知道跟那几个死去的人是不是一伙的,不过此人看来并无取我性命之意,否者哪还有这么舒服的床睡。而大头他们发现我昏迷之后,肯定也是无心寻宝,着急将我扛回船上,一想到那条崎岖的山路,轻装独行都这么费力,几位兄弟还要把我这个一百多斤的人给弄出来,其中不易是可想而知,也够为难他们了。我靠在床上怔怔发呆,孟蕾给我倒了杯水,我接过喝了一口,问道:“你在这里给父亲帮忙?”
孟蕾说:“没有啊,我呀,平时很少来这里的,昨日在这里凑巧碰到了你们,又凑巧的遇到你那个既友善又喜欢说话的朋友,又凑巧的听他说了一些关于你们的英雄事迹,又凑巧我对你们这些事情很感兴趣,然后我就特意在这里等你醒过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