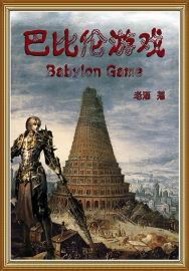我站在原地沉默不语,暗自感叹人世险恶,一边寻思着下次跟张罗碰面应当如何提及此事,一边想着复原一下当时场景,索思王九如何能做到一脚蹬飞格罗姆人的同时又能迅速的撤离,隐隐中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边想边比划,不知不觉蹲下身子,在地上拿石字勾画,突然想到一事,猛的一抬头,发现夫妇二人还站在跟前,歉意一笑,忙问男子:“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你的同伴是被人扔出去的?”我怕他没理解进去,一边说,一边做手势。
男子点了下头,说:“是的,我亲眼所见,就是单手拎起来抛出去的。”
还是单手?那臂力得多大,我不敢想象,背上只冒冷汗,这种臂力我是自愧不如,就算大头,怕也没那个本事。照这么说,王九的人品固然值得怀疑,但是他一定还揣怀另一种目的,明明有着高深莫测的武艺,却一直装疯卖傻欺瞒大家。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另一件事,顿觉脊背发凉。当初杜利军与大伙反目成仇,王九随杜利军而去,之后两人销声匿迹,直到千纸鹤获悉杜利军被人杀害。如此看来,杜利军很有可能就是王九杀死,照这么看来,凭王九的心计跟武功,他要是有心向杜利军下手可谓轻而易举,若杜利军果真是王九所害,目的就是为了独占千年珊瑚。白沙岛时,王九说珊瑚已经物归原主,看来真被孟蕾猜中,一定不是交给张罗,背后另有其人,红哥显然不是,这人在千纸鹤口中只是奴才一枚,那会是谁呢?只怕这个神秘的人或许跟千纸鹤还有一定关系。
我不再逗留,满怀心事告别男子夫妇,过去与陈专家几人汇合,此时陈专家已探查的差不多,采集了满满一袋样品,全由阿克巴多背在身后,陈专家任务已完,四人不再逗留,动身回部落。
回到部落已是次日傍晚,陈专家一进门就说去找拉古布拉的父母询问事情,这倒称奇了,两亲家聊天形如鸡同鸭讲,看他这位老气横生的专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语言天赋。
拉古布拉还没苏醒过来,在房间里没陪多久,阿克巴多着急着让我与胖子去他家中坐坐,拗不过他一脸的热情,二人随其身后前往叨扰。我上次去过阿克巴多的家,当即也不客气,率先走在前面,走到门口停下,准备推门进去,阿克巴多后面推了推我,示意我再往前走。我不解的问:“不是到了吗?”
“还没呢?”阿克巴多乐呵呵的笑着,喜不自禁的说:“还在前面一点点啦,告诉你俩一个事,兄弟我今年结婚了,所以就搬出来另筑了一个小窝。”
“结婚?”这消息实在太让人意想不到了,我开心的一拳锤在阿克巴多的胸膛上。“好啊,小子,嘴巴这么严,在一起几天了也不知会一声。”
“恭喜,恭喜,”胖子马上抱拳道贺。
阿克巴多在我两的贺喜中,羞涩的摸着自己的头,我拉住他:“可是兄弟我现在身上没一样像样的随礼东西,就这样两手空空的进去不合规矩吧。”
“咳,要啥随礼,这里不同中原,没这么多繁文缛节,”阿克巴多手一扬,满不在乎地说:“我们现在啥都不缺,只要你能过来喝杯栗子酒,我已心满意足了。”
实在也拿不出东西,连防身武器昨日都在阴阳谷送人了,现在身上除了那个用来送给妹妹的木盒子,兜里空空如也,不送就不送吧,我喜滋滋的问道: “谁家的姑娘啊?”
“到了,到了,”没走多远,阿克巴多把我们领到一座木屋前面,指着房子自豪的说:“你看,全我自己动手盖的,还不错吧。”
木屋盖的确实很别致,单层结构,全是用大小相仿的杉树垒叠而成,房子四周围了一层走廊,走廊上摆满了鲜花,有山茶、兰花、报春、绿绒蒿、百合、杜鹃,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看来阿克巴多在上面下了不少功夫。踏过几节台阶,阿克巴多推开门,大喊:“珍子,珍子,你看谁来了?”
珍子?阿克巴多的新婚妻子是珍子?当头棒喝!怎么会是珍子,阿克巴多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犹如晴天霹雳,被击个正着。僵在门口,从头冷到脚,只觉得天昏地转,这一脚怎么也迈不进去。阿克巴多正欢喜着,也没察觉到我的失态,边喊珍子,边把我往里拉。我的两条腿就像被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迈出第一脚时,心存最有一丝侥幸问道:“是那木和叔叔家的珍子吗?”
一出口,就讥笑自己犯了低级错误,记得去年住在那木和家中时,听他讲过因为娶了个汉人妻子,所以珍子才有了个汉名。纵观整个部落,除了那木和家中有汉人印迹,还能有谁家的姑娘还取汉人的名字。
阿克巴多并无戒疑,爽朗说道:“还能有谁,这说来还得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把那群魔鬼驱赶出去,让我跟着沾光,成了族人心目中的英雄,我也就得不到世间上最美女子的垂情,所以你这个媒人今日说什么也得到我新家来多喝几杯酒。让我和我美丽的妻子为你斟满一杯祝福的酒。”
正说着,屋里出来一人,不是珍子还能是谁,除了发饰稍微有一点变化,还是那么秀雅脱俗,娇美动人。那木珍子对我们的拜访虽然也表现出了欢喜,却没阿克巴多这么激烈澎湃。站在门前,羞涩矜持的看着客人,一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微微含笑的小嘴,嫣然如天使般的让你不忍亵渎。
我只觉得自己脑子在旋转,像是得了美尼氏综合症般的旋转不停。这就是让我千思梦绕的女子,这就是让我无数个夜晚对着暮色吹口琴思念的女子。此刻真真切切的站在我的面前,却已身着嫁衣为人妻。
物是人非事事休,这一刻,我的梦破了,心也随之碎了,破的很彻底,碎的很倏然。当我看到珍子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来见她,那种被勾略起来的思念和情爱,搅的我五脏六腑全不是滋味,甚是寻死的念头都有。
那木珍子含着笑,招呼我俩入座,还说自己一听说拉古布拉回来了,就马上赶过去看望,可惜她还在昏迷着,言语中尽是替好友担忧。
我耳膜里只觉嗡嗡作响,呆滞的踏进屋里,毫无知觉的被主人按在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还有勇气坐下来,难道是给自己的爱做一次告别,还是准备用酒精把这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彻底的埋葬在这块纯洁朴实的土地上。
阿克巴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利索的摆好酒具,将桌上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他很开心,他不停的侃侃而谈,谈略楼族人的新生活,谈自己对美满日子的展望。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这对新人的房子,只记得自己灌下最后一杯青稞酒的时候,脑袋变的异常的沉重,已经超越了身体所能支撑的范围,一头砸在了桌板上。醒来时,正是中午时分。这一觉睡的足够沉的,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既然是拉古布拉,她坐在床杆上,憔悴的脸上含着笑容,再她的身后站着珍子、阿克巴多、那木和夫妻二人与陈专家,后三人正聊的起劲。
“你醒了?”拉古布拉面带微笑握着我的手,柔声问道。
“你也好了?”我从床上坐起来。
“我醒过来也只比你早了一点点,”说完,拉古布拉又轻声的对我说了一句:“我一直担心再也见不到阿爸、阿妈,谢谢你呀。”
我看到珍子那一刻,还以为她们是来看自己的,原来是拉古布拉的原因,心头不免失落,打量了一下房间,问道:“我睡了多久?”
陈专家听到声音,回身大声说道:“把自己喝成这样也不嫌脸臊。”
珍子闻声,婆娑过来,故意拉长个脸,责怪道:“你也真是的。”
我心中一惊,以为自己那点心思昨晚酒后失态叫她俩夫妻瞧出了端倪,耷拉着脑袋,忐忑不安。
珍子见我为难,扑哧一笑,微嗔道:“你倒会瞒,整个部落都知道你跟拉古布拉的好事,我这位好友倒成了最后收到消息的人。”
一听如此,我松了一口气,也不知道这是一口什么气。心中暗自叫苦,赶鸭子上架的恋情,怎比的上你俩甜蜜的郎情妾意,不敢面视珍子,看了一眼拉古布拉,微微一笑:“我以为阿克巴多跟你讲过,”跟着又充满醋味的说道:“你还不是一样偷偷的嫁人。”
“好了,好了,你俩谁也别埋怨谁的不是了,”阿克巴多站出来说:“刚才族长说了,今天全族要举办一场隆重的歌舞会,一来欢迎我们永远的好兄弟,未来的略楼族女婿,二来为拉古布拉的重生庆喜。顺便再亲自向你和拉古布拉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