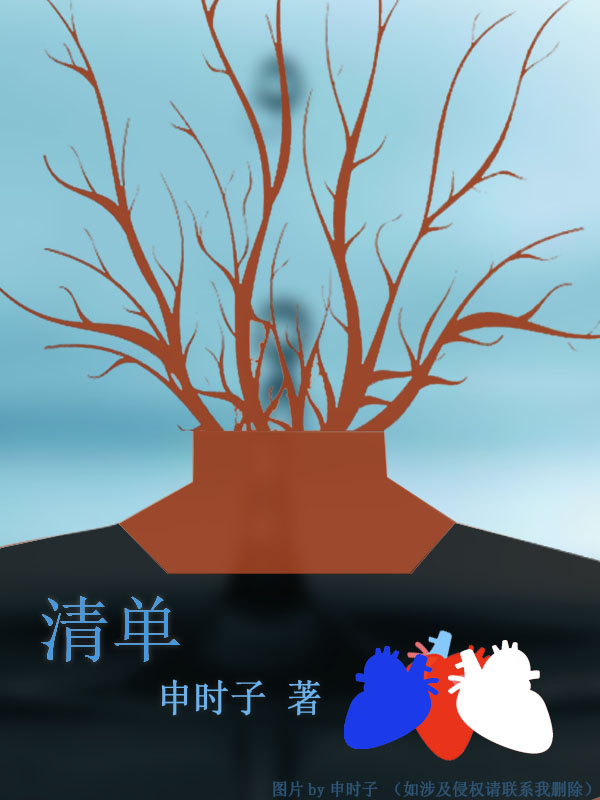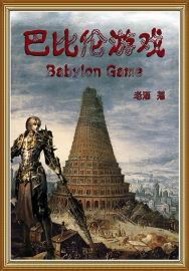再往复杂的地方去想,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肚子里怪笑一声,看着枕边的背包,忍不住拿出父亲的那本日记,稍作迟疑,我翻开了它。
日记一:“今天,船向泉州靠港后,第一件事情,我便是着急的去新华书店买了一个本子,顺便还买了一本高尔基的《童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记载日记了,当我翻开第一页时,脑子里鬼使神差的冒出一句话,于是像个诗人般的把它写在了封页上,写好后,默读了几遍,感觉太贴切了。这是心境,还是抽风,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只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日记与冒险一样都不能少。没有日记,我仿佛少了一位交心的朋友,没有日记,心情落空时便没有寄存的地方。不去奔波,荡悠,感觉那就不是自己。当把日记本平展在板子上的那一刻,就像久违的朋友重新相遇一般,很亲切,很有充实感。
看来父亲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从文字上判断,他写日记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记述点生活中的琐碎事,而是通过日记,以达到自己与自己的交流。从通俗的理解上,这种性格的人叫自言自语,或者自哀自怜。往意境上来说,这就叫做心与灵的交汇。
父亲怎么交汇,怎么自哀自怜都不重要,让我心里不爽的是,他居然说自己生命中离不开的只有两样,一样是日记,一样是冒险。可恨的,居然没有自己妻子与子女的一席之地。尽管我认为我在努力的为他换位思考,可是就看了这么一小段,心中的无名之火又冒升起来。悲恨交织,我狠狠的把本子摔在床的另一头,不解气,又朝着它蹬了一脚。
心头颤颤的难受,憋了一会气,考虑到到晚上睡觉自己的双腿会不老实,怕把本子给拿脚蹂坏,用脚一勾,抓住勾来的本子,顺手往背包里一塞,蒙头大睡。
经过一轮朗日,经过风熏浪敲,我心中的气顺了许多。由于我这人想事多,总不易睡觉,基本上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睡觉,夜深人静时,最易进入苦思冥想。思索入睡倒也成了习惯,最怕的是,有时候越想人越清醒,把人折腾的,就算拿脑袋往墙上撞都无济于事。
倦鸟归巢的心只要出过远门的人都能体会的到,除了嫌航行的速度慢之外,剩下的还是嫌它慢。等待中的时间是最漫长的,寒冬深夜,没合上眼的又只剩下我一人,闲来无事,我脑子里再次想到了父亲的日记,忍不住,展开续看,在第一篇的日记底下,看到日期注明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按落笔时间来算,这本日记到现在已经有个五个多年头了,比傅满江讲诉父亲来白沙岛的时间,差不多提早了七个来月,如此看来,这本日记陪着父亲度过了七个来月的日子。
我翻开了下一页。
日记二:“我不知道我的双腿能尺量多少距离的路程,在为信念,为生计奔波之余,我亦从中寻找自我,如同革命一般崇高,如春风拂过,江水洗涤般清纯,我无需向世人长鸣,只需自己心底的那一声轻微的喃喃声。夏蝉在枝头上低吟,寒梅在严冬中傲放,当船只破水前行,我,义无反顾,我,永不停息,只为了那一道彼岸。每天清晨,当第一缕辉光照射在我的船身上,我笑了,笑的是那么的洒脱,笑的是那么的爽朗。哪怕世间无人识得我笑意何在,然后,我清楚,大海知道,晓风明了,足矣!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
日记三:一杯酒,一支烟,和着暮色,对着朦胧的天际,还有何事能比这更叫人惬意。坐在甲板上,望着余晖,感觉自己正在驱动着渔船追赶日落,我舍不得逝去的时光,就如同我舍不得放下自己的梦想一般。每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次日它依旧会轮转回来,可是,我流逝而过的岁月,谁能将它重新送还给我?既然时不再来,那我唯有不知足的将它绽放开来,开在自己的心田,开在自己的记忆。如果不出什么岔子,后天我们便将抵达目的地,自从新认识了这位有钱人,往后,根本就不愁手中寻到的宝物卖不出好价钱。看来这次也不会列外,刘德一(刘旭的父亲)这家伙,眼睛就是厉害,比千里之高的老鹰还要敏锐,居然又让他发现了一样好东西,若非今日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或许明天就能见到买主了,只能自己宽慰,好事多磨啊,好事多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
日记四:在我兜里揣着厚厚一叠子钞票走在异乡的街道上,欣喜之余,却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个举国悲痛的噩耗,我们伟大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了。街道的风,冷的让我身躯发抖,原本喜悦的心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周总理是我敬佩,是全国人民敬佩的好总理,我在缅怀他为祖国为人民所付出的丰功伟业时,泪水从眼眶中流了出来。回到招待所,我想记下点什么,关于自己沉痛的心情,关于总理在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可是紧握钢笔的手,却不知道如何落下去,只能任凭悲戚的泪水滴在这一页日记上。呜呼,哀哉!人固有一死,却有泰山鸿毛之分,想着自己如幽灵般游荡在陌生城市的角落里,时常自问,是不是应该歇歇脚了?还是真的可以义无反顾的把自己这块卑微的身躯埋葬在大海底处?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号
日记五:本计划这几天回家一趟,却因朋友相邀改变了初衷,可能需要再耽搁一段时间,只能跟家中的妻儿在此道一声抱歉了。听说这次有点棘手,事情也远非前几次这么简单。睡不着,起身想找刘德一说说话,刚还在,这回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前后找了一圈,人影都不曾见到,哎,想必又跑去见那个骚娘们了,只能叹声哥们活的比我精彩。无奈,只有掏出日记,找这位老朋友说说话,也就它最贴心了,陪着我风里来,浪里去的,更不会在我最需要人倾诉的时候撇下我不管。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号
日记六:俗话说,山自有路,水自有道。我在探寻大自然的奇妙之外,同时也在为自己的财富而努力,我这么做可谓是有价与无价之间起到平衡,可是有些人呢?似乎贪婪的没有底线。原本好端端的一次合作,却因有权势人的介入,让整件事情变的扑朔迷离,而我,亦是举旗难定。看着五两半(父亲一个朋友的绰号)被人硬生生的打断了一条腿,以此来要挟于我,我该如何权衡此事?原来权势可以这么轻易的践踏凡人的尊严与自由,就算我举目苍穹,又向谁去寻求答案,老天?算了,还是自己想法子吧。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号
父亲的日记本上前后总共才写了六篇日记,字行都很短,基本上是一行一句话,讲述的成分不多,更多的抒写着自己的心态。看完后,我更是无法入眠,尽管字眼里提到家人就寥寥一两句,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的父亲,以及他的另一面。
在最后一篇日记引起我的深思,他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是被逼式的麻烦,很可能跟寻找七件宝物有关。而里头提及到的这位有权势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指傅满江?但是根据这几天与他的接触,又觉得不大可能,难道还另外有人委托父亲寻找宝物?用委托可能不合适,应该是父亲不想答应对方,搞得对方恼羞成怒,最后只有打断父亲船员的一条腿,更甚者,直接将他囚禁起来,以此来要挟父亲。
在三亚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一个神秘的妇女,拿着刘叔叔的一份信笺让我们打道回府,当时我们就判断刘叔叔很有可能受制于人,如此看来,这个可能性很高,不仅仅是刘叔叔,包括父亲或者船上的其他成员,都很有可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若是这样,我想放弃寻找父亲,似乎很没道理。另外,傅满江对整件事情到底了解多少?不管怎样,若是真决定继续寻访下去,目前起码掘开了冰山一角。
次日,我并没有向谁提起过日记里的内容,当初大头好像翻看过,但是以我对大头的了解,他肯定没正儿八经的往里看,否则他早拿这事跟我说了。
得知父亲正在受迫于人,我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旁敲侧推是我一贯的作风,找了时机问傅满江:“据你所知,寻找七件宝物的人,除了你之外,你能确定另外几波人都是谁吗?”
傅满江不假思索的回答:“记得之前在山洞里跟你提及过的。”
“你了解他们吗?”我复问。
“怎么了?”傅满江反问。
我呵呵一笑,托词道:“不管是寻宝,还是寻父,以后难免要与这些人打交道,早做了解总是好的。”
傅满江叹了口气,说:“各干各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中国有句话,知己知彼方能取胜。”
“中国还有句谚语,井水不犯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