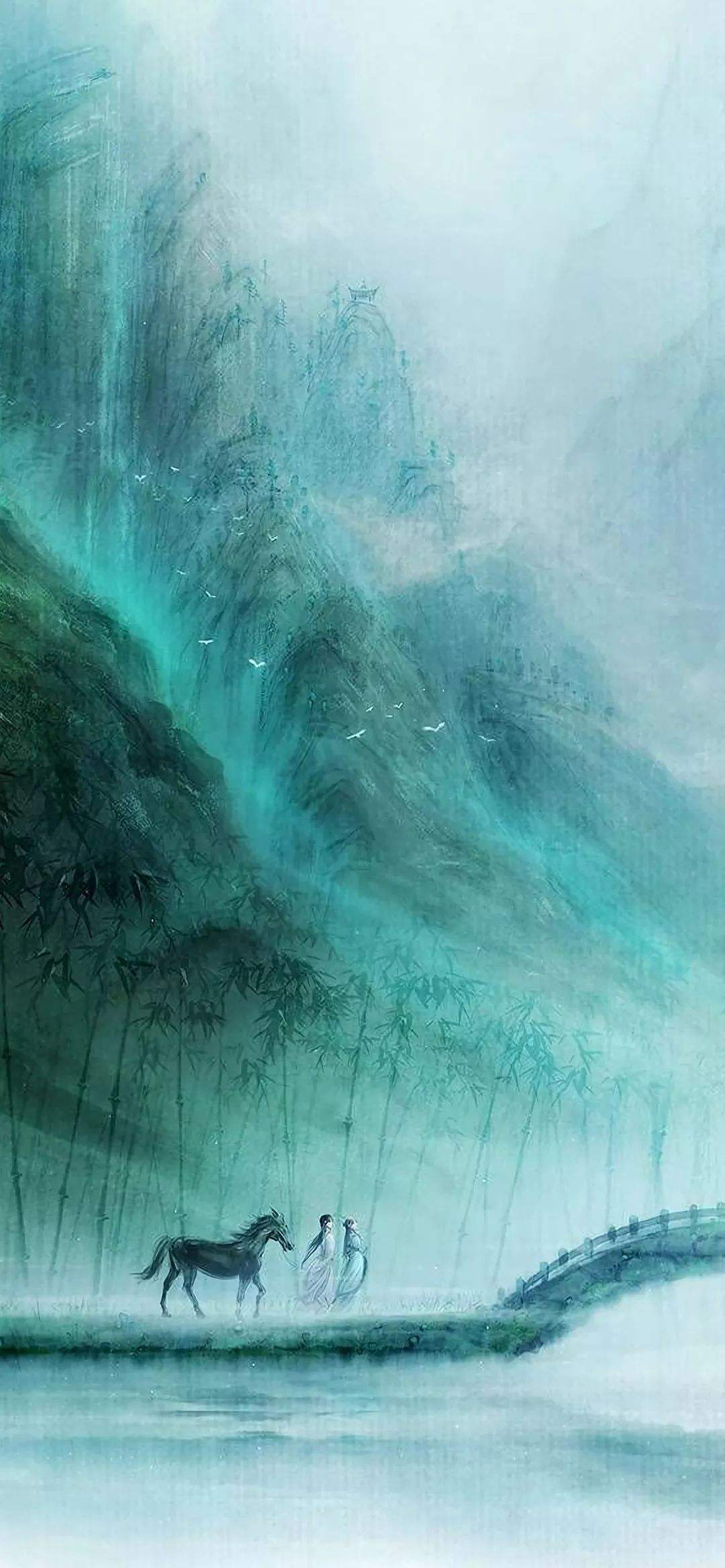公仪敏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之前所住的院子。她习惯习惯。住同样的房间,睡同样的床。她进屋前,在水池前站住。她伸手舀水,从自己的头顶淋了下去。她连舀了十几勺,水沿着头发流遍全身,淌了一地的血水。她蹲在地上,双手紧紧捂脸。
不久前,她还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人;如今,是执剑宰割他人的人。他人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中,如同秋风扫落叶般轻易飘零。她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悲哀。
她自问,难道,这就是弱肉强食?
公仪敏站起身,往房间走去。一步一个血水脚印。她来到卧室,解了衣衫鞋袜,光着身子钻进了被窝。她用被子捂住自己的头,却在鼻孔处挖了个孔来呼吸。她缩着身子,在被窝里静静地待着,突然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自己无能之时,只顾着自己活命,只能眼瞅着他人残害自己的人。如今有了能力,可以击败他人,护好自己人,反而在烦恼。自己果真是闲得慌,没事找事。
她越想越觉得可笑,声音越来越大。身子不停地抖动着,笑得十分酣畅。
白篙端着晚饭过来,听见这么诡异的笑吓了一大跳。她把餐盘往桌上一扔,就过去趴在床边,问:“敏城主,你怎么了?”
公仪敏笑得喘不过来气。她缓了缓,说:“白篙,你说我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
白篙松了口气,扑哧一笑,说:“听你这么一问,好像真有点。”
公仪敏又哈哈大笑起来,被子一抖一抖的。
白篙迟疑着说:“敏城主,你真没事?”
公仪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我能有什么事。好了,你把吃的放着就行,我一会起来吃。”
白篙应了一声出去了,临走前把撒了一地的衣衫袜鞋拿走了。
公仪敏又兀自笑了好一会,才裹着被子起了床。天气已热,被子是薄被子。
因为家眷都留在了莘城,再加上没有带什么食材,所以吃食很简单,是几块干粮,和一碗稀粥。
公仪敏一手捏住被子护体,一手抓了块干粮往嘴巴里塞。时不时端起碗来喝一口粥。她听见有脚步声进来,在卧室门前停住。她以为是白篙回来了,说:“进来吧。”
正想伸手叩门的人,听了公仪敏的话,手一滞,转而推门。
公仪敏嘴中还塞着东西,她头也没回,说:“白篙,还有什么事?”
来者干咳了一声,说:“是我。”
“噗——”公仪敏抬眼看,呛出了声。是公仪善。她赶紧端起稀粥喝了两口润气。
公仪善口气低低地,说:“篙姑娘说,你可能有心事。她让我来送衣服,顺便安慰安慰你。要不,衣服我放在这,我走?”
公仪敏呛得满脸通红,她放下碗,摆了摆手,说:“不用。我也正想和你聊聊。你过来坐。”
公仪善瞥了眼她,挪开视线,迟疑着说:“这——”
公仪敏这才注意到,自己裹着被子。她略一害羞,把露在外面的光脚塞进被子,说:“你出去等会,我换衣服。”
“好。”公仪善应道。他匆匆转身,就想出门。迈了两步路,才发现自己的怀中还搂着衣物。他赶紧把怀中的衣物往一旁的桌子上一放,匆匆合门出去了。
公仪敏低声轻笑了一声,光着脚,单手拎着被子,将它放回床。因为手捏干粮有些脏了,所以她去屋角舀水洗了手擦干,这才开始慢悠悠穿衣服。
她穿戴完毕过去开门。
公仪善远远在大厅的另一角,背对着卧室门站着。听见开门声,他眉眼带笑转过身来,说:“女孩子穿衣就是麻烦。”
公仪敏笑着带上卧室的门,在大厅主位坐下,随口问道:“你猜猜看,我在想什么。”
公仪善在靠她左手边的侧面坐下,斜对着她,说:“你定是在难过,命贱如草根。”
公仪敏呵呵一笑,心中有些吃惊。因为她想起了公孙晟的话,他说公仪善懂她。
公仪善见她笑而不语,也跟着笑了两声,说:“你究竟怎么了?我是你兄长,你和我说说看。”
公仪敏干笑了两声,并不想让公仪善知道他居然猜对了。她说:“也没什么,就是脑子乱糟糟的。可能鲜血残肢见过了,心中不舒服吧。对了,我这会才想起,你们几个还没有成婚。祁树白义他们还小,不着急。漏了他们也罢了。你年纪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了。”
听见公仪敏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公仪善有些不习惯。他挪开视线,盯着地砖不做声。
公仪敏嬉皮笑脸,说:“你看上我们莘城哪家姑娘了?我去给你说说。”
公仪善突然红了脸,呐呐说:“敏城主,你要是没事,我就走了。”
公仪敏呵呵一笑,说:“好了,不逗你了。不过,我觉得白篙和公孙钰,还有紫阳、史佳她们都是好姑娘,你可以留意留意。”
公仪善突然看着公仪敏,说:“敏城主,你觉得人为什么要成婚?”
公仪敏含糊其辞,说:“成婚还需要理由吗?年岁到了,自然就要成婚了。”
公仪善摇了摇头,说:“你安排这些小伙子出战前成婚,不过是为了防止他们血染沙场,而无子嗣。也为了让他们的人生,更加圆满。来人世一遭,若是连女人的滋味都没有尝过,确实有些亏。”
公仪敏被他的话呛到了。她涨红了脸,连咳了三四声。
公仪善兀自说:“可是我总觉得,为了绵延子嗣而成婚,太过仓促。成婚,该是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毕竟要携手共度一生。如今还处在战乱中,我是个流落在外的可怜人,如今能讨得一处安睡之处已知足。成婚的事情,于我而言太过奢侈。此事不提也罢。”
公仪敏心有所触,沉默半晌,说:“今天伤亡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