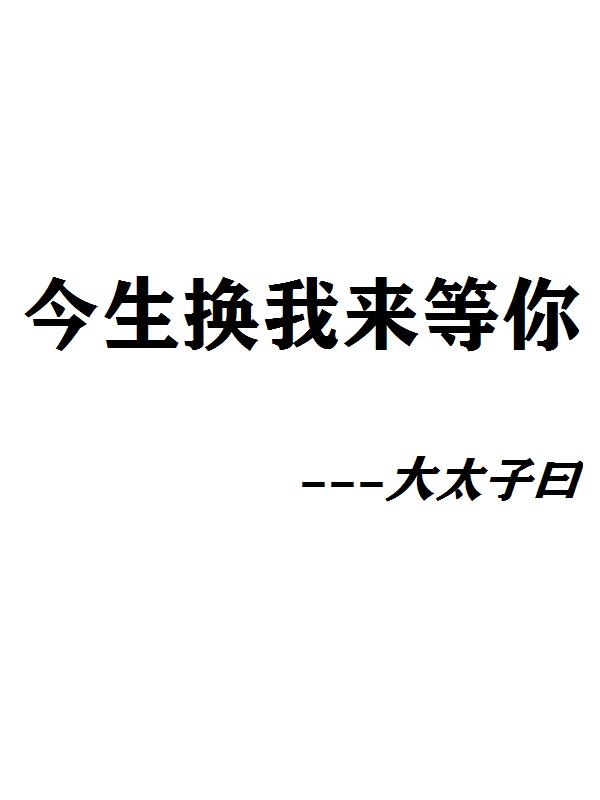我的脑子,百转千回;我的身子,在南郭府的后院穿梭。
南郭彬,如果可以,我愿意与你远离人群。只要和你在一起,就算这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也不会觉得孤独。可是,生在乱世,你我肩上都有担子。我愿,此生我们不要再见,因为我怕再见的时候,我们要刀戟相见。
如果可以,我祈求,下辈子再遇,寻个和平的年代,好好过日子。不要蚀骨的相思,不要心痛的时刻。只要,好好的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你念着我,我想着你,足够。
此生,就当,我负了你吧……
虽然,我也好难过,难过地快要窒息了……
我再次,来到多年前我脱逃的那个墙角。命运,总是兜兜转转。有些人,注定要辜负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纵身一跃,出了院墙。阿篙已经牵着铁血、土灰,等在那里。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匆匆翻身上马,往城门口奔去。
天已经黑了,街上的人并不多。哒哒的马蹄声,踏在青石板上,也踏在我的心上。我的眼泪,掉了两滴,落在铁血的头上。铁血脚步不停,甩了下脑袋,不知是在摇头,还是想甩掉滚烫的泪水。
城门口,辣子他们三个正围着守城的侍卫聊天。嘻嘻哈哈的笑声,响彻夜空,冲淡了夜幕。
远远看见我们出现,辣子还在哈哈笑着,突然一肘子肘在某位老兄的颈后。那人一声不吭,就瘫软在地。
这位突然倒下的侍卫,吸引了其他侍卫的注意。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鼻涕、鱼浆跑过去开门。大门徐徐打开,我和阿篙也骑马到了。我和阿篙一人一个,捞了鼻涕、鱼浆,马不停蹄穿过城门。
又有三匹高头大马,从黑暗的墙角冲出来,上面坐着史宾、公孙晟、公仪佩。史宾伸胳膊一捞,把辣子也捞上马背。
突然有人高喊:“快追!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有几匹马追来,不过很快就被我们甩在后面。如果南郭彬没有喝醉,他也许能追上我们。可是别的人,还是算了。
我们跑得很快,耳畔的风呼呼地刮过。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脸都绷得紧紧地。幸好有月光,不至于看不清路。
我的心,像是缺了一块,冷飕飕地,风能直接吹进去似的。南郭彬,终究要与我形同陌路了。如果不是史宾认得,融城的守城侍卫中,掺杂着几个尉城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起疑心。如果不是公仪佩朝我眨了眨眼睛,我根本就猜不到,他们会这么快动手。
我暗想,幸亏他们把重点放在我身上,而我与南郭彬一起进的房间,所以他们放松了警惕。
春意料峭,我紧紧搂着鱼浆,发出了我的第一声:“你冷不?”
我的声音,没有带着哭腔,没有颤抖,很平静。
鱼浆的声音怪异,好像喘不上来气似的,说:“主人,你要是真的难过,就哭出来吧。”
我说:“傻孩子,有什么好难过的。”
鱼浆说:“那你为什么搂我搂得那么紧?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微微松开胳膊,说:“现在呢?”
鱼浆猛吸了两口气,笑着安慰我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啦。主人,你别难过了,不就是个情郎嘛。回头,晟参谋和宾队长,你随便挑。”不知是谁介绍的,他们三个一直叫公孙晟“晟参谋”。
我“扑哧”一声笑了,说:“我没事。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鱼浆努了努嘴巴,说:“我已经不小了,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我笑着说:“好,你是小伙子了。等回莘城,我给你们三个取个名字,再给你们每人分一把剑,你觉得好不好?”
鱼浆脸上露出欣喜,说:“主人,真的?”
我点头,说:“真的。”
鱼浆说:“不许反悔!”
我笑着说:“你们要是表现差了,我一定会反悔的。所以,我反悔不反悔,取决于你们。”
鱼浆说:“主人,你太狡猾了。我们表现好还是不好,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
和鱼浆说了一会子话,我的心情,变得舒畅起来,不再那么窒息得难以呼吸了。
我说:“鱼浆,你想你阿爹阿妈吗?”
鱼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做‘想阿爹阿妈’。”
鱼浆一直横坐在马背上。他说话的时候,就扭脸朝我看来。而且怕自己挡住我的视线,所以脖子缩着。
我说:“你这么聪明,这么乖,你阿爹阿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鱼浆咧嘴笑了,说:“他们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呢。我有辣子、鼻涕,有你们,就够了。”
我闷声说:“不一样的……”
鱼浆回答:“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个人吗?会真心疼自己的人。有些父母,还不一定会真心疼自己的。我们在尉城乞讨的时候,就亲眼看见有些人家,把自己的孩子卖了。”
我诧异道:“尉城人很缺钱,吃不饱、穿不暖吗?”
鱼浆撇了撇嘴,说:“什么啊,那时有一段时间流行赌博。好多人,都因为输红了眼,所以把自己的孩子卖了。那些孩子可贵了,值钱呐。不过,他们也很挑剔的。女的一定要长得水灵,男的一定要体质好。那些孩子才可怜呢,平时在家娇生惯养、父疼母爱,谁知眨眼间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我和辣子、鼻涕好,不知道什么是‘父疼母爱’,所以也无所谓失去不失去。”
我的心一动,说:“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多久?”
鱼浆回答:“有那么三四年吧,他们在荒庙里交易,我们三个就躲在那里看。后来,我们有钱了,不用住荒庙了,所以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发了会呆。鱼浆见我不出声,便把头扭回去,垂头打起了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