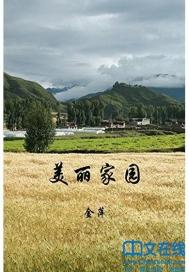日子过得飞快,不觉已经是寒过三巡,枝桠上裹着的银被又被添多了一层压的枝桠凌空似要沉下。
地上更是装饰了一番,从黄的黑的,全换成清一色白的,皑皑白雪铺的到处都是,惹的人好不喜欢。
正背着干柴的白行穿着暖和的厚袄憋着气鼓着脸走下山,正巧看到亭台有个老汉穿着单薄的长衫喝着酒,一旁童子正添起柴火来煮酒。
如此寒冷刺骨的严冬,竟有人穿着单薄长衫伫立冰湖前观湖雪。
真是一番别致景象,白行也是累着,扛着干柴往亭台走去,先打恭,再道:“这雪下的紧,风刮的急,把我冷的牙关打颤,老先生好生厉害,想必素日也是个练家子,不然怎么能穿着这薄衫顶着风雪观湖呢?”
“不然,老朽素日确实有练个一招半式,顶多强身健体,勉强算得上半个练家子,顶着风雪还是靠着锅里的酒祛寒而已。不过小友你顶着风雪上山砍柴,又是为何?”说着教一旁童子添了碗温酒递给白行。
白行接过之后道了一声谢,一口闷下,脸上显出红晕,白行羞笑道:“正住在山脚下,恰好家里柴火不够就上山砍些柴来,一顿劳作热的出了些许虚汗,干了你这杯酒倒让我长了不少精神,不得不说这酒后劲真足。”一旁童子道:“这还用说,不瞒你说这酒可是圣阳名酒。番国进贡,皇族才能喝的起,这酒烈的很。一生津利肺,治咳止痰;二可祛寒取暖,利于五脏。三,酒味十足,味香里辣。对于酒徒来说那可是十足宝贝,你能吃上一口是你的福气。”
白行一听惊得皱起眉头,盯着锅里酒,久久才说道:“敢问这酒大名?”
老汉道:“大名倒无。这酒不过是普通米果酿造,这书童喜爱说荤话,张口闭嘴就爱吹牛,不知尺寸,只怪在老朽荒于管教。”说着敲了敲书童脑袋。
书童一听脸色煞白,耷拉着头闷在原地不敢说话。
白行看了倒也不说话,静候杵在原地看锅上的沸酒起伏。
一阵大风刮过,竟将凌空慢飘的雪花,扫向众人,砉然一声恍若泥石下注,一时怪风更为猛烈。
搅的众人心情一团糟糕。老汉道:“今早时一些湖冰已有化开迹象,时有灵鱼跃动,看似一片生机,还以为转暖了。没曾想正午就变冷了。就只是一阵怪风刮来,林里怪声间或嗷呜,声就吓得人惶恐,又将化开的冰口重新封了上去,瞧这状况,要是再这么待下去,非得冻僵不可。”老汉说着添了一口热酒下肚:“一时半会,也难停下,又不好冒雪出行。这亭台不好遮雪,适才老朽发现一座荒庙倒不是很破旧,避雪毫无问题,倒不如一起去这不远处的荒庙里头避雪。”
白行听了,点头答应便扛着干柴随老汉到了荒庙。
庙里尘封已久,灰尘满布。四野无声,微闻风嚎。众人忙地找了块干净的地坐下,以废桌为柴取暖。老汉道:“老朽听闻日服山曾出过一个探花,官运亨通。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一时风光无限,只可惜晚年被奸人陷害入狱,全家被杀尽了。这庙兴许是以前祠堂改成庙的,后来又因一些事破败了。”
白行听了点头问道:“我住在这日服村这么多年也不曾听过,不知道这探花叫什么名呢?”
老汉道:“李和。”白行想了想,道:“从没听过。”老汉笑道:“这几十年前的老事了,村里早已换了一代人,你要知道那就奇了。”白行不在纠结,转而问道:“不知先生是哪里人?”老汉姓李名物自是野中人,可祖上齐鲁人也,自因一些事迁来到荆州,生根发芽,到老汉这已是隔了三四代的旁支,虽隔几代,可传下来的资产颇丰,平日里喜欢练武也就有闲钱供养身体。
今日来日服山不过是赏湖看雪,没想今日落起急雪来。
白行听了老汉这一说,登时感到不安,一是老汉是邻村大老爷身份差的大,二谈吐上又怕得罪着这大老爷,三有心巴结,可又不敢太有意为之。一时心里五味杂陈,思绪乱成一锅粥。
可此时外边忽然闯进一个精壮汉子,一身官服,配着腰刀,打量着庙里众人,夹着官腔问道:“诸位是从哪来的?”
白行道:“官爷,小的就住在山脚下,这位爷是从邻村来,不知官爷有何见教?”那汉冷“哼”一声,恶狠狠地盯着李物,道:“你是那个村的?”
李物如实回答道:“老朽是从野中来的。”那汉笑一声,道:“自野中到此处可有十几里路,这风大雪大的,光赶路就能耗费半日,你敢说你是野中的?莫不是大话说多了,可笑可笑,竟把人当猪了?”说着从怀里拿出画像往李物身前转了几圈,打量着李物,道:“瞧着挺像的,你是杀人犯?”
书童急忙跳了出来解释道:“我家老爷怎么可能是呢?”
“是不是由我说的算。”说着将他推到一边,汉子看向李物:“你有什么还说的?”
李物撇了眼那官爷,冷冷道:“久不看自己养的猴,也会认错,更何况是长的像的人,你若要这般强词夺理休怪我不客气啦。”
“好!我倒要瞧瞧你到底有什么手段!”说着汉子一把抓住李物的手就要往外走,可没走几步就拉不动,回头看了眼原地不动的李物,心里无名之火烧上心头,炽热的烈火烫热脑干,让汉子脸登时红了片,吱呀吱呀看向李物。
汉子本就是衙门里捕快,仗着自己叔是县令,嚣张拨扈,肆意妄为,遇到不快的人赏他一巴掌也是较为轻,遇到对他出言不逊的人通常都是叫来自己兄弟一通群殴把对自己无礼的人打的遍体鳞伤为止。
这荒郊野岭的,他本就是外出办公突遇大雪慌忙躲进庙内,也不是为了什么捉拿杀人犯这事,只因瞧见李物的脸让他极为不爽,便想拿他开涮,本以为他会服软,不成想碰了个硬茬。
四外皆寂,微微闻风雪刮动。
一时气愤冰冷到了极点,白行忙地上前调和道:“这位官爷兴许是真认错了,不然这位老爷也不会这般做作,你瞧这风大雪大也带不走他,等雪停了也有段时间,不如趁着这段时间仔细瞧瞧去看看,是不是再说了。”
这话说的圆润倒是给了捕快一个台阶。那汉却道:“风大雪大又怎地,今日惹急了何爷我,就算雪神也留不住这厮,长的一副人模狗样,我非得弄你不可。”
李物心里一怒,猛地朝捕快脸上轰出一拳,一拳裹挟着清风,霎时捕快直觉鼻子酸起,鼻血径直流下。
疼痛瞬间让捕快五官脸挤在一起,慌忙捂住鼻子,连连后退,指着李物叫道:“你竟敢袭官,你可知这是多大的罪?胆敢这样肆意妄为,就不怕老子就地正法?”说罢就提刀对向李物。
李物知他急了眼什么事都能做出,便看向一旁书童打起眼神上去劝说,可怎知书童早就被吓得魂不守舍僵在原地,看不到自己老爷打的眼神。
忽然白行喝道:“官爷,别怒了,伤到自己心肝肺可就不好了。”说罢,一把抱住捕快往一旁送去。
捕快却怒不可遏听不进白行劝阻,猛地扭腰欲要将白行甩开,怎奈自己整日沉沦于酒色当中日渐消瘦,如同外层裹了一层鲜艳华丽的外衣里面早是腐朽枯萎。这一甩非但没甩开白行反倒将自己甩到地上。
捕快当即怒地挥刀要砍白行。李物怎能让他得逞,一脚招呼到脸上,给他迎头痛击。受了这一脚捕快鼻血纵流不止,头昏昏沉沉的,晕的要死,好不容易恢复好站起身又因腿脚酸软倒在地上。
白行见状立马把那刀踹到一旁去,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