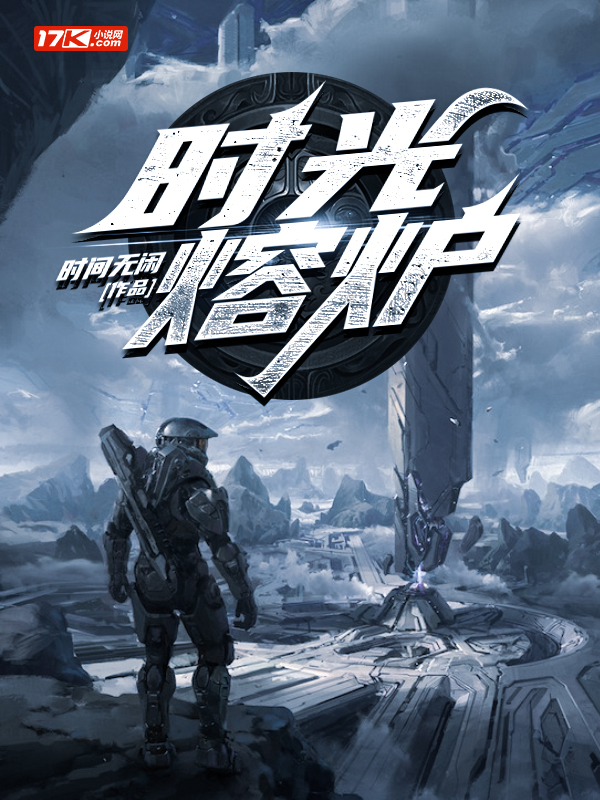1712年9月的某个下午,圣托马斯港劳力市。
七个人孤零零地排成一溜儿蹲在空旷的市场大院地当央,十四条腿饿得节奏混乱地哆嗦着……
“总督,胖又不是我的错?可我饿得真顶不住啦!”
“船长,你就让我出去转一圈儿吧!我保证能弄回两打面包再顺俩钱包……”
“闭嘴!”老德克烦燥地低吼一声,又疑惑地扭脸看向荣兵……
“罗宾,你说这又一上午了,前后左右那帮家伙们都被叫去做工了,咋偏偏就没人叫咱们呢?”
“我哪……知道啊?可能……欺生呗。”荣兵没精打采地回答,他也饿得脑子转速越来越慢了。
“胡扯!刚才那俩黑加勒比人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他们都被叫去搬鱼获了!从早上到现在,四五十个人就剩咱七个!这都两天了,天天这样!你说咋这特么邪门呢??”
“那咋办?头儿?”螺丝有气无力地问。
“哼!以为这就能难住我老德克了?走!换地方!”
圣约翰岛上“克鲁斯贝”小镇的劳力市下午三点二十分。
同样的一幕又在重复重复再重复。早上到现在,劳力市里六七十人一个不剩都被叫走去做短工了——除了德克帮这七个倒霉蛋子。
老德克撅着屁股蹲在地上双手揉搓着头发,发出了饿狮般的低吼:“我特么得罪过你们丹麦的奥丁神咋地?干啥这么往死里整俺们哪?从没听说过丹麦人的地面上这么邪门啊?”
六金刚葫芦娃垂下眼皮默默无语……
“咱们每次明明都占着市场最好的位置!可连那边墙根儿角落里的几个‘泰诺人’都被叫去砍甘蔗了,咋就偏偏又把咱七个剩下啦?罗宾!你小子脑瓜最好使,你给分析分析!”
“真不知道。我来加勒比才几天?我到现在还整不明白哪儿是谁的地盘呢……”荣兵饿得转速越来越慢的脑子基本宕机了。
“嗨!嗨!头儿,那边又来个找人干活哒!看样子应该是个种植园主吧?”切里悄悄指着大门口兴奋地小声喊。
老德克抬头一看,乐了……“哼哼!小样儿地,既然来找人干活儿,那就暴意思啦。现在呆劳力市的除了俺们七个,不信你还能再找出一只耗子来!”
那人穿戴不错,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个挺有钱的主儿。他走进空旷的劳力市先是一愣,然后就眯起眼睛朝这边看过来。见大院中央还有一溜儿人整齐地蹲在那儿,就施施然朝那帮人走了过去。
老德克迅速用手指拢了一下被自己揉搓得很朋克的发型,从容地站起身来,淡定地等待那位先生走近。同时在心中迅速分析着对方可能会需要什么类型的工人,以及自己应该怎样立场坚定同时又态度温婉地讨价还价……
这位先生估计是眼神不大好,走近他们时,还从兜里掏出一个monocle(单片眼镜)对着七人扫视了一圈儿,然后他忽然身体一僵……二话不说返身便走!
七个人连饿带急地全都哆嗦了……老天爷这是摆明了要把大伙先玩残再饿死的节奏啊!两股战战的老德克猛地上前一把拉住那位先生的袖子……随着老德克的手碰触到他衣服的瞬间,这位忽然也像被七个人传染了一样开始哆嗦上了……
“先生!请等一下您别走……”
“撒开!你撒开!干啥?你想干啥!?别怪我没警告你啊,旁边可就是自卫队警戒所!那里有好几千手拿48磅重加农炮的民兵我可告诉你!你真以为能……”
“先生,我就是想……”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理解。这种事儿你想我也想……这年头谁不想挣钱呢?但有句话叫‘君子固穷’你懂吧?不懂?内个……天知道这话是咋忽然钻进我脑子里的,其实我也不太懂,反正就那意思吧。绅士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你总能听懂吧?虽然你看起来不太像个绅……”
“先生,我无法理解你的话,因为我们……”
“啊……帮主!我求您可怜我放过我吧!我真不该那样对您说话我太失礼了我错啦!我知道我听说过,您一定就是近来正在冉冉升起的‘莱德’帮主吧?其实我对贵帮和帮主您一直心怀崇敬之情……”
“谁?我们是……啥帮?”
“您就别再考我啦,因为其实我也几乎差不多等于是您的半个外围粉丝。您当然就是传奇的斧头帮大哥莱德!”
“算了算了快走吧!就您这脑子,我怕去您家干活儿也拿不到工钱!”
“谢谢啊帮主!内个啥……那就祝您事业顺利吧。”
老德克心如死灰地摆摆手,那人果断停止了哆嗦和啰嗦,“噌”地蹿出劳力市大门就不见了。
“他为啥管咱们叫斧头……我、我法克你们六个活该饿死的鬼!谁让你们在衣服下面藏斧头的?谁!?我说怎么这好几天就没人敢搭理咱们呢!”
老德克一转身看见又低头蹲下的六金刚,站着的时候被衣服遮着还看不见,现在一蹲下……齐刷刷地,每人屁股后面都支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利斧!
贝格怯怯地伸出瘦了一圈儿的胖指头点点老德克身后,老德克忽然闭嘴不骂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腰,慢慢抽出一把斧头来……
“嗨!你们几个!一看就是伐木工吧?”一个穿皮衣戴达达尼昂皮帽样子很拽的的男人走进劳力市就粗声大气地嚷嚷。
“这个……可以是……”
“去四英里外的坎达山伐木头一共十几天的活儿没问题吧?”
“这个……必须地……”
“包吃包住完活儿每人3比索有兴趣没?”
“这个……可以有……”
“自带工具不另加钱!”
“明白……”
“工具损坏不管赔偿!”
“可以……”
“走!”
“好……”
1712年12月6日黄昏,法国巴黎辉煌壮丽的凡尔赛宫中。
一位孤独的君王脸上带着未干的泪迹,疲惫地离开了寂静的祈祷室,缓步下楼走出皇家大教堂。心烦意乱地屏退了所有伺从,无心观赏凡尔赛宫中每一处按他的审美情趣精心打造和布置的景观,视若不见地经过那些雕饰奢华的水榭、亭台、柱廊、和喷泉,伴着惨白色的凄冷夕阳,面色忧郁地踏上一条积雪薄覆的的落寞小径,独自朝冬日的运河边走去。
已经过去的1711年是个令人伤感的年份,他的王太子病逝了。可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正在过去的这个1712年更似是要完全摧毁这位曾经光耀整个欧洲的太阳王!2月12日,先是他的长孙媳玛丽不幸染天花去世,不到一周,他的长孙勃艮第公爵路易也因此病随爱妻而去。然而厄运还在逞威!3月,这对夫妻的长子,太阳王的长曾孙布列塔尼公爵,同样因天花病逝。
痛苦的1712,难道你还藏着什么可怕的灾难,正冷笑着躲在浓黑的云层之后,耐心地等待着给这位步履已经有点蹒跚的老人以致命一击吗?从3月到一直到12月,这世上没人能了解这位君王是如何度日如年地熬过来的!现在,这可怕的1712终于快过去了吧?衰老的太阳王每天至少三次虔诚地对天主祈祷,恳求仁慈的主能够保佑他和他的家人熬过这苦难的1712……
1712年12月6日黄昏,加勒比海托尔托拉岛罗德镇北近郊,一座寒酸的农家小院西北角上一间四面漏风的破木板棚里……
或粗豪或尖利的笑声此起彼伏着,溢出板棚响彻在不大的农家小院里。破木板棚里连张桌子都没有,狭小的地当央铺着一块破旧的亚麻布,上面摆着一盆木薯饼子,一盆菜豆炖牛杂,还有一盘晚饭前房东大婶送来的南瓜炒花生。
一个紧挨一个围坐在“餐桌”旁的七个葫芦娃正热烈无比地喧闹着。听罗宾讲到“多大个B事儿啊还架炮轰”时,螺丝腿儿顿时笑得喘不过气来!手抖得连宝贵的朗姆酒都洒了出来。气得坐在对面的老德克笑骂着掰下手里的一块木薯饼子就砸在他脸上!螺丝也不在乎,捡起掉在地上的木薯饼子就塞嘴里了。
一时间,小托尼的嘎嘎声,切里的哈哈声,小梅子的呵呵声,胖贝格的嗬嗬声,再辅之以罗宾的嘿嘿声,在这间狭小的破板棚里乱七八糟地响成一片,就像这七个幸运的葫芦娃抽奖抽到了颗地球似的。
所以你瞧,无论你的生命很偶然地被上老的快递公司随机派送到了哪片时空,其实你都无权报怨命运的不公。真的,无论你是这片时空里的谁,无论是你的身份高贵还是卑贱,无论你是一位光焰无际的君王还是一个贫困潦倒的苦力,时光的沙漏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是如此公平地流淌着。其实,心灵所感受到的苦乐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不过,无论是痛苦的煎熬还是快乐的时光,都在不停地切换着陪伴你而已,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常态吧?就像第二天晚上在同一间木板棚里的场景……
室内一灯如豆,斜阳那点余晖现在也已完全不见了。昏暗狭小的木屋里沉默地坐着七个愁眉不展的葫芦娃。气氛压抑萧索。
良久,老德克咳嗽一声开口了:“大家都说说吧,咋个看法?切里,你说说。”
“还有啥说的?认命呗。”切里低着头摇了摇,一副沮丧的样子。
“贝格,你说说。”
“我……听大伙的。”贝格眼神怯怯的,一副总是这么好说话的样子。
“罗宾,你说说。”
“我也没啥说的。当初我就不赞成来这个岛——不吉利!”
“不吉利?哪儿看出来的?”
“‘托尔托拉’其实本来挺吉利的,我们那儿有个游戏里有句话叫‘托尔托拉庇佑着我们’……可倒霉就倒霉在最后这个‘岛’上了!连一起那就是‘拖而拖拉倒’……这明显是咱们这些打工仔的禁区和恶梦啊!咱农民工兄弟们的血汗钱都是被这么拖而拖拉倒的!卧槽塔格石马的!”
得,就算白问,这小子一激动就从嘴里往外冒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反正没人能听懂。
也难怪荣兵被气得胡说八道的,他这心里是真憋屈啊!整整两个多月,七个人在“茜雪桂种植园”里的汗水全都白流了!当初来种植园干活儿时,庄园管家提出要等咖啡收获季结束之后再一起结算工钱,理由是怕工人中途离开耽误了收获进度。荣兵当时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可老德克觉得没啥,这么大个种植园还能安上轮子跑了不成?可没想到,种植园是不能跑掉,但可以转让啊!
现在种植园主“托奇安尼?西约翰”突然嗝屁!他那刁钻的遗孀“爱妮娜?西约翰”只用了一天就飞速地卖掉了种植园,已经席卷了所有的钱跟情夫搭船离开了“托尔托拉”。人家新接手的种植园主根本不鸟你们的旧账,去镇里找到管家,这个吸血鬼的狗腿子一问三不知地跟你装糊涂,还威胁说再敢打扰他就报治安官抓他们!
马币的!荣兵忍不住在心里祝福着后世那些吸血而肥的王八犊子们!祝福他们早晚都像“茜雪桂种植园”的“托奇安尼?西约翰”一样嘎巴一下瘟死!然后老婆就卷了他的罪孽钱跟姘头跑路再被姘头找个僻静处掐——死!
“罗斯,你说说。”
“我没啥说的,总督你说啥是啥。”螺丝摇晃着头上那撮毛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梅里尔,你说说。”
“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还玛姆大婶儿的房租了……”小梅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还没等老德克点将,小托尼就眼珠一转兴奋地纵马出阵了……
“你们说那些啥用木有!我早观察过了,‘茜雪桂庄园’防范太严,确实没啥机会。但咱们可以去镇里随便找户有钱人家下手啊?管他呢?饥饿的人犯罪连上帝都会原谅哒……”
“噢?那你们大伙的意思呢?”
老德克眯起眼睛深深地盯了小托尼几秒,又环顾着大伙,语调平静地问道。
“我顶托尼!先下手偷,碰上反抗的那就抢!再敢反抗就整死!反正咱们连饭都吃不上了,还管谁的死活呢?”
“我觉得罗斯说得对,又不是咱们想犯罪,咱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切里说得没错!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干吧!”
“罗宾,你……你也……”
“我……听大伙的。”
老德克摆摆手制止了所有人的议论,他又环视了一圈缓缓地开口了……
“各位,我想是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个秘密了。上次进了鲨堡之后,不知为啥,我心里感觉特别不祥!于是我在夜里偷偷向天主祈祷和发誓……如果这次还能活着出去,那我一定要做天主所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做任何一件违背天主旨意的事情!”
说到这儿他把头转向了荣兵……
“罗宾,要不是就在你进来之前的那天夜里,我刚刚在心中向天主发过那个誓愿,恐怕你早死在4号套房里了。罗斯和切里都知道我啥样,要是放在以前,我是绝不会管你死活的!何况我本来就有点讨厌东方人。可我那天却不想再看着阿尔比太过分,也不愿意你就那么死了,因为我觉得天主肯定不愿意那样。”
老德克又环顾着大伙继续说:“现在你们看到了,蒙上帝的恩赐,我自由了。所以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这就是为啥日子再难我也不想带大家去犯罪的原因。好了,现在我给大家选择权,不想和我同路的,门在那儿……请自便吧。”
没人说话,荣兵也没说话,他低着头在心中苦笑:“人生真是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玄妙和无穷无尽的偶然……谁能想到,大不列颠的老德克于1712年4月2日深夜在鲨堡监狱地下黑牢里偷偷对上帝许过的那个愿,居然会救了一个21世纪的中国孩子呢?”
见众人都不说话,荣兵先抬起头来问道:“自卫、复仇、惩罚恶人算不算违誓?”
老德克摇头:“你说的这些不算违誓。如果所有的神父牧师和信徒们真能处处用圣经来约束自己,那全欧洲还有个鸡毛的战争和杀戮?‘打右脸,给左脸’的圣训大家都是拿来说着玩儿的,从来没人当真,我当然也没傻透腔。”
荣兵点点头:“我跟老德克。”
听了老德克的这番解释,荣兵忽然想起,看来“塔丝格?达马侯爵夫人”的那番“信仰论”还真不是瞎掰的。这欧洲人的信仰……呵呵,好吧我啥也没说行了吧?
大家也从刚才企图犯罪的狂热激情中委顿了下来,相互看了看,就纷纷举手表示同意,没一个人离开。只有托尼小声嘟囔了一句:“唉!可惜我的手艺了……”
老德克没出声,又深深地盯了他一眼。
棚屋里刚又陷入了沉默,院子里却响起脚步声,听声音是朝木棚这边走来的。七人相互看看,心情愈加恶劣和忐忑……因为在这院子里走动的只能是一个人——房东玛姆大婶。
玛姆大婶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年龄其实并不老,五十来岁,不过脸上的皱纹却太多了,生活所赐吧。她丈夫以前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商船上的水手,十六年前就在海上得坏血病去世了。她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安德烈斯是一位荷裔英军少尉。1703年在西班牙王位战争中的奥克斯塔特大战中战死了。
小儿子安东尼是一条英国商船上的二副,前年在佛罗里达半岛东岸被一艘巴哈马海盗趁夜袭击了他们的商船。劫掠之后,一个绰号“蝮蛇”的年轻海盗头子似乎对战果不太满意,下令把船上的洋苏木和可可全都扔海里去!
船主对安东尼一向还不错,安东尼不忍心让船主多蒙受这几百英镑毫无必要的损失,就鼓起勇气站了出来,低声下气地向那条“蝮蛇”恳求。结果“蝮蛇”却呲起獠牙乐了……
他命令手下把安东尼打倒在甲板上,自己走过来蹲下,像个快乐的孩子在玩着什么开心的游戏一样,双手各持一支决斗手枪抵住安东尼的两个膝盖……“嘭!”
凌晨,船医给安东尼灌了几缸子朗姆酒当麻醉剂,就直接用骨锯把双腿膝盖以下全部截肢了。他真不幸,居然还活了下来!所以现在只能在屋子里有限地活动,像个废物一样靠着年迈体弱的老母亲养活。
玛姆大婶是荷兰人,在这个以英国殖民为主的罗德镇是很受排挤和孤立的。她的家庭有两代三个男人为所属的国家或公司付出了生命和健全的肢体,可日子却穷得几乎过不下去。她们现在连罗德镇里的房子也住不起,只能住在镇郊。
玛姆大婶是靠着给镇里的富裕人家或自卫队员浆洗衣服勉强过活,偶尔也打各种零工。艰难的生活和不幸的人生遭遇,使她早早地羸弱衰老了。当时老德克他们来到“茜雪桂”种植园打工时,因为庄园女主人爱妮娜?西约翰讨厌工人住进庄园,于是就租了玛姆大婶家院子西北角一间漏风的木板棚暂住。租金只有少得可怜的每月40便士,可现在,就是这昨天就该付的80便士,老德克他们也拿不出来了。
随着大婶脚步声走近,梅里尔第一个深深地把头埋进曲起的双膝之间……因为他是老德克任命的帮中主计长,也就是会计,所有的钱都由他掌管。上个月该付房租那天,种植园以“现在付工钱怕你们拿了钱离开,导致下面的活儿没人干”为由,拖欠了他们的工钱。
手头拮据的梅里尔就红着脸去跟大婶商量,能不能等下个月拿到工钱再一起付清房租?善良的大婶倒是很大度,她宽厚地笑了……
“没事没事,德克先生和你们这些小伙子都是诚实的好人,大婶这么大岁数啦,好人坏人看得出来。大婶虽然穷,可这点房租也不会太在乎的。何况你们这几个孩子又老是帮我干这干那的,安东尼和我都非常喜欢你们。他尤其喜欢和罗宾聊天,他说罗宾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
梅里尔感激地说:“谢谢大婶!您放心,下个月一拿到工钱我马上会付清房租!”
大婶豁达地摆摆手:“瞧你这孩子说的?这不算啥。要是你们手里宽裕了就给。要是不宽裕,你们想住多久大婶都不会要房租的……”
昨天就该是付清两个月房租的日子了,结果……今天大伙却落到了这般田地……唉!!
“德克先生,你想把孩子们饿死吗?”
玛姆大婶刚走进这间灯光昏暗的屋子就开始埋怨老德克。
“呵呵咋会呢?大婶儿,我们刚吃过啦。”其实老德克比大婶也就小个十来岁。但大伙都这么叫,而且大婶长得确实非常老,所以老德克也就跟着这么叫了。
“别跟大婶扯谎!你们连火都没点,哪来吃的?喏……这是今晚我和安东尼的饭,大婶糊里糊涂地就做多了。我怕扔了怪可惜的,放着吧又怕坏了,你们就当帮帮大婶吧。”
玛姆大婶放下一个盆子,很快地转身出去了。
贝格看到大婶刚一出门,马上跳起来掀开盆子上月白色的麻布,里面是满满的一盆蒸甘薯。他就小声嘟囔着:“大婶也真是的,她和安东尼就俩人,干啥一次蒸这么多啊?扔了是怪可惜的。可这东西放上几天也不能坏吧?大婶可真傻!呵呵……”
房间里没人说话也没人动。贝格偷偷看看大家,咽了口唾沫也没敢伸手去拿甘薯。又沉默了一会儿,老德克声音黯哑地说:“每人吃半个,剩下的用布包起来。咱们夜里就走!”
荣兵吃惊地抬起头瞪着他:“你……咱们要赖掉可怜的玛姆大婶的房租逃走??”
老德克的脸“呼”地胀得通红……忽然恼羞成怒地“当啷”一脚把盆子踢翻了!他伸手指着荣兵压低嗓子怒吼:“好!好!有种你别走!你留下等着大婶每天都施舍点吃的准饿不死你!罗宾,你还要不要脸?!”
无星无月的深夜,七个人静静地站在木板棚的门口……
“谁还有啥能给大婶留下的?唉!算了……”
老德克说完又灰心地摆摆手。这七个家伙有六个是经过了监狱洗礼的,另一个小梅子的遭遇似乎比他们几个还惨呢!除了不能割舍的疯狗刀,谁还有啥值得留给大婶的?
七个大男人垂头无语。老德克叹了口气一挥手,七个逃债的民工可耻地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出了院子,连头都不敢回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