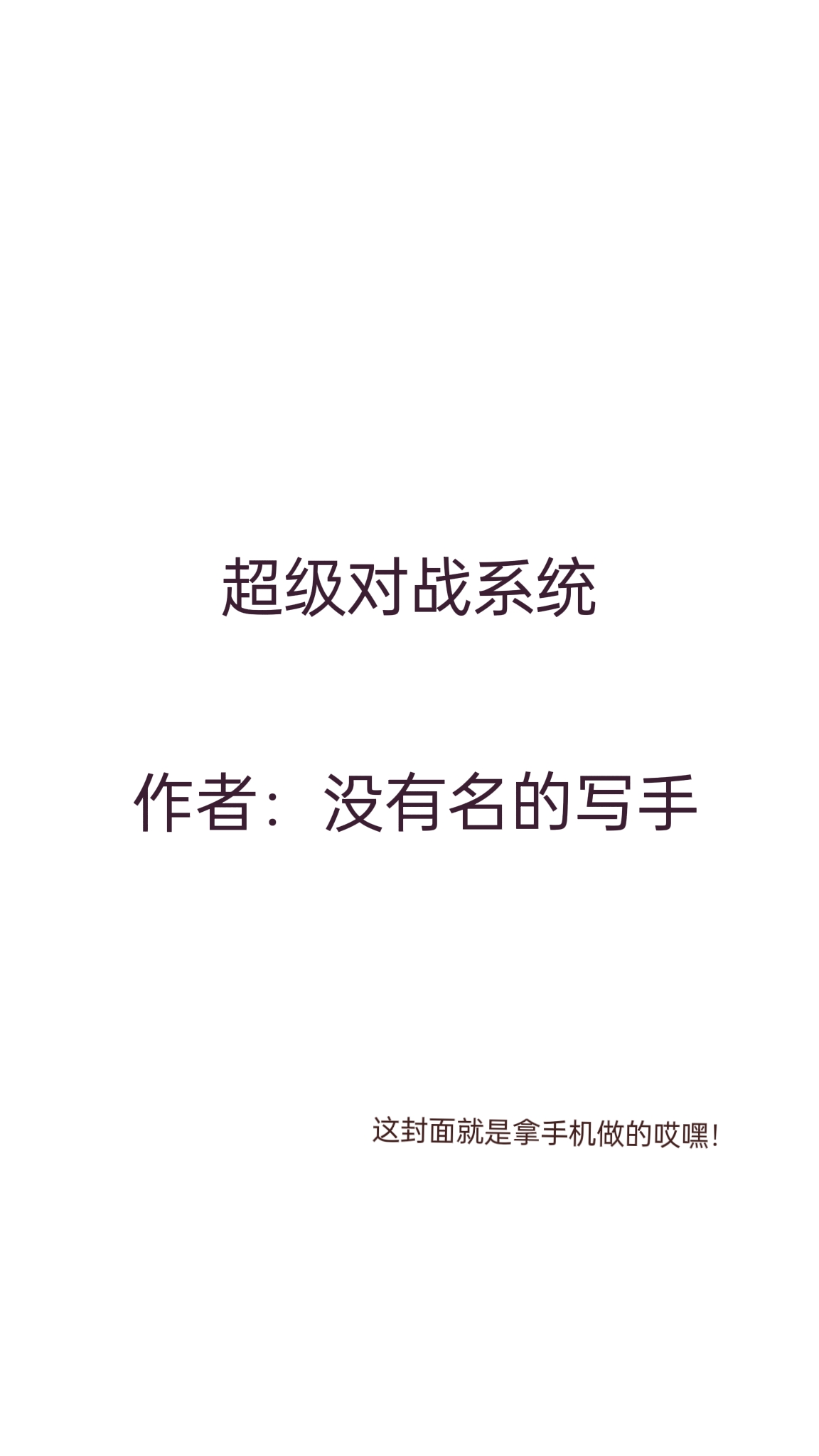天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雨滴从白茫茫的天空中向下飘落。清风抚过,缤纷的雨滴飘散开来,镜头开始缓缓旋转,顺着闪亮的雨滴坠落的方向,不断向地面推进。最后,在一条车流繁杂的交通干道的十字路口,靠近不远处两旁栽有高大梧桐的人行走道的道路右侧,一个穿着白色短衫,黑色长裤,侧着身子倒在柏油路基上的年轻人上空停止。
鲜红色的液体从后脑和后背渗透出来,流在地上,汇成一滩黑红色的浅洼,白色的衬衫浸在里面,染成了红色。身体不停地无规律地抽搐着,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颤抖着微笑,似乎有什么话梗在喉咙中,却喊不出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是目光却是呆滞的迷惘的,停留在茫茫的天空尽头,宇宙深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在看什么,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他的眼眶里,分明有一滴晶莹的热泪,顺着斑斑的血迹流落下来。他伸出一只手,想要抓住什么,他看见,尾指上那枚银闪闪的戒指,在细雨中,泛着冷冷的寒光。
然后,眼中的瞳孔开始放大,目光渐渐失去神色。
……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我又回到了那个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我看见欢穿着那时候非常流行的小旗袍童装,正光着脚坐在外滩某个地方砌沙子过家家,大眼睛乌溜溜地望着我,她在对我笑,我以为她要问我‘桐,滴答到底是多久啊?’我迈开大步向她走去,身上的伤口开始撕裂,血水把西装染湿了,渗出来滴在海水里,我不知道是眼睛被染红了还是海水变红了,我面前的这个世界一片鲜血的颜色。正当我快要涉过海岸的时候,突然一辆大车朝我开过来,我猛地双手并拢挡在胸前,眼前立即漆黑一片。
也许世界上真的有预兆,有报应这回事。
我望着渺茫的天空,山的尽头,云的彼端,穿过浩渺朦胧的时空界限,我来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视线不清楚,我只能看见前方依稀有一棵大树,大树底下,是一个女孩,还有手里撑着的一把红色小伞的轮廓,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向她艰难地伸出手臂,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抹红色,从面前渐渐明亮起来的世界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