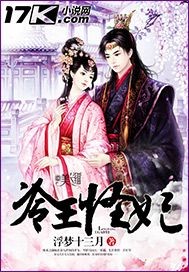以往那些年,白玛每次下山最多三个月便会回转,在山上呆一两个月后才会再次下山。周而复始。
而这次白玛下山已经近半年没有回来了,絮濡沫很是担心,尤其这个月,心里更是七上八下,总感觉白玛已发生了什么意外。思来想去,絮濡沫知道她暂时等不到雪莲成熟了,为了白玛,她准许自己提前出师,下山寻亲。
穿来近九年了,毕竟是第一次真正的要去接触这里的世界,她心里闪过期待,雀跃,却又有点胆怯,迷茫,首要的一点就是下山之后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曾听白玛说过这里若不是军用,百姓手里根本没有舆图,就算有也是手手相传,既不标准也不详细。所以下山后要先找到有人的城市打听清楚再决定之后的线路。
临走前絮濡沫再去看过天山雪莲,确定了一下花期,随后收拾简单的行囊,带些必备的药草和干粮,将羊群散养在湖边,告别雪儿,雄纠纠气昂昂斗志满怀的出发了。
此时已值寒冬,外面的天看起来比天山的低,风也比天山的大,在这塞北之地,万物苍凉隐有风雪,全无绿意。出了天山后路只有一条,其他都是峭壁悬崖。
行了半天才算是出了天山的范围,絮濡沫悠哉游哉的顺着这一条路晃荡着,直到后来面前出现三条分岔路。
眼望着三条路,一条往西南,一条往正南,一条往东南。都是一眼看不到尽头。絮濡沫蹲在原地画着圈圈纠结。
最后,絮濡沫长叹了一口气,选择了一种最科学的办法。
扔鞋。
东南。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前脚始一迈出天山,后脚某处隐蔽的林中便有一只雪白的信鸽一飞冲天,直往京城而去。
……
长颂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日。诚王府 。
男子一身锦袍有些慵懒的斜靠在椅子里,半低了眼,浓长的翘睫遮了眼里的锐光,嘴角噙着淡淡的清笑,轻轻撇着茶杯的茶叶。
“五爷,淮王现如今越发的…肆无忌惮,我们是不是该…”左下首第四把椅子里,一个脸颊微黄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迟疑的道,此人乃刚加入诚王派的吏部左侍郎靳方衷。
“无妨。”上座的尘拜无霁眼亦未抬的打断他的话,随后端起茶杯,轻啜了口。
“此次事件的所谓苗疆余孽,是否属实尚有待追查。不过,本官以为,十多年前收覆苗疆的战役里,大皇子不幸身死战场之事应也与淮王有关。当初可是大皇子和淮王一同跟随前镇国大将军领兵前往。”右下首发须微花的兵部尚书耿志抚须道。
“苗疆?”尘拜无霁挑了一旁的眉,笑容微深,意味深长。
“十七年前收覆苗疆之时,大皇子身死,八年前苗疆巫女蛊惑前镇国大将军行刺皇上,皇上重伤垂死,大将军一家株连九族,而今,又有苗疆余孽隐藏京城,暗杀了二皇子和数位大臣。” 右下首第二位老者,乃督察员左都御史时逸闻,只听他重哼一声,道:“苗疆二字如今都要成为我尘国的禁忌了。”
“苗疆是假,假借苗疆之手才是真吧。”
“太子如今形同虚设,崇王虽不断扩充势力,可现下又动不得,淮王对五爷的按兵不动也一直持观望态度,如今又去了一个二皇子,下一个恐怕会是六皇子轩王了。”
“自五年前崇王从天山归来,淮王就一直派人盯了天山出口,想获一株天山雪莲为皇上解毒,如今看着崇王不断扩大却不能奈何,想必他也如刺在喉。”
“如今崇王壮大也不是坏事,可以牵制淮王,不至淮王一家独大。”
厅堂里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不断谈论着如今的形势,而首座上的尘拜无霁带着疏离的轻笑,一脸风轻云淡的品着茶,似对众人的话充耳不闻。
穆之珩从众人背后行到尘拜无霁身旁,拱了拱身子,一抱拳,用只有两人听到的声音道:“五爷,宁州的飞鸽传书。”说着,将手中的传书递上去。
尘拜无霁此时才微微抬了眼,接过那小小的纸筒,穆之珩垂手顺势退了一步站在身后。
缓缓展开,看罢尘拜无霁轻笑一声,手指微微一动,纸张瞬间碎成千千万万的细末,顺着指缝飘飘洒洒。微仰了头闭着眼睛略作思索,随后,淡然的问道:“本王要去宁州,有何法要父皇放人?”
“此时京城情势紧急,五爷去天山之下的宁州何意?”刑部右侍郎叶庭丰不解的问道。
按察使韩成首先站起,谏言道:“五爷去宁州定有五爷的深意。若想让皇上放五爷去宁州,此时年关将至,极北的鞑子经常在这个时间前后出关打秋谷,五爷可以向皇上请命前去平叛。”
“此事不妥!五爷!宁州接近困仙关。困仙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算带兵前去,他们一见官兵便退回困仙关,官兵一走,他们又再出来。近年来,皇上早默许了他们,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此命定请不下。”兵部尚书耿志劝道。
“我们可以派人暗中协助鞑子,大肆在宁州掳掠,引起京城注意。如此,定可请下。”户部尚书陈世相一脸不在意的冷笑道。
耿志闻言后,立即又出言驳斥道:“此言差矣。宁州常年动荡,百姓已是苦不堪言,而今怎可为一己之私置万民于水火?”
工部右侍郎岳景元想到之前看到的北河文书,遂建议道:“听闻北河城新培育一种粮食,亩产千斤,且不畏严寒水旱,如今季节,五爷可请示皇上带些许新粮去宁州分发,开春试种。”
“此法甚好。”尘拜无霁闻言颔首,同时睁开了一双魅惑的凤眸,赞赏的对岳景元微一颔首,随后道:
“之珩,准备笔墨,本王即刻拟折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