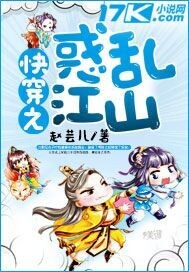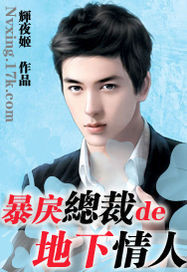陈旭冲,死了。
絮濡沫也不由的深吸一口气,那个掌管天下钱财的户部尚书的小儿子,那个残虐成性的兔儿爷,那个阴柔邪肆的陈大少,一眨眼的功夫,死了?
看来这件事要麻烦了,估计是要连累到尘拜无霁和眼药了,也许刚才眼药的匆忙离去就是听说了此事,更让她心惊的是,从陈大少出现到出事,也就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两盏茶的时间里竟就有人谋划了这一场完美的栽赃陷害,而且牵扯着两位王爷,她一直强调不要卷进他们争夺皇位的战斗力,却还是不知不觉的被人拖了进来。
尘拜无霁面色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一般,并没有太大的惊讶,但絮濡沫依然从他瞬间深邃如渊的黑眸中看到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凝和巍然,他上下打量了眼陶幺,“你是如何逃脱的?”
陶幺一直隐于袖下的手伸了出来,掌心中握着那团雪白的蚕丝长绳,将它交予尘拜无霁手中,“我随着陈旭冲他们刚过了东阳街上了羚角桥,刚上桥便有黑衣人从水中冲出,个个都是好手,二话不说的将刀架在陈旭冲脖子上问冰蚕丝的解法,陈旭冲胆颤之下说了,那些黑衣人一语不发的当着众人面救了我,而后将陈旭冲一行人全部一刀斩杀,离去时,我猜到他们此举是要栽赃给你或者崇王,因为被冰蚕丝捆缚,内力不继只来得及拦下两名黑衣人,但都被他们吞药自尽了,没留下一个活口,我仓促中检查了下周围,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我怕你不知此事再落入敌人圈套,没敢再耽搁,带了你派去跟踪的两人迅速赶了回来,看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
尘拜无霁把玩了一会冰蚕丝,待陶幺一番话说完,又将冰蚕丝递给了絮濡沫,“这是冰心扣,不过要有固定的手法才可以,看你之前的样子似乎挺喜欢的,你拿去玩吧,至于手法,以后我再教你。”
她看了一眼陶幺,沉默的接了过来,冰蚕丝极软极柔,入手细腻冰凉,像鞠了一捧雪水,若不用内力抵制,便如一蓬银针扎入一般酸痛,而她本身就是出自极北的天山,又是在寒潭中休习内力,自小练出的内力便也属了寒性,对这种寒冷早已习以为常,越是冰冷的东西对她的内力增长越有利,她将冰蚕丝一圈一圈的绕在了手腕上,氤氲雾气的蚕丝映着姣白细嫩的手腕,如皓白的明月自纯净的雪山上升起,洒下一派月晖,清冷雅静,美的惊心动魄。
缠绕到最后,絮濡沫试了几次都没系上,这才明白,果然是需要固定的手法才可以,尘拜无霁修长的手从她手中结果两根线头,灵巧的手稍一动作便挽出一朵琼花般的结,他纤密的长睫低垂着,遮了眼中一闪而过的柔情,只余凛冽。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估计陈世相一得知儿子死讯一定会请求皇上搜城的,你去喊起墨浔,让陶幺护送你们出城,那些监视你们的安元营精兵你就不用管了,他们不会伤害你们了。”
絮濡沫一听附近还有安元营的人在附近,不由问道:“既然安元营的人在,难道不能让他们出面证明我们没有杀陈旭冲吗?”
她没问安元营不会伤害他们了是什么意思,通过别浒山一番惊险之旅,她已经了解安元营表面上是被皇上认为有异心从而忽略打压,实际上却隐瞒了所有人在培养发展安元营的势力,安元营这一秘密被他们发现,若不是被十一请旨赐婚,估计已经走到了被灭口的那一步。
“我来时看到他们的人都在外围,只有在你与陶幺打斗时靠近过,随后又退了出去,他们和这朝夕阁所有客人看到的一样,都是我们与陈旭冲有矛盾,他被杀是在外面,他死了,陶幺安然无恙的回来,就不由人不猜忌了,时间紧迫,你快唤上墨浔跟陶幺走,我们合伙骗了陈旭冲瞒不了多久,别让他们再在这件事上做文章,趁刑部来拿人之前,赶快离开,我去羚角桥查探一番,看能否查出些什么,刚才七弟形色匆忙,估计已经过去了,我们一会结伴进宫,不能让陈世相先握了先机!”
说完,尘拜无霁又交代了陶幺几句,又留下了几名隐卫,离开了。
絮濡沫知道这个时候她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到的躲的远远的,让尘拜无霁和眼药全心全意的去应对这场阴谋。
她带着陶幺上到四楼,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伸手敲了敲,顺便解释道:“墨浔就在这间屋子。”
等了片刻没见有人开门,絮濡沫又用力的拍了几下,正拍着,陶幺已一脚踹开房门,一个闪身便晃了进去,没一会的功夫便又出来了,手里提着一封折叠整齐的信纸,交到絮濡沫手中,道:“看样人已经走很长时间了。”
絮濡沫打开信,字写的很漂亮,龙飞凤舞的,却不让人感觉张狂,只觉雅致。
手中的信突然又被陶幺夺了去,絮濡沫急声道:“哎,我还没看…”话没说完便见陶幺夺过信纸后,促狭的看了她一眼,一本正经的将信纸翻转过来,絮濡沫脸一下子红了,反了,竟然拿反了,为什么拿反了看,那字还是觉得好看呢,这下不用装了,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不识字了。
她见陶幺扫过一眼后,内力流转下,信纸化作碎屑飘飘洒洒,雪花般落下,怯懦着小声问道:“他,信里说什么了?”
陶幺一双精致的桃花眼还带着没有消褪的惊讶,促狭,和淡淡的担忧,在絮濡沫身上停留了片刻,才道:“走吧,他说怕被尘国皇帝灭口,他先离开了,寻他主子去了,还说让你放心,你救过他一命,他不会恩将仇报,这些事他不会泄露出去的连累你的。”
陶幺带着絮濡沫直接从墨浔房间的窗户离开的,刚转过一条街便被陶幺拉了一把,她赶忙伏低身子,小心翼翼的抬眼望去,只见街道尽头转过一队步伐整齐的官兵,队伍长长的,见首不见尾,一来便将朝夕阁周围的摊贩驱散,严密的包围起来。
一名骑着马的男子似乎是这个队伍的首领,进去搜查的官兵出来后都在他马前汇报一番,远远的,絮濡沫似乎看到那名男子极其不悦,又出来两名官兵汇报过后,那名男子突然转头,一双如鹰隼般犀利敏锐的眼眸,刺破阳光,直达絮濡沫眼底。
她心中一惊,赶忙低头,不敢确定那男人是否发现了她,只能静静的伏在屋檐上,一动不动。
陶幺轻声说道:“他是陈世相的外甥,独孤鸿,他没发现我们,我们快些离开吧,他在这里查不到我们,马上就会封锁城门了。”
说着率先运起轻功向着城外而去,速度不紧不慢的,絮濡沫在后面跟着,不由好奇的问道:“不是说快些的吗,怎么这么慢,看你武功倒是不错,难道轻功就这么差劲?”
陶幺闻言不由停下窜起的身影,转过头讶异的望着她,“阿霁教的你轻功?”
说完又跃了出去,絮濡沫看了更加好奇,一边跟随他的身影,半步不拉,一边摇头道:“不是,为什么这么问?”
陶幺又停了下来,絮濡沫也只好停下,却见陶幺更加诧异的看她,上上下下,她被他看的有些迷糊,忍不住也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怎么了,有何不妥之处?”
桃花眼突然眯了起来,完全不复之前的郁结与担忧,带着一丝讨好妩媚的笑,笑眯眯的说道:“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与阿霁傲雪步相媲美的轻功,一般的轻功都是提着一口真气,运气时是不能说话的,没想到除了阿霁你也可以,你这轻功叫什么名字,可以教我吗?”
絮濡沫有些纳闷,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她的轻功是在天山随白玛学的,她一直以来以为自己轻功好是内力深厚,听陶幺这么一说却原来不是,细想来,白玛有一段时间回来给她脑子里塞了无数招式和内力运转法门,可惜都被她浑沦吞枣般的糊弄过去了,倒是不知道这轻功是不是那时候学的,反正她现在只要脑筋一转想要腾跃挪移,内力便不知不觉的在身体里的几个大穴中行走,轻功便就这样使出了,但具体怎么使出来的,她还真是不知道。
但,她这人就是烂好心,估计是被自己父母冷落怕了,所以,上一世她认定了的姐妹朋友,只要有什么请求之类的,她为了不失去他们基本都会答应他们,他们借去的衣服,手提包,首饰,钱,甚至车子,都从来没见他们还过,她也知道他们很多都不是真心待她,但她就是怕没有朋友的落寞,她宁愿那些人和她一起假笑,也不愿意一个人流泪,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遇见循弘。
她已经把陶幺当做朋友了,尤其是刚刚还亏欠过陶幺,下意识的她不想拒绝他,但是令她懊恼的是,她又是真的不知道这轻功的来历名字和运用方法,所以她为难的很。
陶幺见了她一脸懊恼模样,倒没有再追究为难她,也不见他有什么失落情绪,只笑吟吟的道:“快出城吧,晚了只能爬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