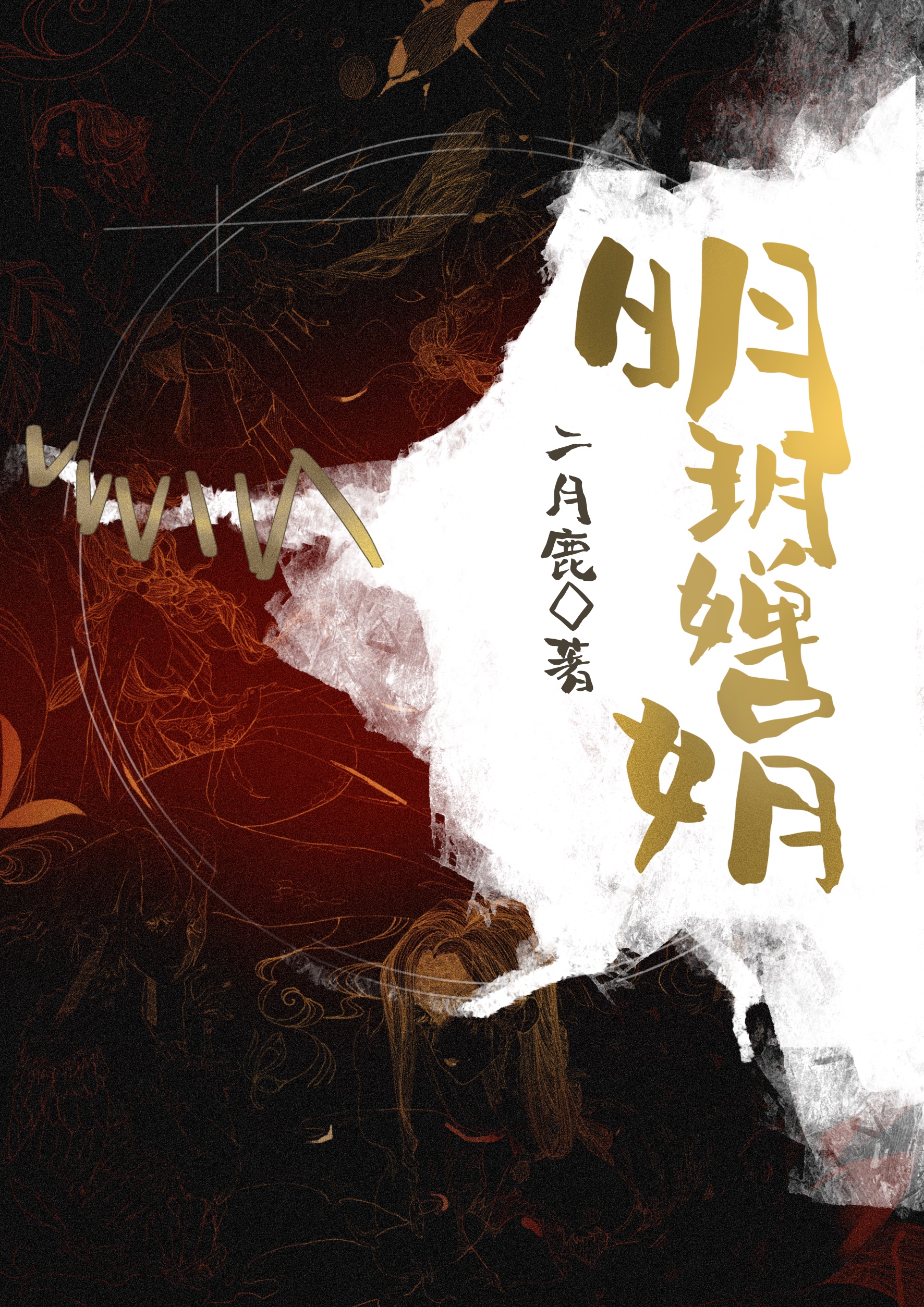说时迟那时快,数十名戴着圆帽、披谒衫、着皂靴的东厂番子悄无声息地冲过来,与围起来的瓦刺人战成一团,但这次是瓦刺寡不敌众。
混乱之中,小王子用头猛地撞向祁王的腹部,剧痛下,祁王手中的长刀不稳,被小王子骤然夺下,刚要反制住祁王,裴南等人冲上来护住祁王后撤到马车旁,小王子不服气地朝祁王冲过来,被赶过来的东厂番子合伙拧着胳膊按住,郑卓趁机在小王子已经受伤的膝盖上狠狠地踹一脚,小王子被迫跪地,番子们手脚麻利的绑起来。
郑卓行礼道:“奴来晚了,让王爷受惊了。”
殷承钰点点头,让郑卓平身退下,转向救场的身着直身的管事,躬身谢道:“多谢管事出手相助,敢问管事姓名?”
领事连忙避开,不敢受祁王的礼,反过来对祁王行大礼道:“小人邓祺,任东厂缉事。今日小人不知王爷来访,未能预先清扫无关紧要的闲人,让王爷受惊,这是小人失职。”说罢,邓祺再叩首。
殷承钰摆摆手,示意邓祺平身,安抚道:“这怨不得你,是本王执意轻车简行,毕竟逛内市要的就是这份热闹,本王不想扰民。”
邓祺再次拱手道:“王爷仁慈,小人感恩戴德。”
殷承钰仔细打量邓祺的眉眼,只觉得熟悉,忽然又想起此人的姓氏,轻声问道:“你与邓祥什么关系?”
邓祺猛地一惊,抬头看了祁王一眼,低头喃喃道:“小人……小人不知道。”
殷承钰了然,邓祺是不敢说。
邓祥是曾经是母后与杨镇当权时期备受倚重的秉笔太监,殷承钰曾多次见邓公公常往来于仁寿宫、乾清宫与前朝。虽然在陛下亲政后被遣到南京养老,但看在母后的面子上,陛下也没有对邓祥的亲眷斩草除根,邓祺便是其中之一,只是也没人再敢提邓公公。
邓祺与邓祥的相貌有相似之处,殷承钰自然觉得眼熟。
既然是故人亲眷,又解了当下燃眉之急,祁王待邓祺自然要热络些,吩咐道:“劳烦邓缉事将这群瓦刺‘商人’收监,至于这些货物……自然就充公了。”
虽然祁王明面上轻描淡写地说充公,但大家都清楚,这就是送给邓祺了。邓祺收了这么一份大礼,有些受宠若惊。
小王子听到手下积攒多年的财物被一扫而空,不禁唾骂道:“大梁王爷,你不要脸!你使诈!”
小王子也想明白,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祁王身上时,根本没有人看到郑卓那瘦小的身影从马车中溜出来,一骨碌躲到车底,颇有经验地混入人群去寻救兵,一转眼就不见了。
小王子的咒骂将殷承钰的注意力重新拉回瓦刺身上,迎着小王子不服不忿的目光,殷承钰讥笑说道:“礼部侍郎没告诉你们当街纵马、谋害亲王是什么后果吗?”
听到“谋害亲王”,小王子瞪圆了眼睛反驳道:“我没有!”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殷承钰不理那他,转过身面向邓祺,命令道:“带回去彻查。”
东厂番子们立刻将直接或间接冒犯祁王的瓦刺人全部收监,尤其也先的小王子。
小王子不服地嚷嚷道:”我阿父是国师也先!你们大梁人敢抓我?!“
邓祺有些迟疑,祁王口中的瓦刺商人,摇身一变成了瓦刺使臣,而且还是国师也先的王子,东厂虽然跋扈,面对瓦刺也怂了。
殷承钰冷眼问道:“你是使臣吗?”
小王子不服不忿道:“我们是!”
殷承钰继续反问道:“今日陛下召见使臣,你们为何不在朝上,反而在内市卖货作乱?”
小王子一时语塞,他就是特意趁着正副使臣不在,这才鼓动兄弟们出来赚点零花钱,顺便抓到机会收拾他口中“不知天高地厚”的祁王,可没想到翻船不说,还把兄弟都搭上了。
可小王子眼珠一转,狡辩道:“我们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你管得着?”
此言一出,邓祺吸了一口凉气。小王子当街蔑视陛下传唤,简直罪不容赦!
“放肆!”殷承钰喝道,“不尊天子诏令,其罪当诛!”
小王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头顶的帽子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有几分急了,反驳道:“你胡说,我没有……唔”
邓祺眼疾手快地将麻核塞进小王子的口中,封住他大不敬的嘴巴,躬身对祁王说道:“瓦刺使臣出言不逊,辱及陛下,此案理应交予东厂处置。”
殷承钰摆摆手,示意邓祺按规矩办事,邓祺谢过祁王体谅,麻溜利索地让手下人将瓦刺人都押了下去,以免再生事端。随后开始理所应当地清算此次瓦刺使臣随行的马匹和皮草,很明显东厂这次要小赚了一笔。
邓祺在宫里混了这么久,也不是吃独食的死木头,他早就敏感地注意到祁王的马车有损,马匹又不知所踪,所谓送佛送到西,他不可能就这样把祁王丢到内市之内。
待手下清理过瓦刺的人,邓祺主动请命道:“王爷想去何处,小人斗胆请求一路护送王爷。”
邓祺如此识趣,殷承钰也颇为满意。虽然她是打算去银磬楼转一圈,然而碰上小王子这个插曲,险胜过后,亲王常服难免有褶皱,厮打过程中,衣摆多了不少脚印,这般狼狈怎么可能出行,凭白丢了亲王的身份。
殷承钰思量片刻,向郑卓吩咐道:”郑卓去告诉银磬楼掌柜,把最新的样式都送到王府来。“随后又看向裴南指派道:”裴南,你派人把马车送去修缮,其余人随本王回府。”
处理过身边人,殷承钰转向邓祺道:“那就有劳公公送本王回府。”
邓祺立马将自己的宝马牵过来,可正在此时,宣课司的人带着北城兵马司的人姗姗来迟。
宣课司主薄正了正衣冠,恭恭敬敬地走上前给祁王行个礼,一脸慌乱地解释道:“小臣得知殿下被困,当即聚集人手来救,可是宣课司的人手有限,小臣不得不向北城兵马司借人手,幸亏兵马司都副指挥使当值,便带着诸位小将赶来,但还是迟了一步,请殿下恕罪。”
殷承钰冷眼看着主薄推诿找借口,听到“请求恕罪”,殷承钰还是忍不住冒出一句反讽道:“主薄哪里用得着本王恕罪,远水救近火,救不了也不算过错嘛,对不对?”
看到宣课司主薄面色有几分难看,还要解释,殷承钰却根本不听,抓过邓祺递过来的马缰绳,利落地翻身上马,扬起马鞭,猛地抽向马的屁股,快马如离弦的箭一般飞驰而去,骇得围在祁王身边的宣课司主薄与兵马司的人纷纷散开。
殷承钰坐在高头大马之上,看着宣课司主薄犹如老鼠一般在马蹄下四处逃窜,皮笑肉不笑地摇着头说道:“诸位真是好打算,告辞。”
既然祁王已经离开,邓祺和裴南也夺过手下人的一匹马,紧追着赶上去。
一时间,内市上一阵尘土飞扬,两侧的商贩纷纷避让。宣课司主薄与兵马司副指挥使许国也不得不掩住口鼻,透过浓厚的烟尘,遥遥望着远处那道红色身影一骑绝尘,两人都生出一点望洋兴叹的心思,京师的贵人们,当真鲜衣怒马,任性妄为,可是他们又能如何?
毕竟这天下,到底是殷家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