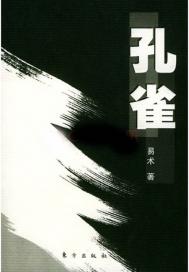读完《胭脂井》,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值得一读,且耐读。
历史小说家最难弄的一件事,就是其作品不但为专家所称道,亦为广大的读者而叫好。此两样,达到其中一样并不太难,但二者兼美,诚非易事。即便如高阳这样的大家,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两善其美。但可以说,《胭脂井》是他写得非常认真的一部佳作。
首先是材料取舍的功力:
小说写了两个大事件,一是戊戌政变,二是庚子拳乱。这两件事,若想写透,每件事都可写出荡气迴肠的百万字巨著来。但高阳先生只用四十余万字写出这段历史,不但愉目,而且惊心。没有上乘功夫,实难做到。况且这段历史去今未远,各种记述汗牛充栋,各种传闻耳熟能详,浸淫其中,非火眼金睛,焉能辩出真伪?当然,小说家非史学家,不必凡事考据,更可正稗兼收。
高阳先生博闻强记,熟读典籍。小说中敷陈之事,多半有据。如湖北黄州发现伪光绪皇帝,记于《睇向斋秘录》;崇绮与刚毅动议废黜光绪皇帝前往荣禄府邸洽商事,载于《蕉廊脞录》;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清除后党事,《便佳簃杂钞》记录甚详。可见动笔之前,高阳于广泛搜求的工作,已做得十分扎实。但史料如珠,如何用一根情节的主线将其连缀,使其成为光彩四射的项链?这就要看“老夫手段”了。小说中慈禧复辟,从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向荣禄告密开始,到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从容就义,其主线是慈禧。围绕她写出了新旧两党的血腥争斗。其中,既有信史,也有稗闻。虽各有纷呈,但都不淹其主。谭嗣同与王五的友谊,本可深写,但小说只写了“大酒缸”相见与菜市口收尸两件事,而且还只是素描式的,没有铺开来写。可见,高阳先生为了主线叙述的突出,对于枝蔓,哪怕很精彩,也是惜墨如金的。
其次是塑造人物的才情:
窃以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中的原始人物。所以,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不是克隆,而是塑造。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其中的人物不单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该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关羽等人,历史中确有其人,但并非确有其事。小说家罗贯中,最大的功劳不是写出了魏蜀吴三国的仇怨纷争,而是成功地把一些历史人物塑造成文学中的典型。塑造人物别无他法,惟有在生动的情节中展现。打个比方,小说中人物好比是鱼,情节则是水。无水之鱼,焉能活否?大海养鳌鲸,池塘养草鲤。所以,没有设计出惊心动魄的大情节,又怎么能描摹出风神各异的艺术形象?
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都是动摇国是震憾社稷的大历史。高阳先生走笔其中,撷英采胜,写出的一些人物,比之历史原型,更加鲜活。如慈禧太后的阴险狡诈、光绪皇帝的懦弱孤苦、荣禄的机心权变、李莲英的左右逢源、载漪的阴骘狂悖,珍妃的聪颖刚烈,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次要人物中,如徐桐父子、赛金花、立方、李西来、许景澄等,也都有不俗的描写。
三是叙述语言的特点:
高阳先生的语言,优点在典雅冷隽,不足在于缺乏幽默感。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是有幸的。这是一种感性的语言,既精确,更精妙。少年时,在外祖父的指导下读《昭明文选》,一篇《江赋》,单是形容涛声的象声词就有数十个,排泻而来。这语言的惊涛,至今令我迷醉。禅之所以产生在中国而不能移植它国,就在于没有这种玄奥的语言的土壤。《红楼梦》将汉语的智慧用到了极处。像“假语村言、真士隐去”、“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这类充满东方思想魔力的语句,换一种语言,怎能表达得如此绝妙?
读高阳先生的书,我总觉得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出身于书香世家且不必说,家风恐怕也是不苟言笑的。因此,高阳先生的小说语言,便如一个徇徇儒者,一边品着青瓷杯中的绿茶,一边娓娓道来。
典雅冷隽,是高阳语言总的风格,反映到《胭脂井》上,一是简洁,二是生动,三是自始至终含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大凡在语言磨砺上下过几年苦功的人,前两点都能做到,比较难以做到的,是第三点。这其中除了作者本人对语言的感悟,更关涉到作者人生的境界。《胭脂井》最后一篇写到光绪皇帝得到珍妃的遗物豆蔻盒时,高阳是这样描述的:
于是皇帝打开盒盖,一阵浓郁的香味,直扑到鼻;顿觉魂销骨荡,刹那间,眼、耳、口、鼻、意,无不都属于珍贵妃了。
寥寥数语,将生离死别的哀痛写到极致。此是明人小品的功夫,看似平淡,细嚼下去,始觉字字珠玑。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又将放在手边的《胭脂井》拿起来稍作浏览。高阳先生作品浩繁,但《胭脂井》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说白一点,很有点书生议论国事的味道。但它毕竟又是正宗的小说。如果在情节的设计上多一点悬念,在珍妃的悲惨命运上再多费一点笔墨,或许小说会更加好看,《胭脂井》的书名,也就更贴切了。
2004.6.13 草于梨园书屋
§§第30章 治疗现代商业社会的药方
——读《商道》有感
在阅读韩国作家崔仁浩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商道》的过程中,我始终怀有一种如对故人的亲切感。尽管我与崔仁浩先生素昧平生,对韩国文学也几乎一无所知。崔先生的这部力著是我阅读的韩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读过头几页后,我就被它吸引,用“一经捧读便不忍释卷”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开篇第一页就写韩国麒坪集团领头人、会长金起燮先生因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试验自己企业刚刚生产的一款新车,在比斯巴登附近发生车祸,不幸辞世。这位会长与书中第一人称的我——作家郑先生有一面之交。因此,在金会长死后,郑先生接受主管麒坪集团实务的企划协调室主任韩基哲的委托,为金会长写一部传记。郑先生在韩哲基的帮助下,清点金会长的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皮夹中有一张小字条,写有“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十个字。郑先生通过查访,发现这句话来自十九世纪的《稼圃集》。而该书的作者,便是当时韩国的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商”的首富林尚沃。尽管历史才前进了不过两百年,但林尚沃在当今的韩国商界,却似乎已无人知晓。于是,郑先生便开始了对林尚沃的商业生涯的研究与发掘……。
我本人写作历史小说,深谙那种搜求历史古卷青灯的寂寞,自然,那种久获不得却因一次偶然而解开历史之迷的快乐也曾使我得意忘形,恨不能即刻举杯邀月痛饮。从崔仁浩先生的书中,我重又获得了这种体验,有时,我们是浩浩沙漠的旅客,有时,我们又恍如剡溪访友的古人。
崔先生笔下的林尚沃,虽然奇特,可是我们并不陌生。在林尚沃生存的年代,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与他经历相仿佛的传奇商人胡雪岩,经高阳先生的小说,胡雪岩在今日中国商界,已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有个商人朋友,说他已读了四遍《胡雪岩》,现正在读第五遍,每遇人生一次转折,他都要读一遍。对于商人来说,《商道》必定也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好书。这样说,也许贬低了《商道》的意义,其实,崔先生揭示的不仅仅是为商之道,更是为人之道。
林尚沃从一个店铺的小伙计,成长为富可敌国的“天下第一商”,只不过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小说巧妙地将一些当时韩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纯祖时期的权臣朴宗庆,洪景来之乱时的造反领袖洪景来与李禧著,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韩国深具影响的大学者秋水金正喜等等,引进林尚沃的商业生涯中。这三方面的人物分别代表着权欲、力量与名誉,作为一个商人,要想有大作为,是不可能绕开这三股势力的。常言道“载舟之水,可以覆舟”,同他们打交道,既可以获得滚滚财源,稍一不慎,也会得到灭顶之灾。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林尚沃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与联系中,林尚沃始终坚守诚信。但是,在大难临头时,仅仅凭着诚信是不足以化险为夷的。书中写到林尚沃一生遇到三次大的灾难,他之所以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全凭一个世外高人石崇禅师对他的指点。石崇禅师是崔先生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是《商道》全书的灵魂所在。石崇出身寒微,是一个弃儿,后被一个技艺精湛的陶工收养,并传授给他全部的陶艺,他本是一个本份木讷的青年,但是,自认识一位漂亮的妓女后,他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令他的养父伤心不已。在经历了许多痛苦与磨难之后,他迷途知返,又回到养父的身边,并没日没夜地钻研陶艺,终于烧制出韩国历史上最为精湛的白瓷匣燔。尔后,又制出更为神奇的戒盈杯,并因此而成为韩国最杰出的陶艺神匠。但是,就在制出戒盈杯的那天,这位神匠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凭借自己的技艺去博取财富,而是携着戒盈杯来到金刚山的秋月庵出家,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石崇禅师。
因为第一次替东家到北京卖人参,为救一个被人贩子拐卖到妓院的弱女子张美龄,林尚沃不惜动用东家的250两银子,这是商人的大忌。林尚沃因此被逐出义州,并因声誉扫地而永不能经商。生活窘迫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来到秋月庵出家。在那里,他认识了石崇禅师并成为弟子。三年后,仍因那位被他救出火坑的北京女子张美龄的奥援,林尚沃重新脱下袈裟,走上了经商之道。临行前,石崇禅师与他有过一次谈话,告诉他这辈子还有三次灾难,并给予了解救之方。
看得出来,崔先生的苦心孤诣,是要通过林尚沃这个人物来揭示主题。应该说,作者的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读罢全书的人,都会接受“戒盈”的理念。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儒家做人的根本,《商道》一书中,多次提到“商即人”,经商即是做人,而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实与戒盈。对于一个人来说,诚实为本、戒盈为用;或者说,诚实为道,戒盈为德。作者将“戒盈杯”这一“道具”贯彻始终,可以看出他的匠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利润的最大化,几乎已成为每个商人的终极目标。更可悲的是,似乎所有的国家、集团与个人,都将这一目标视为经典。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则成为楷模,成为人们崇敬的对象,反之则遭人唾弃。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追逐财富的竞赛确定了人类的游戏规则。而传统的那种悲天悯人、超然物外的人文精神,几乎丧失殆尽。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代意识”,它使所有当今之世的商人乐此不疲,这不是时代的“正声”,而是时代的悲剧。
从《商道》中不难看出,崔先生心仪中国传统文化。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典籍,用儒与禅这两种精神的利器,来剖析与论证“戒盈”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它更是具备了一种“寻根”的意义。
戒盈,是崔先生为现代商业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只是不知道读者诸君,乐意接受这个药方否。
2003.9.21草于武汉望湖楼
§§第31章 闲话历史真实
去年九月,在中国作协港澳台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海峡两岸历史小说研讨会上,唐浩明兄曾对我戏言:“如果你有钱,你就设立一个奖项,在世界范围内征求研究文章,如果有谁能把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研究明白,且让大家都接受他的观点,就给他一百万奖金。”浩明兄说这句话,实乃事出有因。近些年,历史小说的创作非常兴旺。如果用读者决定市场的观点来衡量,无疑历史小说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有嗜史的习惯。小时候读过的《今古贤文》上的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知今”,可作为嗜史的注脚。嗜史并不是怀旧,而是一种观照当今鉴别世事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埃及,俄罗斯等有着悠久历史国度的人民亦复如是。前年,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印度访问。在新德里,主人招待我们观看了一部印度电影《阿育王》,这是一部历史大片。爱情加暴力,故事紧凑曲折,颇有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特点。阿育王所处年代,比中国秦始皇稍早一些。他统一了印度,几乎成了印度历史的代名字。他在征伐期间,嗜杀成性,一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他便昄依佛教。在全国大建梵刹。在阿占陀石窟,我看到了那一时期佛教的辉煌。虽然两千多年时间过去,在今日之印度,阿育王依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印度以他为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少。《阿育王》的热映证明了阿育王这个历史人物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部电影非常喜欢。但问及印度同行,他们中不少的人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回国后,我查阅有关阿育王的资料,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影片中的第二号人物,为阿育王深爱着的那一位另一部落的公主,完全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如果去掉这个人物,可以说整部电影将不复存在。奇怪的是,我的印度同行责难的并不是因为作者杜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令阿育王神魂颠倒。而是认为这部电影过于美国化。印度人支持传统,有着我们中国人无法比拟和难以想像的固执。由此我想到,如果《阿育王》换成是一部中国电影,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专家在赞赏它具有创造性(因为像美国片)的艺术追求的同时,一定还会严厉的指责,它为什么不着重历史,要让阿育王这样一个伟大的开国皇帝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女人?同样都是东方文化,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作品的尺度为什么如此的不同?也许有人会说,印度人注重艺术的真实,而中国人更注重历史的真实。
近些年,在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确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评论家总是用他认为的“历史真实”,来衡量别人的作品。将作品中本属艺术处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侫史或诬史的高度来进行抨击和批判。将文学创作变成历史的考据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问题。文学非物理,它没有客观真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无不充满歧义,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作家,我实在不愿意在“历史的真实”这一命题下过多的绕舌。但是,既然有人老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几句。
前年,应於可训先生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之约,我写了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算是拙著《张居正》的创作谈。文章里,我论及历史的真实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我还说到,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后一个真实,是形而上的,很难做到。大凡历史小说的创作,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即三分虚构,七分真实。这种三七开的说法,源于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是最正宗的历史小说,现在,民间关于三国的许多传说,譬如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关羽亡命走涿洲,张飞喝断霸王桥,赵子龙血战救阿斗等等,都来自于《三国演义》。但是,说到底,《三国演义》只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最权威的史书是陈寿著的《三国志》。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来看,则罗贯中先生的虚构恐怕就不止三分了。上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不是子虚乌有,就是张冠李戴夸大其辞。如此说来,用历史的真实来衡量《三国演义》就大有问题,用文化的真实来衡量,还勉强说得过去。若用事件的真实来对号入座,则必定是理不直气不壮。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似乎也有多处值得商榷。譬如关羽,因为罗贯中先生的精心塑造,他成了忠义的化身,完全不近女色。投降曹操时,曹操送给他十个美女,但他坐怀不乱不肯享用。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他降曹时并未得到十个美女的赏赐;第二,据《华阳国志》、《蜀记》等几部史书记载,关羽在对吕布的战争中,曾一再乞求曹操,希望仗打赢后,能够把吕布手下大将秦宜禄的妻子赐给他。由于他希望迫切,恳求再三,于是引起了曹操的疑心。攻破吕布固守的下邳城后,曹操命人把秦宜禄的妻子带上一看,顿时大惊,原来这少妇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人。于是坚决不肯赐给关羽而留下自家消受。从这个记载来看,关羽是一个好色之徒,罗贯中先生替伟人讳了,也就是说,他粉饰了关羽。
这么说,似乎我要批判《三国演义》违背历史的真实,再刻薄一点,说罗贯中先生厚诬历史了。后辈岂敢如此,举出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历史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虚构。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前面讲过的三点。
如此给历史小说下真实的定义,我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时下有一种风气,在讨论历史真实时,往往对作品中描画的某一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文化心理以及风俗民情忽略不计,而刻意强调人物以及事件的真实性。这种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应该适用于历史教科书,而非历史小说。
勿庸讳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决定了其作品的历史真实。而作家描写历史真实性凭籍的史料,往往会受制于史学家的历史观。例如《明史》,举凡研究明史的人,都必定首先要接触到它,但若一味地相信它或依赖它,则错莫大焉。须知《明史》是清朝人编纂的,对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取舍与评价,则不得不听命于清代统治者的好恶与需要。如对明代皇帝,不管好坏,一律加以美化。就像隆庆皇帝,其沉湎酒色,迷恋道术滥用春药等等劣迹,明人著作中多有记载,正因为他荒淫无度。以至三十六岁就一命呜乎。这样一位庸君,《明史》中却称赞他“端拱寡 、躬行俭约。”对他的私德,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一笔带过。《明史》作者的历史观于此可见,凡帝王,一定要正面歌颂。对皇权有制约的大臣,则被斥为权臣。如果我们依赖《明史》来写作,岂不落入编纂者的皇权至上的圈套?编纂者有此历史观,便会按图索骥,寻找相应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图解与阐释。而对其不利的史料,则弃之毁之。既然史书编纂者有权按自己的历史观来遴选与征集史料,我们作家为何就不能按自己的历史观来“粉饰”与“厚诬”古人呢?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史学家与作家都有权选择自己进入其中一窥堂奥的方式。这里面不存在优劣,只存在历史观的差别。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以苍生谋福祉”。我的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如果有哪位方家觉得鄙人此种做法不妥,敬请批评。
2003.12.13夜草于灯下